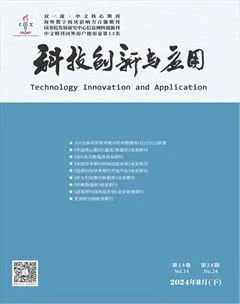地鐵盾構隧道下穿河流施工穩定性分析









摘 要:盾構隧道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穿越河流、湖泊和海洋等富水地層,由于地下高水壓和水源的不斷補給,在施工過程中可能出現較大的風險。下穿河流段的隧道與陸地隧道相比,不僅要承擔土體的重力作用,還需承受較大的水壓力作用,掘進難度較大且風險較高。以青島地鐵2號線二期工程下穿侯家莊河為工程背景研究盾構穿越河流對隧道的影響,通過建立三維有限元模型,模擬分析盾構施工過程對地表、隧道、河床沉降的影響。
關鍵詞:盾構隧道;長距離下穿河流;數值模擬;穩定性分析;地鐵
中圖分類號:U455.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2945(2024)24-0106-0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hield tunnel construction, it is inevitable to cross water-rich strata such as rivers, lakes and oceans. Due to the high underground water pressure and the continuous supply of water sources, there may be greater risk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Compared with the land tunnel, the tunnel under-passing the river section not only needs to bear the gravity of the soil, but also needs to bear the large water pressure, which is difficult to excavate and has high risk. Taking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of Qingdao Metro Line 2 crossing Houjiazhuang River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hield crossing river on tunnel. By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the influence of shield construction process on surface, tunnel and river bottom settlement i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Keywords: shield tunnel; long distance under-passing river; numerical simulation; stability analysis; metro
隨著軌道交通的快速發展,城市地鐵隧道穿越河流、湖泊的情況顯著增加,穿越地層的地質條件越來越復雜。對于盾構下穿河流施工最主要的問題是管片上浮,由于覆土自重較輕和土體處于飽和狀態,容易造成河底地層隆起,并使后構機上移,在管片脫離盾尾時會受到漿液的浮力作用,當管片與覆土自重小于浮力時,管片會發生上浮現象[1]。楊振興等[2]依托鄭州地鐵10號線下穿南水北調干渠工程,基于Buckingham-π定律推導的相似參數,開展盾構隧道下穿輸水干渠設計參數優化室內相似模型試驗。代珂[3]以貴陽地鐵三號線農花區間下穿花溪河為工程背景,結合實時測試,現場試驗等技術,形成了復雜地質條件淺埋地鐵隧道下穿河流綜合施工技術。何鋒等[4]為準確評價綜合管廊下穿河流盾構施工安全性,降低施工過程中的安全事故發生率,基于風險分解結構法(RBS)構建了包括工程地質風險、綜合管廊自身風險、周邊環境風險和施工管理風險4個一級指標的風險評價指標體系。鄧林洋等[5]以深圳地鐵12號線左炮臺站—太子灣站區間下穿碼頭海域工程為例,闡述了泥水平衡盾構機成功下穿碼頭海域、斷層破碎帶及上軟下硬地層的施工技術。黃旭[6]以珠三角城際琶洲支線PZH-1標二工區大學城東站-新造豎井盾構區間工程項目為背景,論述了在水系發達地區采用盾構在軟弱地質條件下穿越2條河流的安全風險管控措施。
本文以青島地鐵2號線二期工程佛合區間盾構隧道下穿侯家莊河為背景,通過建立三維數值模型,研究盾構隧道下穿河流施工過程中的影響性分析。
1 工程概況
青島地鐵2號線二期工程佛合區間全長960 m,左、右隧道間距13 m;區間自佛耳崖站引出,雙線沿金水路直行,以700 m曲線半徑折向東北,而后以800 m曲線半徑下穿侯家莊河側穿金水橋。侯家莊河全長約234 m,寬約128 m,為城市景觀河道,水深約2.5 m,距離河底設計高程最小凈距7.7 m,隧道穿河位置關系圖如圖1所示。
區間隧道主要穿行于強風化花崗巖上亞帶、強風化花崗巖下亞帶、中風化花崗巖和微風化花崗巖,各地層主要物理力學參數列于表1。
2 數值模擬方法與過程
2.1 數值模擬方法
通過考慮盾構隧道施工區間內下穿河流位置以及盾構施工的影響區域,將盾構施工的三維模型的尺寸選取為200 m×150 m×50 m(長×寬×高),模擬右線隧道開挖133環、左線隧道開挖129環,右線隧道開挖50環后開挖左線隧道。模型邊界以外區域的位移和應力變化與盾構施工幾乎不會相互影響,盾構模型示意圖如圖2所示。
模型中盾構區間所穿越地層簡化為水平勻質分布地層,采用摩爾-庫倫本構建立3D單元模型。通過建立實體模型得到了隧道的注漿區域和開挖區域,分別對其外表面進行單元析取的操作。采用各相同性本構得到盾構外殼和管片的2D板單元模型。模型建立所需構件材料見表2。
對模型整體施加自動邊界條件,默認約束模型底部X、Y方向位移,左右約束X方向位移,前后約束Y方向位移。同時對注漿層土體設置改變屬性條件,使其原有的土層屬性改變為注漿屬性。除重力外,荷載分為等效水壓力25 kN/m2,隧道掘進壓力0.12 MPa,管片千斤頂力0.1 MPa,管片注漿壓力0.15 MPa。荷載布置示意圖如圖3所示。
2.2 數值模擬過程
數值分析軟件施工階段的模擬是通過激活/鈍化相關網格組、荷載組以及邊界條件等,模擬盾構施工中的隧道開挖、管片拼接、同步注漿等施工過程。具體施工步驟如下:計算初始應力場,激活所有土層與隧道開挖區域,激活自重、等效水壓力與邊界條件,清零位移;激活右線第1環盾殼與掘進壓力,鈍化第1環開挖區域;激活右線第2環盾殼、掘進壓力、第1環管片與千斤頂力,鈍化第2環開挖區域與第1環盾殼;激活右線第3環盾殼、掘進壓力、第2環管片與千斤頂力、第1環管片注漿與注漿壓力、第1環管片注漿屬性,鈍化第3環開挖區域、第2環盾殼與第1環管片千斤頂力。以此循環掘進,當右線隧道掘進至第51環時,開始掘進左線隧道第1環。
3 數值計算結果分析
3.1 盾構施工對地表的影響分析
由圖4可知,盾構雙線隧道掘進貫通之后,隧道上方地層豎向變形呈現出中間大兩邊小的凹型沉降槽,符合經典peck經驗公式。地表最大豎向位移值為7.68 mm,最小值2.32 mm,地表最大豎向位移值出現在雙線隧道拱頂位置或凹型沉降槽中心。
3.2 盾構施工對隧道圍巖的影響分析
隧道圍巖豎向位移等值線圖如圖5所示。由圖5可以看出,左右線隧道貫通后,距離開挖面越近的土體所受擾動越大,豎向位移最大值沉降值出現在右線隧道拱頂處約1.86 mm;最大隆起值出現在右線隧道底部約0.55 mm,隨著遠離開挖面豎向位移逐漸減小。
3.3 盾構施工對河床的影響分析
盾構隧道開挖后引起河床土體應力釋放,進而發生重分布現象,近隧道周圍土體應力變化較大,遠隧道土體應力變化較小,應力變化從而引起河床土體變形。由圖6可知,隧道正上方河床土體處于沉降狀態,左右線隧道中心線上方各有一個峰值點,最大沉降值為7.48 mm,雙線隧道中心線中間土體沉降小于該值;遠離隧道的河床土體處于隆起狀態,最大隆起量為2.46 mm。盾構下穿河流施工過程中,河床土體位移變化如圖7所示,沿著隧道掘進方向其沉降值基本保持在7.30~7.94 mm之間。
4 結論
通過建立數值分析模型,模擬地鐵盾構隧道下穿侯家莊河施工,針對性地分析盾構施工過程對地表、地層以及河床土體的沉降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盾構掘進過程中,左、右線隧道正上方地表沉降量較大,雙線隧道中間地表沉降較小;隧道圍巖豎向位移最大值出現在右線拱頂處約1.86 mm,隨著遠離開挖面豎向位移逐漸遞減。
2)盾構隧道開挖后河床土體應力發生重分布現象,隧道正上方河床為沉降最大位置,隨著遠離隧道中心線逐漸變化為隆起現象,沿著掘進方向的河床位移值基本保持不變。
參考文獻:
[1] 王德平.超淺覆土大直徑盾構下穿河流反壓防護技術研究[J].科技資訊,2022,20(16):93-96,103.
[2] 楊振興,杜家慶,孫飛祥,等.盾構隧道下穿輸水干渠設計參數優化模型試驗[J].科學技術與工程,2023,23(31):13573-13581.
[3] 代珂.復雜地質條件淺埋地鐵隧道下穿河流施工技術[J].交通世界,2022(22):63-65.
[4] 何鋒,胡少華,章光,等.基于物元理論的綜合管廊下穿河流盾構施工風險評價[J].水電能源科學,2023,41(7):154-157.
[5] 鄧林洋,李紅,劉陽君,等.泥水平衡盾構下穿海域施工技術應用[J].施工技術,2023,50(5):77-79.
[6] 黃旭.軟弱地質條件下盾構下穿河流風險管控關鍵技術研究[J].科技與創新,2022(9):29-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