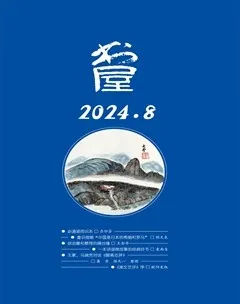由糖葫蘆想到凱恩斯消費主義
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說,凱恩斯主義就是消費主義,刺激消費是各國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激活市場的一把鑰匙。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凱恩斯甚至提議讓政府把錢埋在地下,再雇用工人把錢挖出來,這一埋一挖,就能刺激消費,帶動產業發展。這種看似激進的觀點旨在表明一個道理——人們只要出去消費,市場經濟就會回升。就算是購買一串糖葫蘆,吃一頓美食,甚或買一件沒有實用價值的工藝品,人們只要自信地消費,就一定能創造繁榮。凱恩斯認為,消費者支出就是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因此,鼓勵民眾踴躍消費,甚至鋪張浪費,而不是相反。刺激內需,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是政府主要的經濟刺激措施。從這個角度來看,消費行為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積極做法。
由于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筆者對于凱恩斯主義頗為認同。在市場扮演賣家的角色時,我多么希望走過路過的人購買我的貨品,哪怕他買回去是一種浪費;同樣,當我扮演買家看到路邊“糖葫蘆人”在寒風中的那種期待的目光時,我就希望自己能成為他的客戶,買一串糖葫蘆。我消費后得到的是甜蜜蜜的滋味,他得到的也許只是幾塊錢,但如果持與我同樣想法的人多一點,他也許就積少成多,能夠養家糊口。有這樣的想法,并非有多高尚。同在市場謀生,我最討厭的是,想盡辦法把別人的錢變成自己的錢,在我看來那是一種不道德的商業行為。美國大富豪洛克菲勒說得好:“沒有什么比一個為了錢而把所有精力和時間都花在賺錢上的人更卑鄙和可悲的了。”
當你發現市場失靈后,索取無力,你會停下來思考一下嗎?一個人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多重的,任何人都應該相信,一個有著完全行為能力的人在社會上并非孤立的,而是有責任感的人。即每個人既是買家,又是賣家,甚至每個人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可交易的商品。因為消費文化就因人們彼此交易中的相互聯系而形成。如果同意上述觀點,你就應該思考為什么市場會失靈?何謂蕭條?為什么人們就業難,失業率越來越高?當人們對經濟失去信心時,就會持幣消極觀望,工廠也會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要裁員。如果人們都積極消費,市場就不會失靈。當你積極消費了,你會發現你很開心,隨后你更會覺得市場中的付出和回報幾乎是對等的。筆者經常有這樣的經驗,即我消費了,同時我又銷售了。更直白地說,富人不是靠節約致富的,花錢并不使人貧窮(但在花費中要量力而行),貨幣保持流通,市場才活躍。而相反的例子則走向惡性循環,好比窮人總是握緊自己癟癟的錢袋子,結果發現自己越來越窮。新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家或許會說,“窮人是因懶惰而窮”。并非如此簡單,當務之急在于建立良性的消費文化。
消費文化還關聯著慈善文化。如果你明白施與受的辯證關系,你就會活得開心一點。因為,當你身為賣家時站在買家立場上看問題,你會將心比心——如果我不買別人的商品,又有何資格奢望別人購買自己的商品?如果你不去施舍,別人又怎么會施與自己呢?當然,很多人隨即會反擊道:“我現在沒有任何需求(除了一日三餐),你讓我買什么?我還等著被人救濟,我怎么會有錢救濟別人?”你大可對他說:“難道你沒有精神需求嗎?難道你不喜歡逛街?出門走走,有很多好玩的,還有很多美食等著你去品嘗。至于救濟,有時候對于處于危難中的朋友,你付出時間去探訪,說幾句安慰的話也可。如果你認同時間即金錢,那么你可以把它施舍給更需要的人。”
精神需求從來就不是富人的專利,窮人同樣需要精神生活。如果你留意精神生活,你會發現它隨處可得,比如一幅書法作品、一幅畫、一段音樂、一塊美石、一朵花兒等。這些東西都不實用,但很多時候只要你留意,就會即刻從心里擁有它們,久而久之,你會發現自己在生活中變得越來越自信,越來越懂得去欣賞乃至消費藝術,而不是既貧窮又悲觀厭世。這就是精神生活對于窮人的重要性,因為普通人的生活往往更需要從美的東西中獲得慰藉,而這往往被忽略。
市場總是善于激發你的購買欲,只要你的精神還不至于枯竭,你總能為你僅有的錢找到消費的理由。只有不懂得“錢”的屬性的人,才不明白什么是“自己的錢”。要明白,真正屬于你自己的錢是你花出去的錢,放在銀行里的錢只是一串數字而已。
小人物生活在大環境中,大多是大江東去,隨波逐流,于經濟學對個人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幾乎一無所知。筆者也非內行,只是長期身在市場一線,了解經濟學或許更能理解銷售與消費對市場的作用,理解人際關系。筆者有幸拜讀過經濟學家盧周來的專著《窮人經濟學》,所以對經濟學多少有些了解。盧周來被他的讀者們稱為“窮人經濟學家”,即為窮人發聲的經濟學家。筆者就是通過這位經濟學家認識和了解凱恩斯的。對于為什么會失業,什么是總需求,人們似乎從來不去思考,凱恩斯認為,“總體需求不足可能導致長期高失業率”。總需求就是全球(或一個國家、地區)市場的總購買力。“但在經濟衰退期間,隨著支出下降,強大的力量往往會抑制需求。例如,在經濟衰退期間,不確定性往往會削弱消費者的信心,導致他們減少支出。”特別是在房屋或汽車等大宗商品的可自由支配的購買上。“消費者支出的減少可能會導致企業投資支出減少,因為企業要應對產品需求減弱。這就把增加產出的任務推到了政府的肩上。”根據凱恩斯經濟學原理,政府對市場進行有效干預是調節經濟活動,保持繁榮和解決蕭條的必由之路,也即宏觀調控。至于宏觀調控措施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仁者見仁。有關凱恩斯主義,哈佛大學教授N.格雷高利·曼昆在《紐約時報》撰文稱,要了解經濟面臨的問題,毫無疑問,“這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衰退和蕭條的診斷仍然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盡管凱恩斯已去世半個多世紀了。
提起凱恩斯主義,再次讓我想起了經濟學家朋友盧周來。有一次,他請我們幾位書畫圈的朋友吃飯,是在一個冬季的夜晚。他看到賣糖葫蘆的人還有幾串糖葫蘆沒賣完,于是慷慨解囊全部購下,三個大老爺們便在大街上大嚼酸甜爽口的糖葫蘆。我在想,這個生意人看上去生意還不錯,但他仍然瑟縮在大街上,希望把糖葫蘆都賣掉。終于等到買主了,但他面無表情,不知道是心存感激,還是習以為常,而我這位經濟學家朋友吃起糖葫蘆來卻是有滋有味……這些細節我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設想我是那位賣糖葫蘆的人,為了貼補家用,可能這一天的收入就差這幾串,賣掉了就能回家歇息,妻子緊鎖的眉頭也會舒展許多,孩子的學習費用也許就有了著落,我會不動聲色地感激這位顧客,感嘆天下好心人多一點,世界充滿愛。由此可見,有時候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就體現在一些細微的消費動作上,你花費的不多,但對方獲得的卻能積少成多。甚至可以說,消費就是履行社會責任。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就是讓大家生活得更美好一點,因而經常撰文呼吁人們積極消費,各盡其“財”,幫助更多人,使市場變得更加繁榮,社會變得更加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