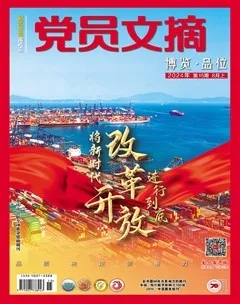43年前,費孝通辦的這個培訓班厲害在哪?

“中國要發展,人民要過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這個學生坐在那兒,不拿錄音機,也不做什么,我真的是心里非常難過。”2018年6月14日,在上海大學樂乎新樓召開的“費孝通與鄉村振興——第五屆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討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繼承費孝通“用自己的知識去服務社會、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的治學精神時,回憶起費孝通批評自己的這段往事。
那是1995年,李友梅從法國讀博回來,正參加北大的一個高級研討班。見到李友梅沒有帶做研究的必備工具錄音筆,費孝通當時語氣很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1981年費孝通在南開大學開辦的社會學專業班的旁聽生。
非常時期的應急手段
1978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著名學者杜任之率先提出恢復重建社會學的主張,這一建議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重視。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到,“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
對于社會學,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理想的“補課”老師是費孝通。1979年春節,胡喬木親自拜訪費孝通,委托其帶頭恢復和重建社會學,這時的費孝通已近70歲。
“最好不要找到我頭上來。”費孝通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我原本沒有學好,又荒疏了這么久,即使有老本本可據,我也教不了。社會科學必須從自己土里長出來。這門學科在中國還得從頭做起。我怎敢輕易承擔這任務呢?”社會學荒廢了近30年,費孝通也擔心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歷史感”讓費孝通還是挑起了擔子,“到了我這樣的年紀還要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個通過新陳代謝而得以綿續常存的社會”。
在費孝通看來,恢復與重建社會學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而當時正是人才青黃不接的時候,老一代社會學者大多80歲左右,很多人早已改行,還有很多人心存顧慮。

在這種情況下,費孝通和時任南開大學哲學系主任的蘇駝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開設短期的專業培訓班。“恢復社會學要培養人才很急,從大一的開始招生要等四年才畢業,太慢了。”蘇駝最后建議采用1958年南開大學籌辦哲學系時的辦法——開辦專業培訓班,把四年的學習內容在一年內學完。
埋下“經世致用”的種子
“實不相瞞,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擠成這樣的。”老伴有病,費孝通讓女兒一家回來工作,便于照顧她。人多了,空間就小了,費孝通只能伏在床邊的小桌子上寫稿。
這是在1979年3月召開的社會學座談會上,費孝通講到自家面臨的“人口問題”。緊接著,費孝通說:“現實生活中,這類的問題實在不少,可以設想,隨著我國四個現代化事業的飛速發展,社會生活的發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內部矛盾必然會不斷發生。如果我們對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能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調查研究,尋求比較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對可能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較早地有所察覺、有所準備,也就可能減少或避免一些社會損失。”
此時,社會大轉型已經開始。這次座談會的前幾個月,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一個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在世人面前展開。
“最早杜任之提議恢復社會學的時候,也是預見到今后的社會發展需要社會學學科。”蘇駝回憶說,這也是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創辦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也使得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遠不止“補課”這么簡單。
費孝通對1981年的南開社會學專業班一直“灌輸”經世致用的理念。他強調,“學習社會學終究是為了認識和了解中國社會,達到民富國強、改造社會的目的。不贊成只在書齋里討生活、為社會學而社會學的做法”。
費太公“釣魚”,愿者“上鉤”
1981年2月26日早晨,天津還很冷,費孝通裹著棉外套,呵著白氣,在南開大學主樓319教室的講臺上操著濃濃的吳音,講著自己的學術經歷。
這是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開學典禮,臺下坐著54名學生。這些人完全是“愿者上鉤”,是費孝通從其他學校“釣”過來的。
1980年12月27日,經費孝通等人協調,教育部終于批準南開大學設立社會學專業,同時批準南開大學從全國77級重點大學優秀大三學生中選拔學員,舉辦社會學專業班。一些機構也選派了若干旁聽生。
南開大學白紅光教授當年正是其中的一員,他當時對社會學一點不了解,認準了“費孝通是個金字招牌,他是個大知識分子,做學問跟著大學問家總錯不了”。
除了沖著費孝通的招牌之外,一些學員也有著更深的打算。
“社會學旨在詮釋現實、建設社會,所以我就是想學社會學。”當時的學員邊燕杰這樣解釋他參加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的動機。
有這樣想法的學員不在少數。當時的任課教師曾做過一次調查,有許多學生反映社會學關心現實的社會問題,比較具體,又是跟人打交道,很可能是一門有前途的學科。
社會學“黃埔一期”:像蒲公英一樣播撒種子
“‘八一年南開班’這個詞,在社會學圈子內已有了國內國際名聲。無論在北京還是南京,臺北還是香港,斯坦福大學還是杜克大學,只要你提起這個名字,朋友送給你的是羨慕的眼光。”這是時任北美華裔社會學家協會主席、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部主任邊燕杰教授在“紀念南開大學1981年社會學專業班二十周年”會議上的發言。
費孝通等人的努力沒有白費。如今,這個班被稱為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獨特的培訓班”、中國社會學界的“黃埔一期”。
從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的54名學員中走出了32位社會學教授,14位社會學系主任(或院長等職務),5位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副會長,其中不少人的影響已經超出了社會學學科。
在蘇駝看來,這更多歸功于“英雄造時勢”而不是“時勢造英雄”。“學員們讀起書來如饑似渴。”彭華民還記得,當時培訓班的學員醉心于學習,一些當時流行的電影也沒人舍得花時間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班的學員有著各自的研究領域,甚至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是針鋒相對的。他們把原因歸結為培訓班的模式——短期的應急課程。重要的不是培養關系圈子,而是像蒲公英一樣把種子撒向全國。
“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或許重新回到改革開放之初的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回到那個對今天社會學影響深遠的“種子”——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重溫學科建設的“初心”和遺產顯得更有必要。
“費孝通教授的座右銘是‘志在富民’,這也是對南開班的激勵,南開班的學術基因是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寫出有用的文章。”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思斌說,“這對純粹為文章而文章的人應有所啟發。”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