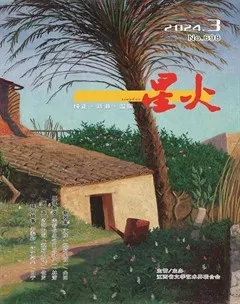四樓住了個鄭法官(短篇)

剛開完庭,庭長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庭長說:“小李,我知道你開了一天的庭,辛苦,但沒辦法,給家里打個電話,晚上遲一點回去。”我問庭長是要加班嗎,庭長說:“加什么班,我們去小鄭家。”這么一說我就明白了。上午來了一對夫妻,來告鄭法官的狀,庭長要親自出馬,去解決問題。
庭長開著私家車,帶上我,先去快餐店叫了兩份快餐。飯畢,我們驅車過去。
“我跟他們約好七點鐘的,你看現在幾點?”庭長說。
“還不到六點半。”
“時間還早,他們可能正在吃晚飯。我開慢一點,提前幾分鐘到就行。”
“早點到比較好,”我說,“她家那邊不好停車子。”
幸虧我提醒,庭長早一點停好了車,不然的話,肯定要遲到。
小鄭家在一個不像小區的小區里,巷子深得仿佛不見底,汽車根本開不進去。我告訴庭長,這里的樓房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放在當年還算高檔,現在早就落伍了。庭長說,小鄭父母是外地人,她是隨父母做生意過來的?我說,也是也不是,那邊生意不好做,她考到我們法院,她父母就跟著過來了。庭長問,他們做的是什么生意?我說,聽講是賣水果,但小鄭說現在水果生意不好做,街上賣水果的人太多了,賺不到錢。
說著話,我們已經走到了小鄭家的樓下。
庭長說:“我們先去老金家,這樣比較好,人家不會懷疑我們偏袒一方。”
然后,我們上樓,敲響了三樓老金家的房門。
上午,一個自稱姓金的人和他老婆來到北門區法院,進了辦公樓,說要找民事審判庭的庭長。那時候我剛開完庭,從審判法庭那邊過來,見到來人,問他們找庭長有什么事。男人臉皮白凈,氣洶洶地,說,我是來告狀的,先找你們庭長,庭長要是不接手,我就去找院長!
話才出口就那么咄咄逼人。我把他們領進了歐陽庭長的辦公室。
等這對夫婦離開庭長辦公室,庭長把小鄭叫了去。那時候小鄭也剛剛開完庭,連胳膊上搭著的法袍都沒放下呢。庭長與她單獨談話,談了一陣,小鄭回了辦公室。我未及與小鄭搭話,庭長又過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
庭長拿起桌上一疊三四頁紙的告狀信,抖一抖,對我說:“告小鄭的。你知道告她什么嗎?他們是小鄭樓下的鄰居,告小鄭罵人,還動手打人。你可相信?”
我笑了。我笑的是不相信。
“這封信是寫給院長的,他們不找院長,來找我。你幫我分析一下,他們是什么心理。”庭長給我出題目。
我拿過信來,一目十行大致看一遍。這白臉漢子名叫金又強,住在小鄭家樓下,小鄭家房子漏水,他找上門去,兩下談不通,小鄭不僅罵人,還跟他動手,今天來,他要求鄭家賠償他的經濟損失,并且賠償精神損失費。
“他們底氣不足,知道找院長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找直接管事的。”我如此分析,“目的很明確,就是想多撈一些便宜。”
“嗯,跟我想的基本一致。”庭長點點頭,“那么你說,我們把信收下來了,下一步該怎么辦?”
“既然抬頭是寫給院長的,我們不如就交給院長,看他怎么處理。”
“不行,絕對不行。”庭長擺手。
我問為什么不行,庭長說:“那樣動靜太大了。一個小姑娘,鬧得全院上下都知道,沒必要。在我們庭,除了你,我還要指望她呢。你們都是辦案主力啊—不就是想撈點便宜嗎,我的意思,想撈便宜,就讓他撈一點。”
這么一說,我懂了。我苦著臉,會心一笑。
庭長又說:“我跟分管領導匯報一下,匯報以后再說吧。”
匯報的結果,就是庭長主動攬下這個活,帶上我去小鄭家,做調解工作。
庭長剛才的話不免叫人發笑,“一個小姑娘”,人家小鄭已經不年輕了,只不過到現在還沒結婚,甚至還沒談戀愛而已。小鄭大學畢業,跟著讀研,之后去公司干了幾年,終于通過司法考試來北門區法院,工作也已經三四年,這么一來二去,三十二歲了。不過小鄭長相好,一張娃娃臉,溫和,看上去倒像是二十剛出頭。這樣的長相,也好也不好,從工作角度講,肯定不占優勢。在法院搞審判,長得老成一點,受人尊重。
下午一上班,庭長就給金又強打電話,告訴他我們晚上過去,七點鐘。
我們首先敲了老金家的門。
開門的,是老金的老婆,緊繃著一張胖臉,像是故意繃著,和身上緊繃的衣服相呼應,很難看。“來了。”歐陽庭長說,說得煞有介事。女人并不應答,我們便徑直往里走。穿過如過道一般的客廳,進得房間。老金背對我們坐著,紅背心,黃褲衩,這會兒側過頭來,朝我們象征性地點點頭。“來了。”庭長又說,是自我解嘲的口吻。
房間不算少,但都不大,東西堆得很亂。正不知如何落座,老金忽然站起來,說:“來來來,你們跟我去看看,看看我講的是不是實話,看看我騙沒騙你們!”幾乎沒有一點兒過渡。我們只好跟著他去旁邊的房間。
抬頭看,靠天花板的墻面果然斑駁,一塊一塊,仿如深暗的山體,有連綿之意。“還有這邊,這邊!”老金說著,又把我們領進隔著廁所的另一個小房間。這邊的圖案有點變化,不像群山,倒像是臟兮兮的河塘了。
“關鍵是這邊!”老金不容我們講話,又把我們帶到廁所門口,指著廁所里面說,“上邊!上邊漏水,漏得嘩嘩的!”
我和庭長鉆進窄小的廁所,仰頭望。一條細長的濕痕沿外露的水管而下,老實說,不至于“嘩嘩的”。
“嗯,是有問題,是有問題。”庭長節制地說。
回到房間,我和庭長在舊沙發上坐下。老金也在旁邊坐下,開始控訴。
“看到了吧?我是不是說假話?這一家,太不上路子了!前面已經出現過好幾次這種情況,漏了幾次水,我住樓下,成天就跟下雨似的!她還在法院,還當法官,我上去評理,她還跟我兇!”
庭長笑著,拍拍他的胳膊,“老金,有話慢慢講,慢慢講。我聽說,派出所這次也出面了,處理的結果你不滿意?”
老金又激動起來,“我提出少說也要賠給我兩千,你知道怎么調?調成七百,說多一百都不能給。 我當然不干!你們這次要是處理不好,我要跟她打官司,告她跟我動手!”
“她一個女孩子,弱不禁風的,還跟你動手?”庭長不笑了,已經笑不出來了,“這樣吧,我們長話短說,我先拿個初步想法,你看行不行?”
“你說。”女人站在旁邊,顯得迫不及待。
“責任是明確的,這個不用說,樓上小鄭家漏水,是樓上的責任。作為單位領導,我拿兩點意見,你們看能不能接受?”庭長看看老金,再仰臉看看女人,“第一,我叫小鄭這兩天就找人施工,把漏水的地方補上,這是最關鍵的,這個要是解決不了,一切都等于零;第二,補好了上面,就來修補你們家的墻,該鏟的鏟,該粉刷的粉刷,這個你們放心,起碼,要搞得比你們家現在這個墻面漂亮。”
“第二點不行!他們來搞,用什么爛料我也不知道,我不放心。”老金說。
“那你說,采取什么辦法?”庭長問。
“她家給我們錢,我們自己修。”女人再次迫不及待。
“這也是個辦法。”庭長說,“要多少錢,你們商量過嗎?”
“商量了,她家不同意。”女人說。
庭長問是多少,女人不言。老金翻眼看看庭長,說:“你問四樓去,你一問就知道。”然后胡亂地擺一擺手,似乎有了些許不耐煩的、逐客的意思。
樓上樓下的房間格局完全一致,連各個房間裝修的簡易程度也基本一致。
小鄭一家人早就在家里坐等了。我們進門,小鄭的父親卻坐不住了,簡單招呼一聲,突然顯出激動的樣子,站起來,坐下,又站起來。小鄭及時伸手,拉他坐下,可他剛坐下,忍不住又站起來。小鄭和母親坐在床沿上,她母親說:“小她,來領導了,你去倒水。”想一想,又說:“小她,你去倒水。”自己卻始終坐著。
小鄭扭臉對半截櫥邊一個正在擺弄手機的大小伙子說:“你去,幫我們領導泡茶。”
“你支派你弟弟干嗎?”小鄭母親說,“你去,小她,你自己去。”
開始我沒聽清她是如何稱呼自己女兒的,不明白“小”字后面跟的是個什么字;幾遍聽下來,突然大悟,原來是“小她”。
這個稱呼,令我感覺奇異。小鄭不是有名字嗎?雖然名字太過普通,可能會被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同名者淹沒,但三十多年下來,作為母親,也不至于連個“桂花”都喊不順口,偏偏要叫她“小她”!
庭長似乎司空見慣,就像小鄭對之全然不在乎一樣。雖是初次登門,初次與小鄭父母見面,但庭長一句客套話都沒有,坐下來便直奔主題:“大哥,你坐,坐下來,我們靠近一點,商量商量。”
這話是富有感染力的,距離頓時拉近了,像一家人。老鄭個頭不高,紫黑著一張瘦削的臉,既粗獷又蒼老,受寵若驚道:“我坐,我坐。”
小鄭挨著她母親,平靜地坐在床沿上,一直沒動。她弟弟去為我們沏了茶。小鄭的母親,四方的臉,如同小鄭父親一樣的黑,嘴里一直絮絮叨叨,只是聽不清在說什么。
小鄭父親沙啞著嗓子,向我們介紹情況。
說三年前,他們一家從河南搬過來,買了這套二手房。這房子質量太差了,老是漏水,幾次維修都修不好。一漏水,老金就上門來,已經賠過三次錢了,這是第四次。“我說要幫他修,他也不愿意,就是伸手,死要錢!第一次賠兩千;第二次找派出所,賠了九百;第三次也找派出所,賠了八百。”老鄭說。這次又找派出所,派出所的老吳上門幾次,說這次比上幾回的損失都小,賠六到七百就差不多了。老金雖然不很愿意,但也找不出推翻的理由。老鄭眼睛一閃,說:“可不知咋的,他知道我女兒是法院的法官了,起先一直是跟我打交道的,現在不干了,一下就把我甩到一邊,專找我女兒的茬!”
“怎么找的茬?”庭長問。
“上樓來,也不找我,專找桂花,開口就要八千,不給,就要去單位,告狀!”
“就這么大點事,責任也明確,他告什么?”庭長說。
“他那天上樓,桂花在洗澡,他也不管,一勁地捶門,桂花洗了一半就穿衣服出來,頭發還滴水,就問他講不講理,把他往門外推。本來這事過去了,他也沒啥可說的,一聽說桂花是法官,就又提起這事,說桂花推了他,打了他。”老鄭說著又站起來。
“是個無賴啊!”我不由得開口。
“別瞎講小李!鄰里糾紛,哪有無賴!”庭長不看我,只看著老鄭,“他說賠償的數額都跟你們商量了,怎么商量的?”
“哪商量了?開口就要八千,不行就要告狀。就是這樣!”
“八千是不可能的,損失就這么大。大哥,我只和你說說利害關系。”庭長語重心長,拽一拽老鄭的袖口,“鄭桂花雖然年輕,可在我們法院,她是辦案主力,一年要辦兩三百件案子呢。她承辦的案子,債務的,房產的,幾百萬、上千萬的都有,你說你們家這個小糾紛對她來說算什么?我是考慮吧,她這兩年都是市先進,又在入黨考察期,這個時候鬧一場官司對她有什么好?不管怎么說,錯在我們,是吧?人家住樓下,沒有錯。真要鬧起來,為了一點鄰里糾紛,對鄭桂花造成影響,你說值得嗎?我看是不值!常言說,三人成虎。本來沒有的事,大家一傳,倒傳得跟真的一樣了。”
“可他也不能獅子大開口,要這么多呀!”老鄭像是有所領悟。
“大哥,大嫂,你們給一個心理底價,你們看能給多少,我和小李下去談。”
“六百五!”女人看上去像是全無主見,卻搶先發話,“屁股大的一塊地方,修一修,能花幾個錢?派出所老吳說了,六百就夠了……我們多給五十!”
“大嫂,你這就叫沒誠意了,相差太大,談不攏啊!大哥,你是明白人,你說呢?”
老鄭磨著牙,下巴頦左右動得很夸張,良久才說:“我看七百只多不少。”
“七百肯定不行!”庭長態度堅決,“真要是打官司,還要找人做鑒定,光是鑒定費,起碼也要上千了。”
“上千,那也不能就我一家付呀!”老鄭戇戇地說,似乎清醒了一下,又道,“那就……那就八百……還是九百?”
“你敗家呀,敗家呀……”女人痛苦地發感嘆。
“大哥大嫂,你們聽著—”庭長站起身,伸出兩個手指頭,作出決斷,“我和小李現在就下樓,我們按這個數字談,兩千。”
我們和小鄭交換一下眼神,及時抽身。這個眼神交換了等于沒交換,小鄭是沒有態度的,一如她那張娃娃臉,竟是懵懂無措的樣子。而她母親,這時卻轉換了攻擊目標,一迭聲地哀嘆:“都是因為你呀,當什么法官呀,遭罪……”
回到三樓,談話繼續。作為事后的復述,我現在已經沒有欲望再去敘寫與這對夫婦交談的經過了。這一輪的談話,只有一件事情或可留下一筆。
何事呢?老金居然拿出一份起訴狀,以表明他打官司的決心。而這份三頁紙的起訴狀,即刻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不為別的,只為其中的字跡。
這份手寫的起訴狀,抬頭“民事起訴狀”幾個字較大,是宋體,橫細豎粗,寫得十分規整,不細看,以為是印刷品;接下來“原告被告”以及“訴訟請求”,則是仿宋體,一筆一劃,很見功力;然后“事實和理由”的長文,則是漂亮的行書字體,自由放松,但每一筆每一劃都仿佛有其出處;到末了,“具狀人”一欄以及時間,又回到了仿宋體。如果說上午在庭長那兒看到的告狀信,單一的行書字體尚會引起人的誤解,以為是別人的代筆之作,那么看到這一份仿佛是在練習硬筆書法、差不多就是賣弄鋼筆字的起訴狀,就不能不叫人驚嘆,這書寫者真是水平夠高,也實在是閑得無聊了。
“這是你寫的字?”我忍不住問。
“我寫的。”老金說。
“這字寫得真漂亮!”我由衷地夸獎。
“那時候我在里面,時間多,沒事干,成天練字,就練出來了。”老金顯出十二分得意的神情,徹底放松了警惕。他說的“里面”是指坐牢。
講這些的時候,我以為他老婆會顯出羞愧之色。沒有。不僅沒有,站在他身邊,一臉自得,似乎為有這樣一個丈夫,頗顯自豪呢。
除了這一節值得記錄,還有一點,也可以順帶一筆。老金說,上回房子漏水,他沒找老鄭,直接上四樓,揪住施工隊那個小頭頭,一下就把對方鎮住了。“我叫他停工,他小子還不愿意停,說簽了合同,不能停。我說,是老子說了算,還是你他媽的合同說了算?!他長得比我橫,光憑我,肯定搞不過他;我是帶著兩個朋友上樓的。我讓他有個數,看我們誰能搞過誰!”
庭長默而不言,我則目瞪口呆。
再上樓,到小鄭家,小鄭的母親正在哭,一抽一抽的,兩行淚還留在黑臉膛上,在燈下閃亮。我突然想到一個叫東施效顰的成語。這個念頭出現得很突兀,有點冒失。
“大嫂,我們就事論事,就是一點小糾紛,不算大,別哭,別哭。”庭長勸道。
“小她是法官,小她是法官又咋啦,就該受人氣呀……”她反復叨嘮著,哭腔里的這句話如同挽歌,聽起來竟有點瘆瘆的。
老鄭站在屋子中央,似已等候多時,說:“我就知道你們談不成,他家那樣,談不成!談不成就算!他不是要打官司嗎?他打好了,我等著!”
“這不行啊,大哥,你要冷靜!”庭長一口否定,“要不是為了鄭桂花,我們就不會上門。我們來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問題。她年輕,不能因為這個小糾紛,耽誤了她的前程。”
“前程!可他家……他家欺人太甚,現在都欺到這一步了!”
“屁股大的一塊地方,死要錢。唉,我命苦啊—”女人又不合時宜地抽泣起來。
“大嫂你別這樣說,這樣說會引起更大矛盾。”庭長正色道,“兩個房間都有,都是一大片,廁所也有,都不小呢。”
“不小什么呀,他拿了錢也不會修的。這種人,我知道!墻上的印子,還說不定是上幾回的呢!”老鄭說著,扭臉去勸哭哭啼啼的女人,沒有效果,有點難堪。老鄭說:“兩位領導上門來做工作,你們的好意我領了;可這一家,你講多少也沒用,他們就是為了錢……這樣吧,作為一家之主,我做主,就定一千,他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敗家呀,你敗家呀……”女人又重復先前的話。
庭長說:“大哥,你還是繞不過這個彎子。他提八千,那是扯淡;可他提兩千,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我想往下拉,也拉不下來……這樣吧,我就在一千五到兩千之間去做工作,就按我說的定了。”
“不行啊—不行啊—”女人及時哭道。
“我把利害關系都跟你們講透了,大哥,你是開明人,我講的意思,你應該懂。”庭長轉臉向小鄭,又說,“小鄭,你拿個主意。你在單位辦案子,果斷得很呢,怎么在家,一句話也不講了?”
小鄭躲過庭長的眼神,低了頭,依然一言不發。
這中間,庭長又談了許多,正面的反面的,反復做工作,如同在老金家我們反復講廢話一樣。很多廢話是不能不講的;同樣,明知道有些工作做了等于白做,還是要做。
庭長再次喊我下樓。我們出門時,身后傳來老鄭沙啞的聲音:“這種人家!干什么呀,搶錢啊?!”
按小鄭的歲數,她應該是獨生子女;我比她大十來歲,連我都是,她憑什么不是呢?可她有一個弟弟。有一個弟弟不算新鮮事,這樣的家庭絕然不少;但有一回,我無意中看到小鄭的一份履歷表,在“家庭成員”一欄中,除了填寫父母和弟弟,她居然還填寫了一個姐姐,在“工作單位”一欄里,填寫的是“失蹤”。
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同在一間辦公室,聊天方便,所以我刻意與她閑聊,方才知曉早前她還不止有一個姐姐,而是兩個。大的沒養成,幾歲就死了;第二個長到十來歲,跟著父母外出做生意,失蹤了,找了兩年也沒找到。父母一心想要男孩,生小鄭的時候,一看是個丫頭,就動了心思,想把她丟棄掉。丟了兩次,沒丟成,都被派出所民警抱著找上門,送回來了,還批評得不輕。父母不甘心,繼續生。又生了兩個,果真都是男孩。大弟弟前幾年拿了個駕駛證,開車給人運貨,因為連夜駕駛,在路上犯困,結果車毀人亡。現在這個是小弟弟,才剛二十歲,成績不好,沒有工作。
也就是說,父母最不待見的就是鄭桂花,可她在家里又最有出息。這很矛盾。雖然矛盾,但在父母眼里,她已經成了“小她”,是習慣成自然了。
聽她平淡地敘述,我仿佛進入到另一個生活圈子里。雖然這另類生活并不陌生,但發生在小鄭身上,我還是感到驚詫。
三樓四樓,我和庭長就這么反反復復,起碼跑了四五個來回。時間在我們的腳底和嘴皮子上迅速流逝,不覺已將近十點半。但是,進展不大。
老金夫妻的回話甚是模糊,兩千元仿佛也能接受,但仍在提八千,有得隴望蜀的試探之意。此間,老金的老婆反復強調,說既然她是法院的,還在乎這幾千塊錢嗎?老金更是得寸進尺,索性問起小鄭的工資,說她每月拿不到一萬五,起碼也能拿到一萬吧,她還在乎這點錢?聽此言,我幾乎瞠目結舌。庭長只好說,哪能呀,我都拿不到,何況是她,剛參加工作,你把我們的收入估計得太高了!
至于老鄭這邊,經我們反復勸說,曉以利害,老鄭終于咬了牙,說:“看在兩位領導的份上,一千五,我答應一千五,多一分也沒有!”而小鄭的母親,像是剛剛學到了一個新詞,哭訴的內容也變了:“搶錢啊,搶錢……”
幾個小時,小鄭始終坐著。這個晚上的小鄭,在我眼里完全換了個人,無聲無息,全無主張,像一截木雕。
庭長打算再下樓去做最后一次嘗試。老鄭決定跟我們一同下去。庭長想了想,說也行,爭取一次把問題解決。又說,最好把錢帶上,當場訂協議,干干凈凈。小鄭母親立刻“不行啊不行”地喊,只是坐著不動。
老鄭扭頭瞪她一眼,匆匆忙忙地打開櫥門,取了錢,跟我們下樓了。
卻不料,剛進門,還沒坐下,兩個男人發生了沖突。
正走在金家廁所和房間的過道處,我和庭長走在前面,老鄭跟在后面,老金也落在后面。就聽得老鄭說:“老金啊老金,你真是算一戶!人說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你相反,你專吃窩邊草!”老金說:“我吃你草,你那幾根鳥毛還夠我吃?!”老鄭說:“不夠你吃,你還吃得歡呢!”然后,兩個人突然就動起手來。待我們聽到動靜回頭看的時候,老金已經把老鄭的手腕反剪住,像擒拿格斗的老手,眨眼之間就將對方制服了。
“你們倆干嗎?”庭長返身過去,橫在他們中間,拉架。
“他嘴里不干不凈,還跟我動手!”老金并無松手的意思。
因為有庭長的幫忙,老鄭狠甩幾下胳膊,掙開了,說:“我就是拍你一下肩膀,跟你開個玩笑,你就跟我動真的!”
“誰跟你開玩笑!都要打官司了,還跟你開玩笑!”老金白著一張臉,轉向庭長,“我說的吧,他們一家人都喜歡動手動腳,你們還不相信!”
“你是小老弟,我憑什么不能……”
“算了算了,誰跟你扯!”不待老鄭說完,老金不耐煩地說。
好歹把兩個人拽進房間,安頓下來。庭長話入正題,說雙方現在所談的賠償數目已經很接近,時間也不早了,我們快刀斬亂麻,早點把問題解決掉。
老鄭硬生生地說,人家歐陽庭長親自來調解了,我高姿態,一千五,多一分也沒有。
老金說,我也不跟你談七千八千了,湊個整數,就兩千,少一個都不行!
老金的老婆站在老金身邊,繃著一張胖臉,明顯是故意繃著,像是聲援。
雙方都是犟脾氣,拉緊了弓,就這么僵持著,都沒有讓步的意思。
庭長說,時間真的不早了,你們都要有點誠意,啊?
在我聽來,庭長這話說得,一點勁道都沒有。
老鄭這時站起身,很主動地從褲子口袋里掏出錢來,一小沓百元鈔票,兀自點著,像是對庭長言談的回應。大約是多出兩張,他將那兩張單獨折起,隨手放進了襯衣口袋。“一千五,我說了,多一分也沒有。”他強調說。
老金看也不看,只冷哼了一聲。
看著他點錢,我一點兒都不抱希望。幾個小時下來,我們的“強弩”早已成了“之末”,看來,我們只能半途而廢打道回府了。
眼看著山窮水盡,調解即將陷入絕境,關鍵時刻,老金的老婆亮出了奇招。
就見她猛一抬手,照著老金的脖子就是一巴掌,脆生生的。
這一巴掌來得太突然了,差不多把我們都打懵了。
“你別死犟了,人家法院領導都來了,你還死犟!你聽我的!”女人居高臨下,下命令似的看著老金。后者抬臉,表情異常麻木,是一副愿打愿挨、司空見慣的態度。女人接著道:“加一百,一千六,討個吉利數字!”
“我說了,一分都不能加,一分都不能加!”老鄭說。
庭長仿佛于黑暗中突然見到一線曙光,沖著老鄭,嚴肅地說:“老鄭,你聽我的,加一百就加一百,凡事向前看,我們早點把問題給解決掉!”
老鄭本能地握著手里的錢,似在抵抗,庭長又說:“剛才我不都跟你說啦,為了鄭桂花的……嗯,前程。”
女人像是嗅出了某種氣味,立刻接話:“老金都答應讓四百了,你憑什么不答應讓一百。人家庭長也辛苦,都來幾個小時了。你聽庭長的,為了你家小她的前程嘛!”
這么說著,女人竟伸出雙手,抓住老鄭握錢的那只手,將他的手指頭一一掰開,把那一沓錢抽過去。緊跟著,她出人意料地又伸出一只手,幾個手指頭迅速探進老鄭的襯衣口袋,老鄭尚未反應過來,那折起的兩張鈔票已經到了她的手指間。她拽出一張,塞往另一只手里那一沓鈔票,將剩下的孤零零的一張,遞給老鄭,但老鄭尚處于驚愕之中,她用食指和中指夾住那張鈔票,從容地伸向老鄭的襯衣口袋,塞了進去。
“這不,簡單得很!問題不就解決啦?”她說。
這一連串的動作,把我看傻了。
后續為雙方訂立協議、叫雙方簽字,都由我來操作。這中間,老鄭和老金仍在杠嘴,庭長則在空談“鄰居好賽金寶”的家常道理,只是那女人,老在我旁邊干擾我的書寫:“寫這玩意干嗎,多費事,又不能當飯吃!付過錢不就行啦?”
這事發生在六年前。我至今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離開小區的時候,我和庭長都有點發懵。我們討論了幾句女人甩向老金的那一巴掌,然后都噤口,像一對寒蟬。那巴掌脆生生的,完全在我們意料之外。
六年后我舊話重提,是因為,這兩天法院又有了新的任命,鄭桂花當了庭長。
她進步的確是快,這與她的綜合素質有關。相比之下,雖然三年前我和她同時提了副庭長,但這一回,她先上了個臺階。我自認絕非小肚雞腸之人,不會在這個問題上糾結,上臺階就意味著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我想表達的意思是,那天晚上小鄭茫然無措的神情,在我眼里是那樣的陌生,仿佛完全換了個人,與她在辦案中干練、精準而又不失溫和的作風、態度比較,簡直判若云泥。一個人,怎么會因為某件事,就變成另外一個人呢?我還想,如果那個晚上調解不成功,事情被我們搞砸了,老金和他女人接下來大鬧一場甚至幾場,攪得天翻地覆,那么小鄭,還會在三年前和我一道提任副庭長,并在眼下升任庭長嗎?
看來無論是誰,在他(她)的周圍,都有一個看得見或者看不見的“場”。
李敬宇,法院工作者,中國作協會員。在《中國作家》《花城》《清明》《長城》《北京文學》《十月》《星火》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100余篇,共200余萬字,部分被選刊選載。發表并出版長篇散文《老浦口》、長篇小說《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