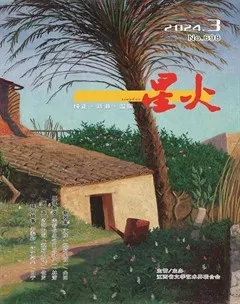消弭的海(短篇小說)

不出所料,一踏上這條路,阿榕的心緒就亂了。
午后的天陰沉沉的,把人也染陰郁了。阿榕忐忑地望了望前方。裹著一層黃泥的柏油路疲軟地伸向遠處,讓人感覺黏糊、骯臟、心煩。自從聽說那女人的消息以后,阿榕返校的路上就沒有了歡樂。往日嘻嘻哈哈地追逐、嬉戲變得索然無味;田野里細皮嫩肉的黃瓜寶寶、豆角須兒、青菜芽兒則像妖嬈過了頭的小女生,不再有趣;嶺上的青松、卷著葉子的茅草也失去了搖曳的姿態。世界是一副萎靡生厭的樣子。阿榕踢著路上的石子,慢慢地走著,故意遠離那些在路上嬉鬧不已的小伙伴們。新穿的小白鞋很快蓬頭垢面,如同他的心情一樣。
同伴里大概有人已經知道了那女人的事情。他們有時候會故意撇下阿榕,落在后面嘻嘻哈哈地討論著什么,或者興奮地朝著某個地方指指點點。他們看阿榕的眼神變得有些怪。這種眼神阿榕從小就從村里人那里感受到了。村里的人也喜歡對著阿榕兄妹指指點點,用這種復雜的眼神看他們。阿榕很早就從他們的眼神里,感受到了有些憐憫有些嘲諷又有些瞧不起的意味。那么多年,他已經習慣了。他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女人。
下了一個斜坡,來到一片開闊的地方,兩邊是大片的田野,一塊塊的田地連著,遠看像一塊塊不規則的畫布,有的種著瓜果蔬菜,有的丟荒了,長滿了黃綠白的小花小草。陰沉的天空飛過幾只嘰嘰喳喳的鳥雀,領頭的那只邊飛邊回頭,后面的幾只碎碎地叫著,有些驚慌地撲騰著翅膀。那肯定是鳥媽媽帶著孩子外出覓食了。阿榕嘆息一聲,連一只鳥都不會放棄自己的孩子,何況是一個會哭會笑的人呢。那女人竟舍得丟下他們兄妹三人,十年不聞不問。最可恨的是,消失十年后,她又回來了。如果她死了,跑了,或者失蹤了,那也就算了,他們會把她當成一個遠去的念想。可是,她又回來了,竟然就在他上學的路上,是的,竟然就在他上學的路上,一個離鎮上很近的地方,和一個男人租了一片地,公然過起了夫妻般的小日子。阿榕做夢也想不到她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而且,大半年過去了,她像一塊沒有感情沒有記憶的石頭一樣,依然沒有去看他們一眼。這感受,如同一個愈合的傷疤,再次被殘忍地撕成血淋淋的傷口。難道她從來不想我們嗎?難道她那么容易就忘掉曾經屬于她的三塊肉嗎?那她為什么要生我們?想到這里,阿榕好想大哭一場,他覺得自己活得太卑賤,太憋屈了。
阿榕忍不住抬頭望向那個望了無數次的地方。不遠處,一排藍頂白墻的板房矗立在田野里。空曠的田野里,這樣的板房還有好幾處,它們像火柴盒一樣裝點在青黃紫的蔬菜中間,好像很喜歡孤獨的樣子,就那么冷冷清清地矗立在那里。阿榕對那些房子很好奇。他牽掛的那排板房,就在一片黃瓜一片豆角一片小白菜的里面的里面。無數次了,阿榕只見過一兩次人活動的身影。也許是棲身田野深處的緣故,板房也變得有些黃綠了,像是染上了大自然的顏色。
有人告訴過阿榕,那女人就住在那排板房里。
阿榕心里已經模糊了那女人的樣子。她離開的時候他才五歲。他只記得她的臉圓圓的,嘴巴有點翹,身材很粗壯。她離開以后,十年的風霜雨雪已經把她留下的痕跡沖洗得干干凈凈。媽媽成了這個家刻意回避的話題,就像某些生活禁忌一樣,誰也不愿意觸碰。兩歲多就被拋下的小妹,看見她的朋友和媽媽在一起時,總是躲開別人的目光,一句話也不說。也許她根本就認為貧窮的家不應該有媽媽。有朋友問過阿榕,你媽媽呢?阿榕說,死掉了。他不愿意別人知道她的存在。
她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女人呢?拋家棄子,麻木不仁,鐵石心腸,愚不可及,不可理喻,阿榕想到那女人時總會想起那些別人給她的標簽。他有些排斥這些字眼,但又想不到更合適的字眼替代它們。他的內心其實更幽深更復雜。他曾經聽到父親跟別人說起過那女人,父親悲憤地罵她是個瘋女人。性情古怪的父親沉默寡言,一個人養大了阿榕兄妹三人。歲月的風霜過早地吹白了他的頭發,吹皺了他的臉。如今的父親目光呆滯,平日除了做事,就是酗酒,醉酒后的他常常死狗一樣蜷縮在路上,直到有人把他拖回家。但阿榕不恨父親。阿榕恨那女人。阿榕繼承了父親的看法,認為那女人就是個瘋子,一個無法理喻的女瘋子。
越來越近了,從柏油路望向板房,中間隔著一大片高高低低的瓜果蔬菜。這里的瓜果蔬菜特別豐富,也特別有生氣。像女人一樣披著青色長發的豆角;綠得發黑的葉叢中,青黃紅綠一團團簇擁著的番茄;驢球一樣垂下來的黃瓜;喜歡挨挨擠擠,又害羞得只露半個紅臉的蘿卜;辣椒樹上則像吊滿了形態各異的體操運動員,有的倒立,有的旋翻,有的懸垂,有的屈伸。阿榕每次走到這里都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至于親近感從哪里來,阿榕大概知道,但他不愿意去想得太清楚。上學放學的時候,他曾經很多次看見種菜的人。一個女人,穿著寬松的深色長衣長褲,有時蹲在低矮的辣椒地里拔草,有時擠在濃密的番茄葉中掐尖,有時彎腰翹著大屁股摘黃瓜,唯一不變的是她的頭上不管天晴下雨都戴著一頂斗笠。阿榕不知道她和她是不是同一個人,還是這些菜農都喜歡這樣打扮。他從來沒有見過她的臉。不知她是專注于工作,還是故意不給他看。有幾次,阿榕故意在路上弄出很大的動靜,比如突然用腳跺響地面,或者故意大聲地喊幾下。
“啊啊啊—”
“哦哦哦—”
那菜農不是稻草人一樣無動于衷,就是只側側頭,從帽檐下匆匆向外瞥一眼。阿榕根本來不及看清她的臉。有一兩次,那菜農竟躲著似的,聽到聲音就往菜畦深處走,直到完全沒了影子。這時候,阿榕的胸口咚咚咚地跳得很快。有一回,他的鼻子陡然發酸,突然好想大喊一聲那人,可張了張嘴又不知該喊什么。他傷心地跑回學校,躲到宿舍后面的苦楝樹下,大哭了一場。
阿榕感覺那菜農就是那女人。
只有那女人才會這樣冷漠無情、難以理喻。
阿榕常常想,日月萬物一定看見了那女人的無情,也看見了他的卑賤。那種憤懣的情緒在阿榕心里久久不能釋懷。此后的兩周里,阿榕在周末上學放學的路上,經過那片菜地時,他仰著頭,加快了腳步,眼睛故意瞟都不瞟菜地一眼。所有人、所有瓜果蔬菜都應該看見他的不滿了吧?阿榕似乎在期待著什么。菜地里寂靜無聲,只偶爾傳來幾聲細碎的蟲鳴,瓜果蔬菜像局外人一樣吸吮著肥沃的養分,長得又肥又綠。阿榕驀然生出了一股憤怒的情緒。他望了望菜地,又望了望柏油路,沒有一個人影。他慌張地跳進路邊的辣椒地里,像滿足了一種奇怪的心理似的,使勁地踩踏著一片剛剛掛果的辣椒樹。看著折斷的辣椒樹像士兵經歷一場戰爭一樣一棵棵倒伏在地,白色的小花和炸裂的辣椒血肉模糊地印在黃色的泥土里,阿榕蹦到嗓子眼的心升起一種復雜的快感。他想到了那女人捶胸頓足的樣子。
一周后,阿榕再次經過那片菜地時,忍不住忐忑地望了望那片辣椒地。踩踏過的辣椒殘骸早已不知去向。新鮮的泥土上,已經重新栽上一列列整齊的辣椒秧,稀疏的幾片嫩葉在晚風里輕輕搖擺,似乎為擺脫了萎蔫的狀態而興奮不已。阿榕的心被這小小的葉片晃動了一下。他急忙扭過頭,腦子里浮現那女人補種辣椒秧的場景。他的心情復雜了起來,有些欣慰,有些失落,又好像有些愧疚,說不清的感受。
天越來越暗了。走到通往板房的小路時,那個像蟲子一樣蠕動在阿榕心里的念頭越來越強烈了。他站在路口,焦慮不安。那蟲子的叮咬讓他痛苦不堪。阿榕重重地喘著氣。最終那蟲子取得了勝利。阿榕突然屏住氣,忐忑地朝板房走去。
小路比想象的要寬,也想象不出的泥濘。板房越來越近。阿榕的胸口咚咚地撞著。板房周圍沒有一個人影。靠近板房的時候,阿榕發現番茄地旁邊的空地上長了一片茂盛的艾草。他竟做賊心虛似的趴了進去。藍頂白墻的板房神秘地呈現在眼前。近了看,白墻已經不白,墻面像涂了一層黃綠色的穢物。板房前面擺滿了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東倒西歪的農具,胡亂堆積的柴火,幾只大得夸張的棕色塑料桶,銹跡斑斑的鐵牛,遮著灰色塑料布的壘成小山似的青竹竿,一堆顏色發黑的薄膜,露出一只水瓢和半個蔫皮球的斗車。地上的雜草里還躺著很多垃圾,塑料袋,礦泉水瓶,農藥瓶,肥料袋。一樣樣像從災難里逃出來似的衣衫襤褸,形態恣意。
阿榕數了數,板房有三個窗,應該是三間房。房門閉著,沒有一點聲音。阿榕有些失望。觀察了一陣,阿榕爬起來,裝成路人的樣子,慢慢走近板房。他似乎聞到了那女人的氣息。想想這就是那女人每天生活的地方,他的頭皮麻了一下。恍惚中,腳下咔嚓一聲,阿榕低頭看了一眼,一根干枯的樹枝被踩成了兩截。阿榕噓出一口氣。“嗚嗚嗚—”板房里突然爆發出一個孩子的哭聲,“媽媽—媽媽—”正當阿榕不知所措時,一顆腦袋從窗戶的防盜網后面伸了出來。“媽媽—媽媽—”一個五六歲的男孩,伸長了脖子哭著朝外面喊。從男孩嘶啞的哭聲,阿榕聽出他之前應該已經哭了蠻久了。男孩伸頭看見阿榕,愣了愣,又膽怯地縮了回去。一種復雜的情感涌了上來,阿榕忍不住追了上去。透過防盜窗,阿榕看見男孩縮在一只到處漏海綿的黑色沙發上,還在哭著喊媽媽。男孩黑黑瘦瘦,小圓臉,翹嘴巴,寬松的衣領上兩塊突出的鎖骨因為哭泣一聳一聳的。這不是小時候的弟弟嗎?阿榕突然明白了一個事實。胸口像堵著什么一樣,阿榕喘不過氣。其實早已想到,可當事實突然袒露在眼前,他還是很難受,也很生氣。阿榕感覺又被世界拋棄了一次。他緊握的拳頭使勁地搓著墻面,幾道粉紅的印跡留在了白色的墻面上。他忍不住,一滴淚滾了下來。
阿榕很想離開這里。
阿榕望了望天。陰郁的天空映暗了大地,一切都顯得那么憂傷。阿榕又望了望眼前的草木蔬菜。你們有媽媽嗎?挨挨擠擠的草木蔬菜一片沉默。阿榕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弟弟,想到了小妹,他們五歲、三歲、兩歲就失去了至愛的人,老天一定也會憐憫他們吧。十年的空白如同一個黑洞,將那個念頭孵出無數幼蟲,使勁地撕咬著阿榕。越想離開,撕咬就越瘋狂。他堅定了留下來的心。
男孩還在兀自哭著。阿榕看了一眼屋里的陳設,一張破舊的沙發,一臺落地扇,中間一張小圓桌,桌上罩著紅色菜罩,里面似乎罩著剩飯剩菜,幾張塑料凳,一張鐵架床,上鋪擺著一臺灰蒙蒙的彩電,下鋪的電線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衣服,房間最角落是疊放的籮筐和堆積的紙盒,地面的空隙上還散落著幾只臟兮兮的布鞋涼鞋,似乎已經被遺忘很久了。一股心酸涌了上來,阿榕不知道是因為男孩,還是因為這個破敗的家。
“你媽媽呢?”阿榕抓著窗條問。
男孩不哭了,瞪大眼睛緊張地看著阿榕。
“你爸爸媽媽都不在家嗎?”
男孩還是不說話,見阿榕盯著他,害怕地躲進了沙發后面。板房又回到了靜悄悄的狀態,像沒有人一樣。
阿榕不甘心離開。他腦子里浮現出那個戴著斗笠穿著深色長衣長褲的女人,心里像被什么東西撓著,酥酥癢癢的。
阿榕又躺回了那片茂盛的艾草叢中。臉兩側,異化的艾草像參天大樹一樣聳入天空,幽香的味兒隱隱傳來。一小塊天空陰郁蒼茫,偶爾飛過悠閑的小鳥和蜻蜓。周圍一片沉寂,細微世界的聲音緩緩流過耳際,心臟咚咚地撞擊,小蟲窸窸窣窣地爬行,番茄葉耳鬢廝磨地細語。艾草的幽香和泥土的味兒愈來愈濃。這一切多么美好。阿榕又感受到了那女人的氣息。他羨慕這些草蟲,它們能夠每天跟她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也羨慕這些瓜果蔬菜,它們每天都能得到她的呵護。想到這些,阿榕感覺自己也渺小了,變成了地上的一棵小草,或者草葉上的一只小甲蟲。艾草鋸齒狀的葉片像那女人伸出的溫暖的手,一陣酥酥麻麻的感覺襲來。阿榕沉浸在這種酥酥麻麻的感覺里,如醉了一般。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阿榕被一陣突突的異響驚醒。睜開眼,天已經黑下來了。板房前已經亮起了燈,白色的光照亮了一小片地方。一臺亮著燈的三輪車停在板房前的空地上,一男一女正從車上卸著東西。阿榕盯著那女人,心跳突然急促起來。燈光下,摘掉了斗笠的女人格外地黑,滄桑的圓臉,嘴巴大而翹,一身深色的長衣長褲。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阿榕鼻腔里陡然一酸,眼淚忍不住滾了下來。終于見到她了。太多的過往、太多的恨意、太多的委屈像熔巖一樣一下涌了上來。阿榕翻過身,望著深沉的天空,任由淚水從眼眶漫過臉頰。他弄不清自己為什么哭泣,似乎為了她,又似乎為了自己。他內心猶如經歷了一場夜晚的暴風驟雨,激烈,泛濫,搖搖晃晃。他想大聲哭出來,卻又硬生生憋了回去。萬物靜寂,天空像一只深沉的大眼望著阿榕。他努力從暴風驟雨里掙脫出來。他不想錯過這個期盼已久的時刻。
禿頂的男人神態焦慮,單手拉過一只籮筐,有些暴躁地扔在地上。“到底是誰收錯了?”男人又抓起一只泡沫箱重重地摔在地上,嘴里喋喋不休。“我記得我只收了三張一百,每一張都認真看過了,不可能有錯啊。”男人停下來盯著女人,僵硬的右肩奇怪地聳著,攤開的左手像一條萎靡不振的蛇,有氣無力地訴說著主人的無奈。“唉—這一天又白干了。”男人的聲音小了下去,白天的遭遇似乎已經耗掉了他所有的力氣。女人一聲不吭,從車上默默抱下幾袋很沉的東西,又像鴨子一樣蹣跚地抱進房里。男孩也從板房里出來了,跟在女人的身后嗚嗚地哭著叫媽媽,一只手時不時去扯女人的衣角。女人回頭抖了一下身子,甩掉了男孩的手,喘著粗氣說:“不哭了阿寶,媽媽卸完東西就做飯了。”男人站在車尾,茫然地看著女人和孩子,似乎還沒有從頹喪中緩過神。女人卸完東西,熄了車燈,帶著孩子走進了明亮的屋里。男人最后一個跟了進去。進門時,阿榕從明亮的背景里,看見了男人右邊那只空蕩蕩的袖子。
原來男人殘了一只手。
阿榕心里咯噔一下,說不清什么感受。阿榕聽親戚說過,這個男人和媽媽以前在一個工廠里打工,后來媽媽被他拐跑了。阿榕恨這個男人。阿榕曾經無數次用最狠毒的語言詛咒他,并幻想自己的詛咒在他身上得到了應驗。可現在男人活生生地站在眼前,并且殘了,他心里卻說不出地復雜,恨不起來了。不僅恨柔軟了,還對男人生出了一些憐憫,再想一想,甚至還萌生出了一些期待,希望男人能像新聞上那些身殘志堅的勇者一樣正常地生活,脾氣也再溫和一點。是因為那個女人嗎?阿榕說不清楚。
板房里傳來了鍋碗的聲音。
過了一會,又傳來了男人絮絮叨叨的斥責聲,接著是女人低低的回應聲。男孩又哭起來了。
阿榕心里酸酸的,沉沉的。他從艾草叢里爬起來,悄悄往外面走。黑暗中,女人黑瘦的圓臉映在他的腦子里,越來越清晰。阿榕邊走邊回頭,望向那排亮著昏黃燈光的板房,心里涌上莫名的悵然和不舍。田野里,一畦畦的黃瓜、豆角、番茄默默地注視著他。一個趔趄,阿榕掉進了路邊的水溝里。他趴在田埂上,冰涼的水沿著褲管迅速流進了他的身體。他腦袋里嗡嗡地響著,全身感覺酸軟無力。他多希望那女人突然出現在他的身后,看見他狼狽的樣子,然后像小時候那樣心疼地呼喚他,將他扶起來。他趴在那里,靜靜地等著聲音出現。然而,除了唧唧的蟲鳴,什么聲音也沒有。
阿榕最終自己爬了起來。
借著朦朧的月光,阿榕繼續往外走,匆匆地。晚風拂面,阿榕的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到了大路,他竟難以自抑地痛哭起來。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想哭,似乎大哭一場就能撫平所有的傷痛。他加快了腳步,奔跑起來。夜色朦朧,風呼呼地吹過耳際,阿榕使勁地跑著,越哭越大聲。黑魆魆的柏油路,模糊不清的田野,影影綽綽的樹木,紛紛拋到了身后。阿榕突然模糊地感覺到自己有些理解那女人了。淚水似乎從他心里消弭了一些東西,又彌補了一些東西。阿榕朝著光亮的地方越跑越快,越跑越想哭。最后,他忍不住一路跑,一路號啕起來,“媽媽……媽媽……”
佐羅,80后,廣西臨桂人,中短篇小說愛好者。作者系首次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