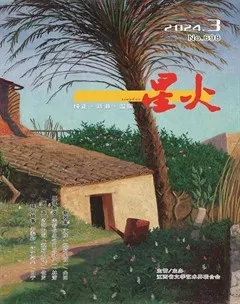去泰和,過文學年

一
魏琦在路邊招手。她先一步到達這里。大巴車速慢下來,停到路邊的一棵古樟下,驛友們紛紛下車,眼睛掃向眼前這片闊大的灘涂,或仰頭看頭頂樟樹屈曲的巨大枝干。從入住的蜀口洲生態島到這里,大約兩小時車程,有人早已不能忍受。這是2024年1月27日,第六屆《星火》文學年的第二天。前一天,來自全省各地的《星火》驛站驛友八十余人會聚泰和蜀口洲,今天一早乘坐大巴,翻越一道道林木茂密積雪猶存的山嶺和一座座村莊,來到名叫八六河的這段牛吼河邊。冷冽的空氣里混著草木蔬菜香和鮮牛糞的味道,水聲嘩嘩。驛友多數久居城市,對迎面撲來的混雜氣息難免有一刻的驚詫,但隨即生出終于置身草野的確實感。文學年和香樟筆會、稻田寫詩、發現家園等驛站其他活動一樣,逐好生態而居,過文學年,本就是一場從深陷的生活里暫時抽身,奔赴山林草澤的夢之旅。
而泰和生態正好。忘記是哪一年,從贛南去往贛中峽江,繞道興國走南韶高速。南方多丘陵,一連穿過四五條隧道后,車從興國進入泰和地界。空氣像是忽然變得濕潤,之前只長茅草和零星矮松的群山,忽然就綠意蔥蘢。我握著方向盤,精神頓時一振。
雪后的泥土松軟泥濘,一腳踩下,滿鞋是泥。一段步行之后,進入這片灘涂。灘涂周圍是山,牛吼河從一片山中來,流向另一片山,河水在這里拐彎,沖出這片灘涂。一條河在水流湍急時能發出如牛的吼聲,想必聲勢浩大。但這時的牛吼河秀麗溫婉,河水在冬日里波光清冷。灘涂上有牛,大小十來頭,無人看管。它們不吼,正悠閑地啃草。當舉著《星火》旗背著《星火》包的這群人列隊走過,所有的牛都忽然呆立不動,睜著眼睛看著這群陌生人。站在河灘四望,滿眼是豐富的植被,綠葉的落葉的,闊葉的針葉的,堆積如云的獨立不群的,枝枝向上的枝葉低垂的,高的喬木矮的荊棘,層層疊疊。遠山橫在牛吼河望處盡頭,驛友們散落在河灘上。他們有多久沒親近一條河,一塊河邊的草灘,一群草灘上的牛?有人在河邊找到一塊疑似扔在童年的卵石,尖叫起來。
離開牛吼河,驛友前往贛江邊的麻洲。麻洲也稱金灘古林,據傳有八百余年歷史,旁邊村莊的讀書人科舉得中進士,就在這里種下一棵樟樹,年深日久積木成林,哪怕世事更迭如潮汐漲落,樟林卻一直蓬勃蓊郁,成為眼前古木參天的樣子。這樣看來,這片樟林也是一片讀書林。古人比我們更明白,樹比人活得長久,一個人的聲名功業再烜赫,也有煙消云散那一刻,但樹會帶著一個人的掌溫長久活下去。一本書或一份刊物,也有理由比單個的人活得長久,有更綿長的存活的歷史,被更多人接納,并傳遞給更多人。走在林中,忽然想起資溪法水上傅村也有一片讀書人種下的林子,見證過一群身穿《星火》文青服的人,在蓄水的稻田里彎下腰身,用腳寫下詩句。多年以后,那片林子是否也會成為某個隱喻?驛友們在古樟林里穿行,會合,揮手致意,漫步,和某棵樹交談。驛旗的紅和《星火》包的黃,與古樟林樹頂輝煌的五彩和邊上贛江的深綠輝映。幾名驛友坐在一棵橫臥的老樹上晃動雙腳,唱一首關于明天的歌,他們沒有憂慮的樣子,像是回憶起自己曾經的青春并沉入其中。有人舉起相機拍下這一幕。
一些樹上掛著一塊醒目的牌子,標識樹名、習性與樹齡,也指示用途:樟樹“可提煉樟腦和樟油,木材堅硬美觀,宜制作家具,雕刻工藝品”;山胡椒“全身都是寶,根部都可采掘使用,果實和種子可提取精油,榨取工業用油,醫用價值很高”;槐樹“可烹調食用,也可作中藥或染料,葉和根皮有清熱解毒作用,可治療瘡毒,木材供建筑用,種仁含淀粉,可供釀酒或作糊料飼料”。一棵活了五百年或兩百年的樹,面對人類中心主義或實用主義的執拗,大概只能笑一笑。樹有什么作用?它能不能像莊子那棵大樗,樹立在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枝葉招搖只為呼應風雨和流云,讓人作為超越功利的陪伴者,無為其側寢臥其下,像眼前這群人一樣?
二
回到蜀口洲已是傍晚。歐陽宗祠崇德堂邊上的廚房在余干驛友劉三明的操持下早已灶火熊熊,文學年的年夜飯已經開做,蒸籠上的騰騰熱氣與年夜飯各式菜肴的滋味一道從廚房窗口翻涌而出,繚繞在宗祠、古戲臺、回廊、探花解元臺和進士書院的雕梁畫棟與青磚卵石的古色古香里。來自全省各地的美食,能上桌的已上桌,需要動手做的,則有驛友輪換著進入廚房系上圍裙,掄起鍋鏟在大鍋里翻炒。宗祠里隔著天井前后擺開九張圓桌,已經擺在桌上的有全南的燙皮、陜西的龍須酥、興國的紅薯干、遂川的草林豆餅、南康的畬鄉土餅、宜春的溫湯佬皮蛋、上饒的三粉粿和蛋卷、武寧的芝麻糖片、臨川的菜梗、泰和的沃柑、井岡山的南瓜酥等小吃,驛友們圍坐桌邊挑揀小吃入口,或抬頭打量貼掛在宗祠兩側墻上的歐陽氏明清兩朝出的二十一名進士紗帽官服的畫像與他們的生平德行以及為官履歷,不免暗想宗祠門口“天下歐陽無二氏,翰林文學第一家”的對聯的確不是誕語。
一個村莊同一姓氏,三百六十年間二十一人得中進士,還有更多的舉人,科舉之盛放在全國也不多見。為什么是蜀江村歐陽氏?有人作了探究,歸因于儒學觀念深入人心,數百年間科舉制度盛行,家族基因里的為官觀念,名師執教出高徒,以學立身讀書刻苦,甚至還因為祖墳選了風水寶地,等等。當然,這些可能都是理由,在一代又一代蜀江村人那里,也都說得通。一天后我站在蜀口洲頭,看見蜀江從身邊流出匯入滔滔贛江,一艘貨船正劃開闊大的江面向北駛去,身后是推開的波浪,前方是渺遠的天際。我突然想象某個蜀江村人,當他乘坐一艘船同樣揚帆北去,船頭的風迎面吹來,他的衣袂在風中翻卷,江岸的蘆葦與翩飛的沙鷗,會同未知的世界一道盡入眼底,他心里原先圈定的世界是否會砉然瓦解,而另一個自己開始升騰?
天井邊擺開另一張圓桌,桌上鋪開數條裁剪好的紅紙,桌邊是圍觀的驛友,驛站的書法家南康燎原驛驛友黎業東正提筆書寫驛友撰寫的兩副對聯。一副是,星火搭橋,文學薪傳春作證;情懷接力,書香墨繼島為媒。另一副是,蜀口洲迎贛鄱客,星火人過文學年。對聯不求雅馴,但求應景。暮色從天井上方涌進來,幾名驛友在立柱間懸掛紅色的燈籠。黎業東寫完最后一字,吐氣擱筆,圍觀的驛友喝一聲好。天巖和繼亮搬來梯子,將兩副對聯分別張貼到宗祠入口處“朝天八龍”與“進士”兩塊匾額下。古舊的宗祠張燈結彩,文學年更有了舊歷大年的樣子。
上菜了,幾名驛友手捧托盤魚貫而入,將下廚的驛友親手烹制的菜送到每張桌上,當泰和本地的烏雞湯與特色鵝頸、余干的辣椒炒肉、南康的狀元荷包肉、弋陽的年糕、興國的梅菜扣肉和魚絲、安福的冬筍炒肉、上高的大蒜炒香腸、井岡山的香煎粉蒸肉等主菜紛紛隆重登場,驛友們分桌而坐,手持筷子躍躍欲動,只等年夜飯開席;而當章貢驛火炬手鐘逸在宗祠門口點燃爆竹,連綿的巨響在蜀口洲的夜空長時間回蕩,文學年開始進入最歡樂的時段。同坐一桌的驛友互相致意,鄰桌的驛友互致祝福。人們紛紛起身,捧杯在桌與桌之間穿行,向熟悉的陌生的驛友致以文學年的新春問候。等十多天后,舊歷大年真正到來,他們回想起泰和蜀口洲的這個文學年,也許會恍然驚覺,自己的確曾在某一時刻有過多數人不曾有的“多出來的一生”。
人們把煙花搬上宗祠前面的探花解元臺,煙花騰空,臺下的人仰面驚呼。煙花在夜空爆裂的一瞬,火光照亮不同的一張張臉。更多驛友上到臺上,點燃手里的仙女棒,煙花在他們手里哧哧燃燒,在臺上圍成一圈不斷轉圈的他們,開心得像一群孩子。
三
又是篝火。當然,必須有篝火。不用細數篝火多少次燃起。篝火已是《星火》驛站活動的靈魂。如果篝火燃起之前每個《星火》人面對天地山川草木人煙構成的燦爛文理,還是如星星般散落的個體,當篝火燃起,《星火》人圍坐一圈,面對火光也面對火光照亮的自己,夜空下的《星火》人則已聚成一團火。
在篝火文藝沙龍主持人熊昱、夜葉、天巖簡單的開場白之后,安福驛驛長簡小娟帶領驛友為篝火添柴。不久之前,安福驛促成《星火》編輯部與安福縣衛健系統聯手創建《星火》微光讀書角,讓一份純文學刊物在可見的將來遍布安福的城鄉衛生醫療機構,文學跨入之前從未涉及的領域,文學刊物的服務手臂延伸至更遠的地方。醫學醫治肉身,文學治愈心靈。每講及此,簡小娟都難抑激動,為人生還有激情可與一群人共同燃燒,去突破圈層,挑戰之前的不可能,證明生命依舊存在諸多可能性。安福驛之后,永新驛驛長汪雪英帶領一群年輕的驛友祝福所有人新年快樂。汪雪英無疑是快樂的,她在鄉間種植水稻紅薯和其他莊稼,同時寫詩歌散文,是真正在稻田寫詩的人。此后各驛站驛友次第上前,為篝火添上從各自驛站帶來的木柴,在篝火的暖光里,有人講述一段驛站故事,在故事里重溫某一刻的感動;有人回顧《星火》給自己帶來的第一束光,并在對光的追逐中,最終自己成為光。有人在手風琴的伴奏下唱歌,唱《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有人讀詩,讀自己的詩,讀《陌生人,讓我們一起過個年吧》。有人即興創作,與驛友聯動;有人說愿景,暢想更文藝的生活。有人多次參加《星火》驛站活動,依然覺得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有人第一次參加活動,慶幸自己像一滴水匯入江河。靦腆的人感受到表達的熱烈,終于鼓起勇氣向一團火表白;最沉穩的參與者被此起彼伏的熱烈感染,想到曾經一起走過的路,突然生出離別的傷感。
篝火夜談,在這里,袒露心聲的言辭是唯一的主角,《星火》則是明亮的線索。言辭像飛舞的蝴蝶,所有熱烈的內斂的、深情的直白的、巧妙的樸拙的、成熟的稚嫩的、綿長的簡短的、詼諧的莊重的、閃光的暗淡的詞語,都被傾聽者一一捕捉。在這里,言辭也像溪流,各有源頭與途徑,最終匯成寬廣的詞語之河。據說孤獨的人經歷過篝火夜談,都不再孤獨;曾經浮躁的內心經歷過篝火夜談,都褪去浮華與功利,還原成一顆本來的赤子之心。
在訴說與傾聽的雙向奔赴中,不覺又到深夜,所有人手里的柴都已添完,一盆篝火燃燒將盡,炭火在夜風里忽明忽暗。圍成一圈的人聚得更攏,章貢驛驛友毛愛民拉起手風琴,所有人揮動手里的光,再一次唱起《明天會更好》。當手風琴拉長最后一個音符,夜談結束,人們陸續散去,鐘逸留下來,守到最后一點火星熄滅。
四
文學年進入第三天,一場奇妙的頒獎儀式(本質是編輯部表彰驛站先進集體和個人)在蜀口洲頭舉行。現場無需布景,接納蜀江北流的贛江是天然的巨大背景;無需紅毯,環島的紅色塑膠路面延伸到這里;也無需配樂,手風琴隨時切題的伴奏,贛江的濤聲,風吹古樟樹葉間細密的私語,混成最好的背景音樂。一起過文學年的全體驛友組成盛大的觀禮團。表彰名單高度保密,盡管觀禮者心中對誰將獲獎各有答案,但在頒獎嘉賓念出名字之前,獲獎者對自己即將獲獎仍一無所知。獲獎名單是一串閃亮的名字。
有必要重溫一遍名單和飽含才華與激情的授獎辭。
最美驛長:簡小娟
授獎辭:
《星火》安福驛一年來裂變式增長與爆發,就像火點旺了更多的火,愛喚醒了更深的愛。
安福驛的不斷壯大,是真正能福澤讀者的成功。42個《星火》讀書角的創建,是安福驛走進安福衛健系統的一小步,卻是文學破圈邁出的一大步。
作為安福驛驛長,你的表白總是那么謹慎,你的努力卻如此堅韌并不斷給人驚喜,你或許無意爭先,卻被舉輕若重的責任心一路追趕,一不留神奔跑成穿越四季的領頭羊。
鑒于安福驛在2023年驛站建設中一騎絕塵的驚艷表現,鑒于你無私無悔無愧于心的真誠奉獻,鑒于你在榮譽面前如履薄冰的謙遜品格,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特授予你2023年度《星火》驛站最美驛長稱號!
最美驛站:安福驛 永新驛 信豐驛 奉新驛 燎原驛 宜春文藝驛 都昌驛 余干驛 廣信驛 浮梁驛 黃金驛
授獎辭:
鑒于安福驛、永新驛、信豐驛、奉新驛、燎原驛、宜春文藝驛、都昌驛、余干驛、廣信驛、浮梁驛、黃金驛在2023年驛站建設中的驚艷表現,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特授予以上讀者驛站2023年度最美《星火》驛站稱號!
最美火炬手:王艷金 鐘逸
授獎辭:
鑒于王艷金長期以穩定的熱情和高效的行動助力《星火》驛站建設和品牌宣傳,鐘逸在《星火》品牌活動中的默默奉獻和穩定表現,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特授予你們2023年度《星火》驛站最美火炬手稱號!
最美朗讀者:熊昱
授獎辭:
鑒于你長期以迷人的聲線助力《星火》作品的傳播,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特授予你2023年度《星火》驛站最美朗讀者稱號!
最美評刊員:黎業東
授獎辭:
鑒于你長期穩定熱心地評論推介《星火》作品,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特授予你2023年度《星火》驛站最美評刊員稱號!
最美志愿作家:戴姍 江錦靈 帥美華 賴韻如 天巖 洪秋香 汪雪英 簡小娟
授獎辭:
鑒于你們一年來以飽滿的熱情和務實的行動投身“作家教你寫作”文藝志愿服務活動,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特授予你們2023年度最美志愿作家稱號!
《星火》驛站成立近六年,才迎來一場鄭重其事的確認與表彰。獎品是《星火》靈感本、《原漿散文精選集》和觀禮團的歡呼。獲獎者的激動與緊張,在顫抖的獲獎感言中表露無余。他們像重回學生時代,領受一份精神認可多于物質鼓舞的獎勵。最美評刊員黎業東說,這些年和《星火》在一起,心里一直燃著一團火,但這個榮譽還是太突然。三次上臺的簡小娟說的是,火點燃了更多的火,作為一名草根作家,和《星火》在一起,你無法預料事情將怎么發展,會遇見什么樣的人,這正是成為《星火》人最迷人的部分。頒獎禮進行到中途,江邊下起了小雨。頒獎禮在雨中繼續進行。
五
《星火》文學年和《星火》驛站的其他活動一樣,一旦啟動,會自行運轉,不同的人各司其職并形成合力,于是活動順利推進,哪怕偶有突發情況,最終也能圓滿。因此前期投入精力組織安排文學年各項事宜的泰和驛驛長魏琦,在文學年三天的大部分時候,都不像身負重任的樣子,而是兩手插兜混在背著《星火》包的驛友群里,靜觀多于來回奔走。
她好像也一直都是這樣,在陌生的人群里多數時候不聲不響,哪怕出聲,說出的也不是驚人之語。我曾經多次將她和另一位寡言的驛長混淆。她曾經不聲不響滿世界游走,幾乎走遍了全中國,到過三十多個國家,足跡遍布亞洲歐洲非洲和澳洲。就剩美洲沒去了,實在是有點遠。她語言平靜,語氣并不顯得多么遺憾。去的最遠的地方,是非洲北部的摩洛哥,還是西歐的比利時,搞不太清了。語言不通怎么辦?現在手機都有翻譯軟件,很方便,再說還有簡單的手勢啊。她說這些的時候,同樣語言平靜。她說家里墻上掛了一幅世界地圖,沒事的時候就對著地圖呆看,身未動,但心已遠。
文學年后接著就是春節。大年初一,當驛友們在微信群互致新年問候時,魏琦已經背著《星火》包,獨自出現在與廣西東興一河之隔的越南芒街。她開著一輛車,兩天后到了德天跨國大瀑布,再過一天,則到了一處名叫風子蕩的天坑。每到一處,她都拍來打卡照發在微信群里。我看見其中一張打卡照,她背著《星火》包,站在天坑底部一塊石頭上,背對鏡頭伸出雙手,指向頭頂的天坑入口,有光從那里照進來。
她說這是她旅行生涯里最特別的一次。第一次速降到天坑底部。天坑里有陽光照進的地方有植物生長,而光照不到的地方,則是真正的暗無天日。她順著一條干涸的地下河,徒步一小時,才從另一個出口出來。魏琦說,當在不見絲毫光亮的地下河摸索行進時,像走在另一個世界。我想說的是,當她背著《星火》包一次又一次在世界游走,是不是也一次又一次走在另一個世界?
一個從我們置身的世界里多出來的另一個世界。
田寧,江西上猶人。作品見于《星火》《滇池》《湖南文學》等刊。獲谷雨文學獎短篇小說獎、梁斌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