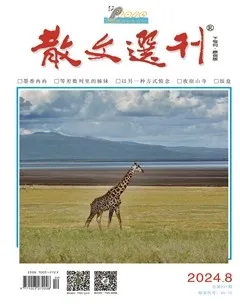等差數列里的姊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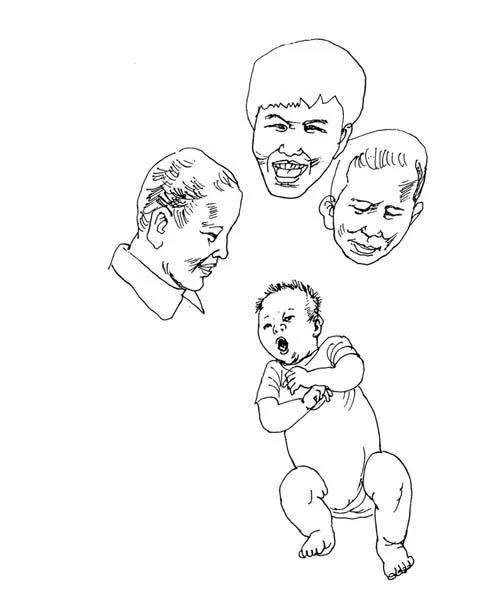
我有一個姐姐,大我三歲;我有一個弟弟,小我三歲;姐姐叫英,我叫鎊(后來,身份證名字改為“磅”),弟弟叫法。身處社會最底層的父母,他們以農民最樸實的本能,經過一番煞費苦心的設計,終于把我們弄成一個等差數列帶進了人間。
其實,我還有一個妹妹老四,她比弟弟還小三歲。她的降生,似乎是上天要賦予這個等差數列一個更加完美的定義域,姐姐是首項,是不變的;妹妹是末項,是上蒼的魔法變進來的;弟弟在妹妹的擁擠下,跟我一起擠成了中間項,我們就這樣擁擠于山間一處懸掛著34 號門牌的小屋,那是一間二層的木瓦房,小屋邊還緊挨著一個修葺得更加矮小的小屋,那是爺爺的住處。小屋與小屋相連,我們姊妹于34 號會聚,像流水相聚的浮萍,像覓巢歸來的春燕。
那是一個初夏的午后,那時的老四尚未來到人間。我們母女四人圍在竹篾、籮筐前,挑揀一堆的茶葉。我們分工明確,媽媽揀最精致的小芽尖兒;姐姐揀兩片葉兒的小芽苞兒;我揀三到四片葉兒的;弟弟一把一把抓最粗的老茶。如果我是質檢員,三弟的作品肯定是過不得關的。可媽媽從不壞了弟弟的興致,還盡夸他挑得快,挑得好。三弟對于媽媽的夸獎,一向很會享用,他像充了氣的氣球,又蹦又跳、輕飄飄的。我一向分不清、道不明這是三弟的天真,還是無知,但苦于媽媽在旁,只能偷偷用鄙夷的眼神掃射他,撞擊他。他竟更得意了,還用扮鬼臉還擊于我。
此時,只有姐姐是永遠中立、安靜的樣子,像是海洋中的一座孤島,又像是圍裹孤島的一片大海,她既深沉又孤寂,智慧又善良。我問過姐姐,是不是虛長幾歲的年華,是不是一聲聲“姐姐”的叫喚,讓她變成了獨特的樣子,她一時囁嚅,我沒問出答案。
在我們挑揀完所有茶葉的時候,夕陽還在山頭露出半個笑臉。媽媽對我們宣布:“明年,你們就要多一個姊妹了。”“多一個弟弟吧。”她又補充作了說明。當時我和弟弟都把媽媽的話當耳旁風,我向來對未卜先知的言論持有狐疑的執念,因為我見了太多大人們關于明天和未來信誓旦旦的承諾皆是在時間里撲了空;而弟弟更愿意在言論里捕捉關于吃和玩兒的信息,對于其他信息一律毫無興趣。三弟癡迷于扮鬼臉與我隔空較量,并為自成一派的“變臉”技藝而沾沾自喜、揚揚自得。
或許是“哥哥”二字壓制了我的膽量,束縛了我的手腳,我不敢同三弟一樣肆無忌憚,心有不甘的我謹慎地以比槍手勢予以回擊,再借余光偷偷瞥過母親和姐姐的臉龐。媽媽的面容平靜祥和,只有姐姐愣神于須臾之間。這種瞬間的愣神旁人極難用理智去分辨,唯有那時的我洞察到。我確信,恍惚間愣神漣漪起始于她仰起的側臉,轉瞬,又隱沒于那深邃的眼眸。她用很自然的低頭動作掩飾,再抬頭時,她的臉龐清澈動人,靜如止水。
或許,真就姐姐聽進了媽媽的話,或許真就因她虛長了幾歲,就因她被屢屢叫喚為“姐姐”,她就在本不該懂的年紀里懂得了他人不懂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斜陽照在姐姐緋紅的臉龐上,這抹動人緋紅是陽光賜予她的色彩,是青春賦予她的氣息,是父母期盼她長大的急切呼喚。斜陽又輕輕擦過媽媽和三弟的衣袖,在地坪上留下淺淺的影子,再又緩緩地走進了那間小屋。
一年后,看似一模一樣的春末夏初的午后,總要有一些故事要發生。
那個靜謐安睡的午后,被母親一聲腹痛的哀號喚醒。女人們按部就班,開始忙活,她們有說有笑,從屋子進進出出。男人們則是站在地坪里講一些無關于女人生產的話,說說土地莊稼、雞鴨牛羊,扯扯風水寶地與天上人間。他們好像對女人生產漠不關心,無心幫忙,或者說該幫的忙、該出的力皆早已傾情奉獻。屋里,一個女人說剪刀在哪里,就有另一個女人四處去找尋;一個女人說水熱好了沒,就有另一個女人使勁兒地往土灶里塞柴火;又有一個女人說毛巾、毯子準備好了嗎,房間里就傳來另一個女人翻箱倒柜的響動……這時必有一個女人大聲地吶喊:“再用點兒力,用盡你所有的力,就跟吃壞肚子使勁兒往外拉一樣,再也不要保留……我就要看到小腦殼了。”
“痛死了。”唯這是我母親在整個下午uMfN7HZm/ssDOL8YDJ+6Zw==里叫喊得最清晰的一句,其他盡是她的吼叫。“痛死,你也得再頂一頂。”“你都生仨了,咋還這么費勁兒,我生第一個崽都跟雞下蛋似的……”又有一個女人在旁附和。
“痛死了。”我又聽見了母親撕心裂肺的嘶吼。漸漸地,母親的嘶吼哀號漸而微弱細渺,女人的加油吶喊也不那么沉重有力。我以為是母親不那么疼痛了。接生婆張阿婆神色凝重地從昏暗的屋里走出來,父親三步并兩步迎了過去。張阿婆在父親耳旁嘀咕了幾句,又踅足折了回去。我似乎隱隱聽見了關于“死”的細小字眼卻又無從查證,可我清晰看見了父親一臉從容轉瞬成了愁眉緊鎖。我開始多心并擔心起來,我的母親是不是要死去了。
父親開始在院子里踱步,來來回回,一刻都不消停。祖父坐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吧嗒吧嗒地抽著水煙。只有姐姐、我、弟弟三人靜靜地,并排著坐在門口的石階上,等待大人們的指令,苦等那一聲破空而來的哭響。我甚至于幻想以姊妹仨悲慟哀歌來化解“小四”沉寂無聲所帶來的空前災難,我懵懵懂懂,堅信只有母親的孩子的真切痛哭才能拯救她的性命,才能結束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慌亂。
陽光在我們的頭頂走了一圈兒又一圈兒,我們的影子也從西邊倒向了東邊。不知等了多久,夕陽要徹底落山了,再也留不住;父親的額頭冒著汗,他杵在院子里;祖父的手指在煙袋疙瘩里不停摸索著,不知在找尋什么;樓上幾乎也沒了什么動靜。我料想,屋子里的女人們鐵定是把所有古老的接生儀式走了一遍又一遍,她們實在是黔驢技窮了;而房外的男人呢,我是親耳聽著他們對三界神靈苦苦哀求并虔誠念誦了一遍遍,他們也只能是希冀于神明庇佑了。可這個小家伙呢,還是遲遲不來人間。它是有多么厭惡這個人世間呢!
寂靜,有的時候比死亡更可怕。就在所有人都在無計可施、面如死灰的時候,就在所有人認定這將是由一個喜劇淪為一個悲劇甚至是一尸兩命的慘痛事實的時候,這個小家伙竟以一聲帶著哭腔的嘶吼撕破一片死寂,老四與哭吼聲幾乎同時來到人間。可誰還有那個閑心管它是哪個先來哪個后到呢,他們都來不及從驚魂未定里逃出,來不及躲進一片喜悅與祥和。總之,它來了,母女平安,這就足夠了。
“生了,是個女孩兒。”這喊聲和哭聲也幾乎是同時發出的,父親從站著變成了坐著,爺爺從坐著變成了站著,他們姿勢的變化也幾乎是同頻進行的。
我們也一起抬頭向二樓的樓廊看去,企圖從兩扇玻璃窗里睥睨出個究竟與未來。我們還只是看到了兩扇小窗,還有窗沿兒上擺著的一盆尚未開花的劍蘭。姐姐扭過頭,靠近我耳朵說:“生了,是個妹妹。”我也扭過頭,靠近弟弟的耳朵說:“生了,是個妹妹。”弟弟也扭過頭,發現沒有耳朵可訴說,就跑去拽著祖父褲腿上的一個破洞,跟破洞說:“生了,是個妹妹。”
慌亂的午后在小四起起落落的哭啼聲里,在女人們逐漸恢復理智而又溫柔有力的驅趕下,終是消失于淺淺的夏夜里。“劫后余生”,母親用自己的親身劫難來演繹這個古老成語的真諦,它將比任何課堂、任何辭典的說文解字都清晰透明、生動形象。這也必將是一個令我永生不忘的幸福詞語。
我和姐姐的歡樂在小四帶來的哭聲與笑聲中變得松軟、擴展而蔓延,我和姐姐學大人的樣子,捏捏她的小臉,勾勾她的小鼻,管她叫“細細妞”,輕輕地叫她“小四”。小四哭與笑像輕柔白云包裹整個山頂、整個34 號。三弟也學我們,學我們歡快的樣子。我和姐姐的歡快隨著時光的腳印一路前行,而三弟的快樂是潮漲潮落的。他玩兒瘋了依然忘乎所以地笑,他靜下來時,就又悶悶不樂,他時而快樂、時而悲傷。他似乎覺察到小四將給他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他時不時在空氣里揮舞著小拳頭,他以比小四更猛烈的哭聲與笑聲來表達他的悲傷與歡樂,他甚至一度妄想以這種瘋癲手段來重新奪回繼續被母乳喂養的權利。他的危機感是敏銳的,也是極其準確的。
又是一個夏日的午后,在三弟的眼里,那肯定是一個遭罪的午后。他被迫從帶著兩扇玻璃窗和配有一段木樓廊的前屋搬出,離開那個踮腳倚欄桿就恰好瞧見山前潺潺燕子溝和天空白云飄蕩的“ 上等房間”,他從此就要跟入睡前形影不離的父母和那一張溫暖柔軟的床分離。那是一個足以體現身份高人一等的住所。他從此就要住進一個狹小而昏暗的房間,跟我們分攤難過與黑暗。后屋,只有一個小木窗,即使打開木窗也只能看到后山那株風燭殘年的老楓樹和稀稀拉拉的枯黃竹林子,關上窗就是一個暗無天日的悲慘世界。
確實,我對后屋的印象與評價也的確是如此。我們畢竟是親兄弟,我與他皆有著一樣敏銳的感知和一樣正確的審美,在他的眼里是那樣,在我的眼里也是那樣。
緊緊一墻之隔的距離,三弟近乎使完了全部氣力才把自己從“前”挪到“后”,他沒帶什么行李,也沒什么行李可帶,僅是帶著兩眼汪汪的淚水和一個小小梅花枕頭,迎接他的是姐姐的安靜與柔軟的微笑,還有一個哥哥的幸災樂禍的鄙夷之情。從此,他的活動空間從光明透亮的前屋退出;從此,他的睡眠再也無法得到母親無微不至的輕撫與告慰。三弟苦苦喊了一聲“姐”就摔入姐姐的懷里。至此,他正式與“前屋”的過去告別,即使他萬般不舍、萬般哀求,可無論怎樣,前屋的兩位主人,眼下是仨人,他們皆是“啞巴吃秤砣——鐵了心”。
而最早走完這一段艱辛路程的是我的姐姐,那時迎接她的只有一張小床與無邊的黑暗。我猜想她曾無數次戰栗于我與父母安睡的房門前的那條狹窄的過道,戰栗于那一小方平坦的樓板卻又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可她終是選擇了向“退”妥協,她一度躊躇,一步步退縮,她無助地退向黑色無聲的世界,或許是黑暗世界主動侵襲了她,也或許是她壓根兒就沒得選擇。我猜想她度過了無數個無聲的暗夜,我猜想她無數次等待我的到來,或者說在等待三弟的降生,她為此等待了將近三年。
在小四快滿一周歲的時候,我已經七歲,在她快樂成長的日子里,在長輩們都習慣喊她老四的時候,在我和姐姐沉溺于喊她小四的時候,弟弟也跟著期期艾艾、含糊不清地叫她小四的時候,在我們都認為她是集萬千寵愛于一身而降落人間的小精靈的時候,一個困擾我們姊妹整個青春乃至一生的謎團毫無征兆地籠罩上我們。
那又是一個夏日,只是從午后推延到了翌日清晨。我們仨都還沉浸于后屋不再黑暗的睡夢,我的父母竟藏匿于天色未亮的黑暗謎團里,他們將土灶里的草灰涂抹于臉上,如敵特一般做了喬裝打扮,他們鬼鬼祟祟地摸出了村莊,他們應該沒有經過爺爺的同意,他們瞞過了村莊所有人,將小四從暗夜的34 號裹挾進小鎮的另一個黑暗里。襁褓里,小四的心口間,僅是戴了一只寫著生辰八字的平安符。
父母是再一次吃了秤砣鐵了心,他們把小四與襁褓一起托付給了一張還未開張的豬肉鋪案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時的小四早已清醒、早已號啕大哭。一年前,她有多么不想降生那個人世間,此時就有多么不想離開這個人世間,這個34 號。
清晨的天色還是暗的,暗得像一團迷霧,沒人看得清,就像纏繞在小四身上的謎團一樣,唯生辰八字,成了一條可有可無的線索和一個不清不楚的答案。
這些可惡的細節是在我們逐漸成長歲月的旁敲側擊與追溯過往的合理推演下得出的,父母一直是不置可否的樣子。
后來,祖父走了。無比衰老、了無生機的祖父從矮小的小屋里搬出,在祖廳的一張門板上留戀了兩天,就頭也不回徹底地離開人間,離開34 號。他跟祖母一起住進了燕子溝旁高高的向陽坡上。從此陽光無須半點兒輾轉即可尋到在一起的他們。后來,我的父親又從莊稼漢轉行當了礦工,母親也跟著他到處流浪。
時光無聲逝去。父母帶著一身無可逆轉的傷害從礦井爬出,爬上地面再次成了農民,此時的我們皆已成了家。
再后來,幾經行政區劃歸并與村規模優化調整,老家的地理范疇從大變小,又從小變大。34 號門牌更寫成更為吉利的66號和8 號,可我們終是覺得任何一個吉祥的數字都沒有原來的34 號好,于是我又故意把那張已墜入歷史長河的34 號打撈出來,并明目張膽地懸掛于老屋門前。或許34 號,才是數列里我們姊妹四人關于家的真正意義上的地理坐標。
我不想換。我怕有人尋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