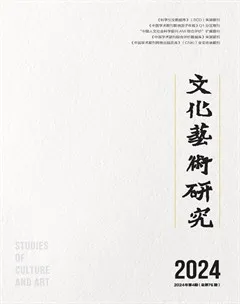用成語作劇:原型情境與創作模式
摘要:基于約定俗成的成語而創作的成語劇是一種小型教育示范劇,可在普及性戲劇課上教大家來演,借鑒西方的原型批評理論,重點研發文學經典中的原型情境,意在用形成于古代的各種原型情境來表現當代人的思想和情緒。成語本身往往很簡單,編劇既要拓展角色的數量和厚度,又要壓縮故事的空間和時間,編好至少含有兩個鮮明角色的有意義的沖突。劇長十多分鐘、有趣好玩又蘊含哲理的成語劇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也能成為向社會推廣戲劇的抓手。
關鍵詞:成語劇;原型情境;建構模式;普及性戲劇課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180(2024)04-0018-08
一、漢語成語與原型批評
“揠苗助長”的故事如果放到現代,一定十分可笑。古代真會有人無知到試圖拔起禾苗來“助長”嗎?《孟子》里的這四個字講了一個絕妙的寓言故事,口口相傳兩千多年,成了全球漢語世界中的著名成語。對漢語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成語的象征性“能指”早已大大超越了字面的“所指”,而從它的象征意義來看,當今世界“拔苗助長”的人不計其數。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如“刻舟求劍”“掩耳盜鈴”“守株待兔”等成語,本來都有其對應的具體的歷史典故——盡管多半是虛構的,但現代人早就習慣了用它們來借古喻今。這是成語中的一大類。此外,也有不少成語沒有明顯的時代背景,例如“見義勇為”“大公無私”等。這兩類成語都是人們經常使用的,第一類并不會因為源于古代就只能用在關于古人的故事里,事實上,它們在當代情境中的出現頻率反而更高。
為了幫助中小學開設普及性的戲劇課,我和上海戲劇學院的戲劇教育研發團隊編排了十多個“成語劇”,都是時長十來分鐘的短劇。a 成語這么多,哪些成語更適合編排為中小學生所需要的戲劇呢?如果選沒有歷史包袱的成語,創作的自由度就大得多,“見義勇為”之類的故事在任何時代、地方都可能發生。但因為成語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數語文老師更喜歡有歷史典故的成語劇——這類成語相對難懂些,更需要用直觀的戲劇形式來幫助學生理解、體驗,那些典故本身往往是有名的故事,穿上古裝來演,也會更像模像樣。網上看到的成語劇劇照大多是這一類。
成語是千百年來約定俗“成”的,絕大多數只有四個字,通俗易懂,耳熟能詳,甚至連不具備漢字讀寫能力的海外華人也可能聽過或用過,因此,在漢語世界中,成語的普及程度甚至可能超過一些文學經典中的主人公。由于漢語的特殊性,像這樣形式上往往只有四個音節,內容常常包含歷史典故的成語在其他語言文化中很難找到對應物。成語與英漢詞典中的“idiom”或“proverb”不一樣,更像“parable”或者“fable”——直譯就是“寓言”。西方也沒有我們這樣的“成語劇”——最相似的可能是中世紀教堂里演繹圣經故事的各類宗教劇,自從文藝復興世俗戲劇繁榮以后就不再流行了。不過,現代西方文論中有一個重要流派“原型批評”,著意于探尋歷史上各種文獻中反復出現的各類意象及其意義。我們不妨參照這個思路,來梳理一下某些中文文體中的“原型”。中華語文有數千年未間斷的歷史,各類文獻中的“原型”眾多,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原型批評理論稱西方文化中歷代流傳、大眾熟悉的經典人物為“原型”(archetype)。“原型人物”比現代中國文學理論中常說的“典型人物”更強調深廣的歷史、宗教的維度,而不必局限于特定作品中的具體人物形象。原型批評的倡導者諾斯羅普·弗萊研究的起點就是神話:“我們就從神話世界著手并開始我們對原型的研究吧。這是一個既有虛構型又有主題型構思的抽象的或純文學的世界,這個世界絲毫不受以我們所熟悉的經驗為根據,按近似真實的要求進行改編這一規則的制約。”[1]181 這個說法也適用于中國神話中的女媧、愚公等人物,但西方神話中的原型人物遠更錯綜復雜,背后的人物關系網絡也要大得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故其后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2]因此,當女CNPNAEBn5EP5upug5i17VtBe9mYb2uI2XKjlnJT4Hb8=媧、愚公等神話人物出現在成語中時,更值得研究的是這些形象所指的實用的社會學意義,而不是西方那樣的神話學、宗教學意義。這一點跟現代西方的原型研究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他們也常把古代神話與借用其意象反映社會現實的當代作品進行比較。弗萊在1957 年的《批評的剖析》中寫道:“六十年前,蕭伯納曾著重指出易卜生戲劇以及他自己的戲劇中主題的社會意義。今天,艾略特先生在《雞尾酒會》中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阿爾克提斯(希臘神話中的神)這一原型上去。”[1]181《雞尾酒會》看上去是個現實主義的客廳劇,但艾略特巧妙地給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穿上“時裝”,將其植入倫敦中上層社會的當代生活。這是文學原型的一個極好范例:既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有哲理,又能反映當下的社會心理,接地氣。
19 世紀意大利戲劇家喬治·波爾蒂曾經歸納過“36 種戲劇情境”,與后來的原型情境相比,顯得有些過于瑣碎。但這樣的模式研究對戲劇創作很有實用價值,而當代這種研究反而罕見了。源于神話研究的原型批評和戲劇中的編劇法最大的相通之處,就是重訪歷史文獻,對人類千百年來一直成功使用卻又常常熟視無睹的模式(或曰套路)進行歸納、推廣和創新——包括原型人物和原型情境。用中國的成語來作劇既是一種復古——把人們說了千百年的成語放到舞臺上來把玩,更是一種創新——要用這些形成于古代的情境和意象來表現當代人的思想和情緒。如果能把榮格、弗萊等人“原型意象”的學術理念,波爾蒂“36 種戲劇情境”的編劇理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規定情境”的導演理念結合起來,不但成語劇可以做得更好,通用的編劇理論、戲劇理論也將有更大的發展。
二、成語的三類原型情境
漢語成語中很難找到西方文學中那樣的原型人物,成語中的人物——包括廣義的“人物”,即角色(character),如:“狐假虎威”的狐貍、“螳臂當車”的螳螂等,以及難得有兩個對立人物的“愚公移山”故事中的愚公和智叟,都語焉不詳——就連在其典故出處(如《戰國策》《莊子》)中,那些文字也都簡而又簡,而且多半獨立成篇,不能跟西方經典那些關系網中的原型人物如俄狄浦斯、克瑞翁、美狄亞、猶大、浮士德等相比。我們的成語故事更像《伊索寓言》那樣的短篇寓言,正如弗萊所說的:“當一部虛構作品為表現主題而寫,或單從主題加以解釋時,它就成了一篇喻世故事(parable)或解釋性的寓言(fable)。”[1]74 既然成語故事中的“人物”過于平面,我們也就不必硬套“原型人物”的概念,不妨借用其研究思路,來探討漢語成語中“原型情境”的意義。成語全都以小見大,形式上的“小”都很像,但象征“大”的手法各不相同。它們在漢語文獻和口語中存在了千百年,既反映了精神分析學家榮格所謂的“集體無意識”,也蘊含著豐富的人物關系及情境,更符合馬克思強調的作為“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例如狐貍、老虎,以及怕它們的百獸;例如拼死擋車的螳螂和駕車的人;例如愚公與智叟,以及做最后決策的天帝。“狐假虎威”“螳臂當車”“愚公移山”這三個成語都象征著地位不同的人所處的特定社會情境,但三個主人公的對手不一樣,行動也各有特色。
從表面上看,“一根筋”的螳螂最簡單,盡管沒有任何獲勝的可能,還是要用螳臂去抵擋比它強大無數倍的車輪,因此,多數人習慣用“螳臂當車”來比喻自不量力、自取其辱的蠢人。然而,這個成語在《莊子·人間世》之后,又有了一個更有趣的典故。漢代韓嬰的《韓詩外傳》傳遞的是完全相反的寓意:握有絕對權力的齊莊公看到這個為了擋他的車竟然毫不怕死的“蟲”,出人意料地說:“以此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他寬容地決定“回車而避之”,竟為這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士讓了路。螳螂這一角色的兩種相反境遇,為成語劇的辯證闡釋與創作提供了絕妙的素材。信奉辯證法的布萊希特曾為中小學生寫過一對奇特的小型“教育劇”(didactic play)《說“是”的人》和《說“不”的人》。前者取材于一個日本能劇,一個孩子在野營途中得病,將耽誤集體的行動,他同意集體決定,對大家說“是”后就跳進深淵,讓集體不受影響繼續前進。該劇演出后,布萊希特聽到不少學生的反對意見,就又寫了一個《說“不”的人》,讓同樣情境中的主角說“不”,不肯犧牲自己。后來,兩個戲結成一對演出,刺激學生觀眾展開討論。同樣,“螳臂當車”也可寫成兩個相反的辯證劇,或者把正反兩個結局放在同一個辯證劇里。故事中弱者面對強者的社會結構不會變,但螳螂遇到的駕車人未必一成不變,在“螳臂”對抗“車輪”的原型情境中,具體角色所構成的規定情境也可以不一樣。
“狐假虎威”所體現的社會權力結構更復雜,表面上就有三種不同的角色,代表了從高到低的三個層次。老虎抓住了狐貍欲食之,狐貍騙老虎說它是天帝任命的百獸之長,不能吃,還可以立刻向老虎證明。老虎緊跟著它出去一走,果然看到百獸紛紛逃跑,就相信了它。狐貍本來明顯弱于獨霸強權的老虎,但它用計謀蒙騙老虎,同時也借它與老虎的近距離來嚇唬地位最低的百獸。這個原型情境折射出古代“君、吏、民”的三層社會結構,因為民無法近距離接觸到君,吏就可以“假虎威”,借君的威勢來糊弄民。甚至地位最高的君也常常會被中間的吏所蒙騙——連電視劇中的那些皇帝都只有靠具有傳奇性的“微服私訪”才能打破這樣的原型結構。
愚公是成語中難得的傳遞正能量的榜樣形象。毛澤東致黨的七大閉幕詞就用“愚公移山”作為標題,該文感染力極強,20 世紀60 年代幾乎人人會背。愚公在智叟面前義正詞嚴,沒有絲毫猶豫,最后果然大獲全勝,移山成功。但是,只記住成語的四個字是不夠的,因為靠人力徒手移除高山的行動有悖科學常識,作為成語源頭的典故也并不那么簡單。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明確指出了移山是如何實現的——愚公還沒等到子孫接班就“感動了上天”。因此,這個成語所代表的實質性的原型情境并不是表面的愚公與智叟二人斗嘴,而是真正擁有移山之力的“上天”與小民之間的結構性關系——上天能不能聽到小民的聲音,會不會為小民做主?在《列子》的典故里,天帝是因為“操蛇之神”打小報告而得知愚公移山之事的。我們的成語劇保留了這條線,點明移山驚動了蛇蟲代表的風水環境,引起天帝的關切。但光是這個原因,可能導致天帝阻止愚公移山,因此我們加上一條更重要的情節線,讓愚公的孫子孫女溜出去“上訪”(智叟看到,以為孩子吃不了苦逃走了),天帝聽了孩子們的陳情,理解了他們爺爺的苦心,也體恤他們一家的辛苦,于是派大力神去幫他移山。在《愚公移山》的故事中,愚公與天帝的關系這個原型情境才是關鍵。如果忽略了幕后的天帝這個最重要的推動力,僅僅展現課文里那幾句愚公駁智叟的豪言壯語,如“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再加上一些鐵臂揮鋤的勞動場面,這樣的“課本劇”就會流于膚淺的圖解和宣傳。
上述三個成語所代表的這類原型情境的所指較為宏觀,展現出角色社會身份的高低與博弈,主要探究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第二類成語的原型情境著眼點相對微觀,著重探究“人與自我”的關系,往往聚焦于一個奇特的自作聰明的人物,如“拔苗助長”“掩耳盜鈴”“守株待兔”等。這些只有單個人物的成語要發展成戲劇,必須給主角配置適當的對手。這既是戲劇的規律使然,更是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人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才能看清自己的本質。而配置角色時首先要考慮的是,這個成語背后有著什么樣的原型情境?這樣一看,本來微觀的“單人”成語常常也會放大為相對宏觀的矛盾。以“拔苗助長”為例,這人為什么要拔苗,是餓極了想要苗快點長成來吃嗎?事實上,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拔苗助長”的人并不是要吃苗或米,而是急切地想要幫助苗成長——在當今中國,這一點最明顯地體現在有學齡子女的父母心中。因此,成語劇《拔苗助長》設置了一個城市里常見的中產家庭——一個初中生及其熱衷“雞娃”的父母。父親為了讓女兒快速成才,跳級上頂級大學,把自己的農學課題“移植”給她,告訴大學面試官,女兒在“研究速成稻谷”。這樣的“速成”結果可想而知。
“掩耳盜鈴”的原型情境看起來簡單,就是一個自作自受的信息不對稱情境。這種情境在信息化時代按理不容易發生,但是,快速發展的社交媒體既代表了信息爆炸,又造成了愈演愈烈的“信息繭房”現象,反而使這種荒唐事更多了。本來擁有海量信息的人刻意屏蔽掉自己不想聽的聲音,結果偏聽則暗、則聾,成為“掩耳盜鈴”而不知的愚人。在我們的成語劇里,一個校園霸凌者剝奪了受害者的自由,因為自己裝了“高科技耳朵”,施虐時聽不到任何抗議聲,只聽到受害者被迫唱出的歌,還自以為得意。相比之下,“守株待兔”故事的主人公只是懶人而不是壞人,這個原型情境很像現在流行的“躺平”;守株和躺平都不是戲劇情境,因為二者的特征都是沒有積極行動,沒有競爭對手;“待兔”“躺平”都是可以無限延續的靜態,不會產生有沖突的劇情。我們在成語劇里給守株待兔者配上性格相反的對手——主動出擊者,雙方擔任辯論賽的正方與反方,表演一個史前人類原型的戲中戲,前者演堅守家園的農人,后者演一心開疆辟土的獵人,看最后哪方能說服對方。
第三類成語的原型情境主要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多是一些哲理性的寓言故事,如“坐井觀天”“杞人憂天”“莊周夢蝶”等。莊子“坐井觀天”的故事與柏拉圖的“洞穴之喻”異曲同工,都指出人要想認識世界所受的局限,提醒人警惕以偏概全的錯誤。成語劇把兩位哲人合二為一,設置了一位說書人“莊柏”,并進一步指出,要想認識世界,一定要走出井底的洞穴,親身去看、去實踐。“杞人憂天”問世兩千多年來,意義有了很大變化,古人擔憂天塌是因為不懂天降隕石的原理。科學與科幻文藝的發展使人越來越認可“憂天”“探天”的必要,因此,我們的成語劇也做成科幻劇,探索“憂天”這一問題的多種解法。成語劇《莊周夢蝶》不但展現了莊子與蝴蝶的關系,還加進莊子與惠子辯論“安知魚之樂”的問題,從“齊物論”的視角全面探究人類與動物的共生關系。這些關系既反映了先秦哲人的超前理念,也是當今科學發展的重要課題,這樣的原型情境值得戲劇人長期開發。
成語中的原型情境需要分而析之,但又有不少重疊的例子,很難絕對地劃分開來,如《莊周夢蝶》既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又可以說是通過追問“我是誰”來探究人與自我關系的典型案例。三大類的歸納還十分初步,將來一定會有更多更深入的發現。
三、成語劇的建構模式
在我們的十多個成語劇中,第一組《刻舟求劍》《愚公移山》《女媧補天》是常見的古裝成語劇,把成語背后的歷史典故展現在舞臺上。第二組《見義勇為》《張冠李戴》《杞人憂天》則是時裝成語劇,劇情發生時間不是當代就是未來。這三個劇又各有不同,《見義勇為》講的是當代故事,寫了一個地鐵上發生的案子。《張冠李戴》的劇情在不久后的將來。“杞人憂天”里的“杞人”在列子的時代是個可笑的諷刺對象,但今天可以從新的視角來看這個老故事,人類對太空的探索就是從哲學家、科學家的“問天”“憂天”開始的,很多好萊塢災難片都是“憂天”的科幻式展現。中國近幾年的兩部科幻電影巨制《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更是出手不凡——主人公不但“憂天”,還開始動手實行既大膽想象又細致入微的應對措施。成語劇《杞人憂天》受到這個思路的啟發,可以說也是一部“憂天”之作。此外,我們的《女媧補天》和《守株待兔》也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類“憂天”的母題。這樣的科幻式的關于未來的故事能讓成語劇不但為語文老師教學提供幫助,也可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的課堂上讓大家討論的話題。
第三組《拔苗助長》《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掩耳盜鈴》的建構模式又另具一格。這四個劇有一個不同于前兩組劇的共同特點:主要劇情發生在現代或者未來,且并不只是介紹一下成語就算了,還要在全新的情境中把成語的歷史典故演出來,甚至再進一步對它原初的意思來點“尬評”。這樣,全劇就呈現為一種古今平行的雙重結構,或者說套層結構。用學術界喜歡的術語,可以說這是一種“元成語劇”——關于成語的成語劇。這個新概念跟“元戲劇”有關,但也有差異。“元戲劇”是1963 年由利昂內爾·阿貝爾提出的概念,50 多年來在學界一直不溫不火,近幾年隨著“元宇宙”的討論,“元戲劇”也熱了起來。但嚴格地說,此“元”與彼“元”有著不小的差別。元宇宙的“元”指的是平行宇宙——“人類運用數字技術構建的,由現實世界映射或超越現實世界,可與現實世界交互的虛擬世界”,那種世界事實上誰也沒有真的進入過,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形而上的概念——更像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學)中的“meta”。元戲劇則不同,它的第一個杰出典范是皮蘭德婁1921 年首演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這六個人自稱從一個并不在場的劇作家的頭腦中走出,來到正準備開演的另一部戲的舞臺上,這樣的人設驚世駭俗,具有很強的形而上成分。但是,“元戲劇”還是可以在形而下的舞臺上呈現出來的。“元戲劇”更準確的中文翻譯是“關于戲劇的戲劇”,而“元成語劇”就是“關于成語的成語劇”。
可能有人會問:才十來分鐘的小戲,有必要弄得這么深奧復雜嗎?當然,學術性的術語只是在學術領域里才會有用——理論上的精細分類和分析有助于今后在實踐中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多樣化的成語劇來。對于中小學生來說,未必需要用“元成語劇”這種生僻的術語來解釋。但他們的老師也許會有興趣了解這種新結構成語劇形成的背景——其實恰恰就是為了學校教育的需要而開發的。成語劇的創作、排練、演出、討論都以普及性的戲劇教育為主要目標,《見義勇為》這類時裝成語劇的教育意義直白易懂,一看就清楚。然而占比更大的是0jGYbMGS2W7ZInZAkLs4qcXYtbSRWcfr8L052gs9R84=古裝成語劇,古裝戲必須古為今用,這就需要經過一種思路和語境的轉換,所以,語文老師在進行古代寓言教學時,多半會把重點放在現實意義這方面。而在排演成語劇時,往往是專注于演好古代的人物,把古為今用的思路轉換留給演出后的討論——但如果演出后沒有時間安排討論怎么辦呢?
有的成語劇就讓穿古裝的古人直接對現代人說話——《莊生夢蝶》《坐井觀天》里就有這樣近乎“穿越”的臺詞。這些臺詞究竟是古人的言論還是現代人說的話呢?處理得巧妙會很有意思,能讓有些觀眾發出會心的微笑,但也有些人還不大習慣接受這樣的形式,會感覺“跳戲”。《拔苗助長》等四個“元成語劇”其實是用了一種不同的“穿越”手法,干脆對觀眾挑明,把古今兩條線平行地展現在舞臺上,直觀地提供現代人運用古代寓言的范例,還可以直接討論古人的成語對于現代人是否適用這樣的問題。這種雙重結構讓主題帶有更強的辯證性,也就不容易遵循以前的慣例,在結尾處用一兩句話來明確“點題”。這個特點可能會給相對低齡的學生帶來一定的理解難度,因此,這樣的劇也許更適合年齡大一些的學生,甚至大學生、研究生。
還有三個特別的成語劇《莊周夢蝶》《莊生夢蝶》《坐井觀天》要歸為特別的一組,既是因為其構成模式與“元成語劇”相似——作者本人進入戲中,更是因為它們都取材于一個共同的歷史人物。成語中出現真人名字的極少,而《莊周夢蝶》《莊生夢蝶》的主人公就是莊子,講的還是同一個故事。二者最明顯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角色都穿古裝,而后者讓歷史人物莊子仿佛“穿越”到了既像現代又似乎是中性的情境中——具體的服裝風格可以由導演來選擇。《坐井觀天》也有點或隱或顯的“穿越”的感覺,角色可以穿古裝,也可以穿中性服裝。嚴格說來,莊子在這個劇里還只是半個主人公,因為劇中的敘述者“莊柏”是中國的莊子與差不多同時代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合體。莊子筆下的“井底之蛙”和柏拉圖講述的“洞穴之喻”都是富含哲理的著名寓言,而且故事本身也很相似,所以我們就把他們合在一起,給年輕人講一講屬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帶普遍性的哲理。
原型批評學者弗萊指出,跟“讀畫”相似,“在文學批評中,我們也時常需要從詩歌‘往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組織”[1]187。他說的是批評家的工作,其實,用成語作劇的過程也十分相似,編劇一定要經常性地“從詩歌往后站”,以便盡可能全面地認識成語及其源頭典故的“原型組織”,也就是本文所說的“原型情境”。
四、成語劇編劇的人設與場景
至今,我們演出過的十多個成語劇的構成有不同的模式,但每個劇的創作都遵循一個同樣的原則:體量再小也必須是真正的戲劇——具有實質性的能形成足夠張力的角色行動,最好要有懸念;成語劇不應是表面圖解故事的服裝秀、cosplay 加團體操。要演成語劇,首先需要編劇的創作——這是命題作文的創作,但絕不是改編。四個字的成語不可能提供戲劇改編的足夠素材——就是加上一小段文言故事也還遠遠不夠。要用一個成語來做出真正的戲劇,必須在四個字的基礎上實質性地加人加戲。時裝成語劇這樣做相對容易些,沒有歷史包袱,選材自由得多。難的是占大多數的古裝成語劇,雖然本身帶有故事性,但成語自帶的大多不是戲劇性的故事。
戲劇性與非戲劇性故事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具有或明顯或潛在的沖突,故事中至少有兩個有個性、有分量的人物或動物角色。“愚公移山”的成語故事里本來就有愚公和智叟,是兩個相當理想的戲劇人物,而“莊周夢蝶”的故事里只有莊子和蝴蝶。“蝴蝶”能不能以實體形象出現?這正是故事所質疑的。因此編劇只能先回避這個難題,引入曾經和莊子有過辯論的惠子,讓這兩個智者的斗嘴貫穿全劇。確定了兩個對手以后,還有個相當大的問題,一個成語一般只突出一個主要人物,就是有了智叟、惠子這樣的對立面,也只不過是陪襯。一強一弱的對壘就像一場不好看的球賽,戲劇中的對手也要盡可能地勢均力敵。這就需要給配角加戲,有時候主角也要加戲:多數情況下要加的并不是英雄事跡,反而恰恰是主角的軟肋,還要被配角及時抓住,這樣才能造成危機,產生懸念。在成語劇《愚公移山》中,智叟就發現了愚公的軟肋:愚公認為子子孫孫會永遠像他那樣移山不止,但子孫未必都那么聽長輩的話——這剛好是當代很多年輕人的問題。這個劇的懸念就在愚公的子孫們究竟是怎么想的,因此還需要更多角色——必須是有個性的人物,而不是一群人一起做點挖山動作。
在《莊周夢蝶》中,惠子的口才比一般人認為的厲害得多,這就逼得莊子必須用更多的行動來反駁惠子、證明自己。《莊生夢蝶》里的莊子也提到了惠子,但惠子并沒出現。這里,莊子的對手是個虛構的現代人,一個傾慕莊子但誤解了莊子的“小迷弟”小賈。莊子聽了老賈的抱怨后趕來開導小賈。劇中還有一些動物角色,因為莊子的夢就是“夢蝶”,而他與惠子的爭辯也是關于人能不能懂得“魚之樂”,小賈的誤解和最后的恍然大悟都圍繞著人與動物的關系展開,這就在兒童劇常見的動物形象中,融進了一般只有大學生才會討論的有相當深度的哲學問題。“螳臂當車”的故事中,螳螂與車輪的沖突很強烈,但角色太少太簡單,因此把《莊子·人間世》中先生對客人用寓言講道理這個情節放進戲里,變成“戲中戲”,角色、情節都豐富了。“刻舟求劍”和“女媧補天”本來都只是一個人的故事,都必須增加角色,給主人公提供有沖突、有懸念的平臺來展現其魅力。女媧的對立面出于私利,不但反對她補天,還教唆人偷走她的補天石去“消滅”天上的隕星。“刻舟求劍”本來是個現代人不大容易理解的笑話,為了提高它的可信性,就在主角身邊加了一個當眾揭他短的對手——這里的“當眾”非常重要,所以還要多幾個角色,讓主角因為愛面子怕難堪而不顧現實硬撐到底。
就橫向的人物設置而言,成語劇必須精準地拓展——從成語僅有的四個字拓展開去,加人加戲。但也不能加太多,最理想的是五六個角色。學校舞臺上常看到“人海戰術”——為了讓更多學生有上臺露臉的機會,其實是使他們淪為成群結隊走過場的龍套,并不能學到戲劇表演最重要的內涵。從縱向的情節安排來看,編成語劇要特別講究壓縮——歸并故事情節,壓縮演出時長。多數成語故事本身的戲劇性不夠,除了人物過于簡單平面,還有個問題就是故事拖得太長,很難在舞臺上集中呈現。憂天的杞人究竟“憂”了多久?守株待兔的人又準備“待”多久?“憂”和“待”雖是動詞,但都比較抽象,并不指代緊迫的戲劇行動,因此必須加以改造:或是轉化成積極的行動——把泛泛的憂天變成焦急地排隊買方舟票逃離地球;或是借編劇手法來濃縮時間——先把“守株待兔”變成“守球待寶”,剛說完要等兩千年,就有兩塊“寶貝隕石”先后飛撞而來,刻意用怪誕的情節來凸顯守株待兔的不可預測。
按時間壓縮的單一標準,一個十來分鐘的劇最好能集中在一個場景中,我們最早創作的《見義勇為》《刻舟求劍》在這方面最典型。《見義勇為》找了個可以嚴格實現“三一律”的理想場景,讓一樁偷竊案發生在運行中的地鐵車廂里。《刻舟求劍》本來就發生在船上,這個空間也是高度集中的,雖然時間在現實中會長很多,但劃船的風格化肢體動作能讓人看到時間的加速流逝,也可以算是三一律。此外的大多數成語故事不是場景太簡單——如“掩耳盜鈴”,不加情節撐不起一個戲,就是涉及多個場景,用獨幕劇很難講好故事。因此,編成語劇常要尋找不同的講故事方法。
《杯弓蛇影》看上去也是一個獨幕劇,四個人圍著桌子坐著說話,再加一個服務員,甚至比其他幾個戲更像傳統的話劇,但劇中有一個特別的設定,要求每人講一分鐘自己的旅游故事,這就把原本極難在舞臺上展示的五光十色的旅游場面轉換為角色的演說技巧。他們可以站著講,也可以像曲藝演員那樣邊說邊比畫,甚至用閃回相對完整地表演出來,這都是導演和演員可以自由發揮的創作空間。《愚公移山》剛好相反,一家人世世代代要移除兩座大山,時間、空間幾乎都是無窮大,怎么集中到舞臺上呢?把切入點設置在孫子孫女的“出走”——這是一個戲劇必需的緊迫的時間點,而不是小說敘述中常見的漫長的線。智叟幸災樂禍地對愚公說,看到你的孫子們吃不了苦溜走了,你那兒子又去找孩子了,你一個人還想移山?愚公不為所動,不信他們會逃走。這就有了懸念,讓觀眾為愚公捏把汗,但我們又不想推翻這個傳統的成語,不想丑化大家熟悉的愚公形象。所以,一會兒孩子們就回來了——原來他們是因為體恤爺爺而去找天帝陳情,還帶回了大力神來幫助愚公移山。天帝和大力神本來是典故里有的情節,但典籍中的話顯得太虛、太簡單,現在有了向天帝陳情的孩子作為活生生的紐帶,情節不但在時間上集中了,也更合理了。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成語劇中角色數量的拓展和場景時間的壓縮看似對立,其實可以相輔相成。只要編劇時正反兩個主要人物設置好了,自然會引發沖突,也常常會自然地把場景集中起來。
結 語
成語劇是一種全新的戲劇樣式,因為一開始是為中小學生而開發的,還很少有專業戲劇人進入這個領域來認真耕耘。這些年里,我和上海戲劇學院的戲劇教育團隊做了一些工作,發現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富礦”,值得大力開發、長期開發。短小精干、有趣好玩又蘊含哲理的成語劇不僅可以是學習傳統文化的載體,也能成為向全社會推廣戲劇藝術的抓手。但成語劇又很不容易做好,不能因為它的“小兒科”屬性就掉以輕心,以為只要發揮“集體智慧”,即興“編創”(devising,西方一種邊緣戲劇團體的做法)一下就可以了。成語劇衍生于語文課,必須是以劇為本的“劇”,首先要寫好文學劇本——適合演員表演,特別是適合未經專業訓練的素人排演的劇本。能不能吸引大家都來演,歷來是檢驗劇本好壞的重要標準。事實上,成語劇最好的、最現成的理想范本并不是“劇”的形式,而是其內核“成語”本身。千百年前的古人創作的寓言之所以能以成語的形式一直流傳到現在,是因為它們的創作者目光敏銳,直擊事件的底蘊,又用極接地氣的方式打動了世世代代的普通人,還將他們變成了傳播者——這個呈現和傳播的過程恰恰對應了愚公自己未必能實現的那句話“子子孫孫無窮匱也”。成語是中華語言文字中一類很特殊的“能指”,看似輕松幽默,但其“所指”往往十分厚重,積淀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原型”——既有象征社會大環境的“原型情境”,又有特定社會角色的“原型行動”,如“移山”“擋車”“拔苗”“掩耳”等等。
成語劇有可能像成語那樣長久地流傳下去嗎?單個成語劇可能性不大——或許再好也不過是給早就已是經典的成語“狗尾續貂”。但成語只有幾個字,一般不容易讓人聯想到“原型情境”,而擴容后的成語劇有了明顯的戲劇情境,或許能啟發更多的人來深入研究本來就蘊藏在成語之中的各種社會、文化的“原型”。成語劇是一種全新的藝術樣式,能不能和古老的成語一起流傳下去,要看創作者、傳播者有沒有愚公的精神,持之以恒——但這事可別指望天帝派大力神來幫忙。
參考文獻:
[1]諾斯羅普·弗萊. 批評的剖析[M]. 陳慧,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2]魯迅. 魯迅文集(八)[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16.
(責任編輯:馮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