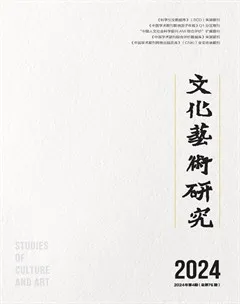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維納斯》歷史意義的再生機制研究
摘要:當代美國非裔女劇作家蘇珊- 洛里·帕克斯的代表作《維納斯》是一部基于真實歷史改編的戲劇。該劇通過豐富的文化符號,再現了南非土著婦女巴特曼的一生,重新詮釋了歷史文本。運用洛特曼的文化符號學理論,跨語境解讀《維納斯》中獨特的符號體系,揭示出動態文本觀的重要性,有助于系統理解該劇的歷史意義衍生機制。戲劇文本的創造功能與記憶功能的相互作用實現了歷史意義的挖掘,創新的交際模式在信息傳遞與創造的過程中有效修訂了原有歷史,空間模擬復現了非裔群體作為邊緣人的雙重困境。《維納斯》不僅激發了讀者和觀眾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意識,還鼓勵人們審視和思考歷史的真實性,從而實現了歷史書寫的更深層次意義。
關鍵詞:《維納斯》;蘇珊- 洛里·帕克斯;歷史意義;再生機制
中圖分類號:J83;I7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180(2024)04-0042-08
當代美國非裔女劇作家蘇珊- 洛里·帕克斯(Suzan-Lori Parks, 1963—)因其獨樹一幟的現代寫作風格以及對非裔群體生存現狀的審視與深思而廣受矚目。作為美國戲劇史上首位獲得普利策戲劇獎的非裔女劇作家,她將戲劇作為“創作歷史事件的孵化器”[1]5,在其實驗性劇作《維納斯》(Venus, 1997)中,敘說了南非土著婦女薩爾特杰·巴特曼(Saartje Barrtman)坎坷跌宕的一生。國內外學界多從后現代戲劇手法、戲劇主題等角度闡釋該部作品。基于學界已有研究,本文聚焦該劇蘊含的紛繁復雜的符號系統,梳理帕克斯書寫歷史的新方式,探析劇作家是如何令維納斯的故事在歷經漫長歲月后,仍舊可以在現代語境中實現歷史意義的再生。
符號學自誕生以來,逐步發展成一種廣泛應用于多個學科領域的研究工具,展現出跨學科、跨語境研究的潛力。20 世紀塔爾圖符號學派的領軍人物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 1922 — 1993)開創的文化符號學,融合了科學性與人文性,其強大的符號域穿透力為研究具有敘事復雜性的當代戲劇提供了新的方法論。洛特曼的文化符號學強調符號的多層次、多維度解釋,超越語言符號的表層意義,更深入地關注符號在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深層含義和作用。戲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通過空間模擬和符號的互動,能夠讓觀眾深入體驗和理解歷史和社會的復雜性,進而激發他們對歷史的思考和反思。將塔爾圖- 莫斯科學派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與美國非裔戲劇研究結合,可以在探討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的跨語境闡釋的同時,深入分析戲劇文本意義生成機制下的歷史挖掘、互動機制下的歷史修訂以及空間模擬機制下的歷史重現。
一、文本意義生成機制下的歷史挖掘
尤里·洛特曼開創的文化符號學以意義生成的問題為核心,將文本(text)定義為“完整意義和完整功能的攜帶者”[2]19,并將其視為文化符號學的核心要素以及pTFADd98tJ45rmfFBvXnqKjJwemmpj1pB70oIrgG87Q=“文化的基本元素”[3]7。洛特曼在其前期學術思想精華——《在思維的世界里》(Universe of the Mind)中指出文本的三大功能,即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the transfer of the message)、創造性功能(the creative function)和記憶功能(thefunction of memory),這三種功能使文本意義生成機制得以運作。洛特曼認為,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兩個參與者即便采用相同的自然語言、同等的記憶維度與共同的準則理解,也無法確保代碼的同一性”[4]13。因此,在戲劇文本中,創造功能與記憶功能更能靈活地促進戲劇文本的闡釋與傳播。
由于黑人對創傷歷史的潛意識逃避以及白人對自身錯誤的有意掩蓋,關于薩爾特杰·巴特曼及其痛苦經歷的詳細記錄在歷史上并不多見。對巴特曼的許多學術研究都“集中在其身體上,而人們對她的展覽和背景細節知之甚少”[5]189。受白人主導的主流歷史敘述所控制,非裔歷史記錄的真實性存在廣泛爭議。面對現實中的多重阻礙,以及可能被視為“消費巴特曼”的風險,帕克斯在她的戲劇文本中融合了個人的民族情感與藝術追求,將文本作為傳遞歷史意義的載體,從而使其內在結構更為復雜。相對于結構主義的相對封閉性和解構主義的過度顛覆性,洛特曼的文化符號學因其強調“文本的功能化與智能化”[2]183,為解讀這一作品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在《維納斯》中,帕克斯通過實驗性的戲劇手法突破了傳統語言的束縛,充分發揮該戲劇文本的創造功能與記憶功能,通過戲劇形式實現了能指和所指的具象表征和意義共通。
《維納斯》中,隱喻性的戲劇結構與異質性的戲劇對話相互交織,充分發揮了戲劇文本的創造功能,從而實現了對特定歷史段落的深入挖掘,這種處理方式使文本的歷史意義獲得新生和更新。文本作為“一個滿足所有符號可能性的系統,不僅可以傳遞現成的信息,而且是新信息的生成器”[4]13。文本的成分結構越復雜,其產生意義的可能性就會越大。在敘事手法方面,《維納斯》戲劇結構中慣性和非慣性之間的矛盾為挖掘歷史提供了新契機。帕克斯曾對該劇非常規的戲劇結構予以解釋:“通過每一行文字,我都在重寫時間線——創造歷史,這段(歷史)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但尚未被窺探到”[1]5。有別于常規的傳統戲劇的順序排序,該劇采用了反常規化的降序場景排序,戲劇由第31 幕開始,到第1 幕結束,倒敘結構破壞了劇情慣性的發展規律,增加了劇作的信息量,也映射了這段未被窺探的歷史將以新穎的方式再次進入讀者和觀眾的視野。此外,在戲劇的開篇和結尾,死去的維納斯以相同的方式出現,該循環情節的設置巧妙地將過去與現在緊密聯系。這一設計突破了傳統戲劇舞臺對時間與空間的桎梏,在同一文本中達成了穿越不同時空語境的協作。循環的舞臺指令使意義的解釋得以持續進行,提醒人們審視歷史的同時不要忘記現實的立足點。同時,這也隱晦地指出白人對非裔群體造成的創傷是長期存在且難以消解的。
在語言風格上,《維納斯》戲劇對話中語言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成為非裔群體遭受迫害的屈辱歷史意義再生的語言表征。“符號圈以其異質性為標志,填充符號空間的語言是多種多樣的。”[4]125作為文本符號,《維納斯》文本空間中的戲劇語言表現形態多樣,不僅有字典中查閱不到的詞語,還包含了音樂術語、醫學術語、黑人常用俚語等,構建出多個異質話語層,為挖掘歷史提供了諸多素材,其中最具創新性的戲劇語言表現形式是帕克斯的文字游戲。例如,當維納斯向馬戲團老板討要薪酬卻慘遭拒絕時,她用“Gimmmmmie!”替代了“Give me!”的常規表達[6]95。帕克斯在吉格茨(Jiggetts)的采訪中解釋了在戲劇中運用這種非傳統語言進行表達的目的,“這不僅僅是人們所謂的‘黑人英語’與‘標準英語’的對比……試圖非常具體地表達人物的情感變化”[7]。她通過獨創的偏離語言規范的話語方式,將文字符號轉化為情感表征的符碼,實現了情感傳遞。這種方式投射出維納斯面對資本掌控者的丑惡嘴臉時所產生的憤怒情感。在該劇中,類似這樣非常規語言的表達頻繁出現,既是對已有歷史的重新拼接和改編,也是對所傳達情緒價值的擴容,同時增加了讀者與觀眾對人物情感把控的難度。解讀文學文本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翻譯活動,“翻譯是意識的主要機制”,但因為“符號域中的不同語言在符號學上是不對稱的,即它們沒有相互的語義對應關系,所以整個符號域可以被視為意義的生成器”。[4]127 在《維納斯》中,非常規語言表達雖加劇了符號圈不勻質性,為文本解讀帶來了困難,但在解碼與翻譯的過程中,讀者和觀眾對劇作家想要傳達的信息進行再考量,反而促使文本可闡釋空間的延展,推動了歷史意義的再生。
此外,維納斯的身體作為一個可獨立遷移的象征符號,在不同語境下保存原有信息并賦予新的含義,成功實現了對原有記憶的重塑。這種處理方式促成了《維納斯》這一文本的記憶功能,激發了非裔族群對這段歷史意義的反思和更新。“文本不僅是新意義的生成者,也是文化記憶的凝聚者。”[4]18為印證文本記憶功能的跨語境闡釋能力,洛特曼曾以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巔峰之作《哈姆雷特》為例,解釋文本記憶功能的持續性影響:“盡管我們可能忘記了莎士比亞和他的觀眾們所知道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個時代以來我們所學到的東西,這就是賦予文本的新意義。”[4]19 這種解讀方式為分析當代戲劇文本中的助記功能提供了可能性。
在《維納斯》中,帕克斯將維納斯的身體塑造成對該歷史產生記憶的媒介。同時,該媒介本身也具有符號性質,“通過象征載體實現的符號化是文化記憶行為與結果的核心特質”[8]。在劇中,身體符號使文化記憶的象征以戲劇的方式呈現。首先,置身于資本營利的語境中,維納斯的身體成為流通的活體資本。畸形秀的文化現象19 世紀曾在西方風靡一時,這種表演貌似為畸形癥群體提供了謀生方式,實際上卻是極具剝削性的非人性化行為。觀眾們認為鎖在籠子里供人觀賞的維納斯是“可恥的、有原罪的”[6]87,畸形秀老板也時常對維納斯惡語相向,但是他們在嫌棄辱罵她的同時,卻又千方百計地從她身上獲利。這種兩面派的行為映射出白人對維納斯身體的欲望投射,暴露出白人對非裔群體顯性和隱性剝削的實質,揭示了受益者對金錢與欲望的渴望是建立在泯滅人性的歷史現實之上。當資本掌控者意識到“(觀眾)愿意為觀看一個擁有碩大臀部的黑人付錢”[6]87 這一商機時,為使利益最大化,他們迎合觀眾的獵奇心理,又推出了“多花多得”的營銷策略:“如果我多付一點兒錢,我就能多看一會兒,如果再多付一點兒錢,我就能站在特別的地方觀看。”[6]24 久而久之,維納斯的身體任人擺布,不再受個人的支配,成為符號化的產物和白人操控的對象。
隨著劇情的發展,維納斯所處語境發生了新的變化:在“科學”的語境中,她的身體在負載符號的同時,成為種族主義者刀下的活標本。當她被轉賣到男爵醫生手中時,身體作為一種意象符號,其所處語境開始變化。她曾反復詢問男爵醫生:“愛我嗎?”男爵回應:“我愛你。”但隨即又補充道:“我喜歡你!當然,只是在我特定的圈子里。”[6]162 這個“圈子”即男爵的“科學領域”。他利用維納斯的愛與信任,企圖實現成為“解剖學界哥倫布”[6]191 的幻想。在“偽科學”的保護下,維納斯的身體再一次被公開在大眾視野之中,男爵醫生及其同伴們不僅對維納斯的身體進行測量,而且還實施了侵犯,在這具身體上再度留下了罪惡的痕跡。這種“傷痕和傷疤代表的身體記憶比頭腦的記憶更可靠”[9]280,令這段創傷史在時間的塵封下,在非裔群體的代際傳遞中不斷引發“疼痛”。因此,隨著在不同語境中的遷移,文本中身體象征所映射的記憶功能,在不同時間與地點均保持了文本與代碼的多樣性,使讀者與觀眾切實了解到文本以及文本外所發生的歷史實踐與記憶,達成了文本可闡釋空間的延展。在帕克斯的戲劇實踐中,藝術手法的創造功能及維納斯身體符號的記憶功能在同一文本中協同運作,“區別只是方法論上的,因為實際上,所有功能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無法獨立運作”[10]9。它們共同將非裔群體在歷史上缺失的一頁以獨特的形式展現在讀者與觀眾面前,通過在文本這一有機生命體中的相互作用實現了歷史意義的挖掘與更新。
二、文本互動機制下的歷史修訂
洛特曼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提出了“我—他/ 她”型交際模式("I-s/he" system)和“我—我”型交際模式("I-I" system)的概念。在“我—他/ 她”型交際模式中,假設“我”自己擁有信息,而“他/ 她”是信息的接收者,這種模式通常在文化交流中占主導地位,但也存在理想化和局限性。基于雅各布森的交際理論,洛特曼更深入地探討了“我—我”型交際模式,即向已經知道信息的人傳遞信息。雖然這種模式看似與“我—他/ 她”型相矛盾,但實際上二者有共通之處。通過這種交際模式,創作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信息傳遞不對稱性成為意義創新的機會。
在“我—他/ 她”的交際過程中,《維納斯》中蘊含的多重符號被個性化解讀,打破了原有意象符號的簡單物質內涵。“我—他/ 她”交際模式著重信息的傳遞功能[2]126,劇作家通過輸入大量外來信息,使戲劇呈現多層次的符號體系,這些符號幫助讀者和觀眾熟悉歷史事實,并擴展其知識儲備。然而,由于劇作家與讀者、觀眾之間存在知識和信息的不完全對等,個體理解上的差異使符號編碼具有了創造性。因此,讀者和觀眾對戲劇的解讀并非簡單地還原了劇作家帕克斯作為信息發出者想要傳遞的意義。他們在參考符號本身的含義的同時,經常會增加符號編碼的豐富性,進行多重解釋。這樣做不僅傳遞了基本的信息,還彌補了歷史意義中被忽視或誤讀的部分。這種多重闡釋的過程使得戲劇在傳達歷史意義的同時,也呈現了創造的可能性以及讀者與觀眾的主觀參與。
首先,《維納斯》中,薩爾特杰·巴特曼的藝名“維納斯”在表現明顯的戲諷意味的同時,也呈現出一個具象生動的維納斯形象。在羅馬神話語境下,維納斯是美的女神。然而,當這種本該受人仰望的魅力投射到戲劇中的維納斯身上時,卻被解讀為對非裔女性充滿偏見且帶有色情的想象,體現了白人對非裔族群的固化印象。與此同時,帕克斯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維納斯,她渴望被愛、被撫摸、被親吻。這種意象的所指成功打破了原有刻板的歷史印象,向讀者和觀眾傳遞了一個渴望愛情并勇于表達愛情的維納斯形象。這種創新的表達方式豐富了歷史的意義,使人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和體驗非裔群體在歷史中的情感和人性。其次,帕克斯將戲劇物體“巧克力”作為歷史意義的具體指向載體,映射了維納斯的悲劇。一方面,馬戲團老板采用侮辱性的方式將巧克力作為給予維納斯的獎勵,他“把零食放在她的腳邊,看著她喂食”[6]101,這一戲劇物體傳遞了受益者對表演者虐待與歧視的信息。另一方面,巧克力可以被解碼為甜蜜與脂肪并存的商品,它使人們在獲得滿足和愉悅的同時,也陷入放縱和沉迷。男爵與維納斯初次見面時贈予她“紅色心形盒子巧克力”[6]137,在這里,巧克力并不是愛情的象征,男爵從未真正愛慕過維納斯,“就像維納斯為獲取快樂而沉迷于巧克力一樣,偽善的男爵將維納斯視為一種為快樂而消費的商品”[11]74。在甜言蜜語及巧克力的誘惑下,維納斯逐漸喪失對情感與人性的判斷。她對巧克力的沉迷隱喻了“對自己身體的消耗”[5],也同時暗示她無法擺脫被壓迫和奴役的命運,最終淪為供他人消費的商品。傳統語境中代表甜蜜浪漫的巧克力使讀者和觀眾超越其本意,通過閱讀的體驗和反思,產生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凸顯了這段歷史的悲劇性走向。劇中另一個戲劇物體“鐵鏈”的寓意也超越了原有語義的相關性,創造出更多的信息。在劇中,維納斯一直被鐵鏈所束縛,她對金錢與名聲的渴望成為一條無形的鐵鏈,將她拽向深淵。她渴望在殖民者的土地上實現自我價值,然而身處剝削與權力不平衡的關系中,這種遐想本就是不切實際的。此外,偉大的存在鎖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是十八世紀歐洲神學對萬物自上而下的分級,位于最底端的是巖石以及無生命的物質。劇中畸形秀老板稱維納斯及八位畸形秀表演者為“上帝存在鎖鏈中最底端的九位”[6]60。帕克斯利用這一概念隱晦傳達了白人對非裔族群及殘障群體的蔑視。她采用碎片化的話語設置打破了語言布局規律,“八大奇觀”反復合唱的“鐵鏈、鐵鏈、鐵鏈”[6]59 使這一意象在被讀者和觀眾解讀時衍生出新的意義。舞臺上,反復響起的關于鐵鏈的吟唱“呈現了‘存在鎖鏈’的神學概念,也讓觀眾聯想到被奴役的維納斯”[11]。因此,這一意象符號在互動中被闡釋為被奴役和被輕侮,戳穿了在畸形秀歷史上,資本掌控者為牟取暴利而編織的謊言。最后,“鐵鏈”隱形的奴役在舞臺上被顯化為有形的囚禁,“維納斯再次被囚禁,不是籠子,而是像狗一樣被拴在院子里”[6]59。此時,鐵鏈永久地拴住了維納斯的命運,它從無形到有形,含義在互動中逐層遞進,成為維納斯悲劇的終結。
相較于“我—他/ 她”交際模式的傳遞功能,《維納斯》中的附加代碼在“我—我”的交際模式下充分發揮其創造功能,更有力地將沉默敘事轉變為有聲敘事,將單薄的歷史敘事化身為更豐滿的歷史敘事,實現了歷史意義的修訂。“我—我”交際模式指“受試者向自己,即向已經知道信息的人傳遞信息”,這一模式主要是“引入第二個補充代碼的結果”[4]22。基于“我—他/ 她”型交際模式,讀者和觀眾已經對維納斯的故事背景有了簡要了解。然而,介于對維納斯歷史記載的片面性以及劇中主線情節的局限性,對劇作的意義理解仍略顯封閉。因此,借助“我—我”交際模式來解碼劇作家為該劇引入的一系列附加代碼,可以為戲劇賦予補充的意義。這種方法幫助信息接收者解構他們心中原有的信息框架,從而獲得新的認知。
“戲中戲”作為一段附加的虛構副線故事,其中所包含的信息為讀者和觀眾提供了解碼原情節以外的附加代碼,并獲取具有補充價值的信息。《維納斯》的“戲中戲”里的一對英國情侶是維納斯與男爵的縮影。在“我—我”互動下,讀者和觀眾得到耳目一新的信息,作為旁觀者來觀戲的維納斯同樣實現了與自我的互動。歷史上,維納斯始終作為一個失語的表演者供他人凝視,但當她從劇中脫離而成為“戲中戲”的一名觀眾時,她看清了殘酷的真相:為滿足未婚夫的獵奇心態,“戲中戲”里的未婚妻偽裝成維納斯來吸引對方,重獲未婚夫的愛。通過“戲中戲”這一附加代碼,讀者和觀眾可以在與自我交際的過程中,補充除“我—他/ 她”交際之外原文本中的內隱信息。其一,男爵對維納斯的愛與“戲中戲”里未婚夫的愛一樣具有偽裝性和欺騙性。其二,白人認為非裔女性的氣質可輕而易舉地被模仿與偽造。因此,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場域下,維納斯想通過外表獲得認可的愿望是難以實現的。不同于在空間中傳輸信息的“我—他/ 她”交際模式,“我—我”交際模式往往是在時間中進行傳輸。同作為非裔女性,帕克斯通過“戲中戲”的附加代碼與維納斯實現了跨越時間的對話:權能不平衡下,本就不存在公平,唯有認清真相,非裔女性才能展露其獨特氣質。此外,在原有歷史記載中,“沒有任何有關維納斯愛上男爵的記錄”[12]43。帕克斯通過添加與原歷史文本無關的情節信息——“男爵與維納斯的愛情故事”,再次為讀者和觀眾重新解讀歷史提供了附加代碼,成為其書寫歷史的新方式。歷史霸權下有關維納斯的刻畫囊括了長期以來白人對非裔女性固定模型的積累:“自奴隸貿易時起,黑人女性的身體便一直是白人凝視目光下的欲望客體,是原始蒙昧的性欲化符號。”[13]此類固定文本建模存在種族偏見,因此附加代碼的介入為帕克斯“修訂”歷史意義提供了文本空間。帕克斯打破維納斯的刻板形象,讀者和觀眾自身的原有記憶與劇中呈現的靈動鮮活的維納斯之間的巨大反差成為新意義迸發的契機。
回溯劇中兩條交際線路,《維納斯》中多元的意象符號以及虛構的附加代碼與主線真實的歷史故事多重雜糅,協同實現了文本的互動機制。“藝術不是從‘我—他/ 她’系統或‘我—我’系統中誕生的”[4]32。該劇的戲劇藝術在兩個系統中共生,在信息傳遞與創造的過程中修訂了原有扁平化的歷史,翻轉了維納斯在歷史上長期失語的狀態,填補了原有歷史書寫的空白,達成了歷史意義的修訂。
三、空間模擬機制中的歷史再現
作為意義再生的手段之一,文本的空間模擬機制可以通過對現實空間形式的模仿實現。洛特曼擁有獨特的時空觀,他將物理世界抽象化,將空間與文化相聯結,指出“文化與空間雖為本質上不同類型的存在,但具有內在的對應關系”[14]。基于這樣的空間模擬機制,洛特曼將符號外推至更廣闊的符號空間,誕生了其核心觀點“符號域”(semiosphere),即“語言存在和運作所必需的符號空間”(semiosphere)[4]123。在符號域中,二元對立的中心(center)與邊緣(periphery)以及邊界(boundary)的存在,令有限的文本空間語言呈現出對文化世界圖景(culture's world-picture)的無限模擬,實現抽象現實世界的具象化再現。
《維納斯》這部富含藝術性的戲劇文本,在具有交際性能的同時,也兼具空間特性。作為意義再生的手段之一,文本的空間模擬機制能夠通過對現實空間形式的模仿來實現文本中的空間建模。洛特曼的文化空間觀深化了文化符號學的核心理論,即“符號域”,這一理論不僅具有抽象性質,還具備實際的空間意義。因此,在這樣既具象又抽象的符號域中,“中心”“邊緣”的對立以及對“界限”的穿越交錯地分布在戲劇文本空間中,在《維納斯》有限的篇幅與框架下再現了現實空間與抽象空間中非裔群體的歷史記憶。
在現實空間層面,維納斯在“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移以及兩者間存在的鴻溝,真實呈現了非裔女性的生存困境。“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是符號域中最為本質的特性。盡管這種符號域具有抽象性質,但“絕不意味這個空間本身不具備實際意義”[2]39。在《維納斯》這一戲劇符號域中,維納斯的第一次空間位移是從非洲來到英國,差距巨大的社會空間景象揭示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社會環境的侵擾與破壞。維納斯在被販賣之前曾是非洲種植園的普通奴隸,她深知非洲的土地無法使其獲得名利,因此,當白人商人向她描繪“鋪滿了黃金”[6]37 的英國大街時,長期存在的“邊緣”地帶貧困使她立刻被“中心”地帶虛幻的金錢所迷惑。維納斯被引誘的原因歸根結底是“邊緣”與“中心”社會經濟極不平等的歷史事實。然而,當維納斯到達“中心”時,她發現英國的現實與白人商人所描繪的金碧輝煌大相徑庭。盡管到達了中心地帶,但她所面對的環境比邊緣地帶更為糟糕。“空間建模可以成為一種表達非空間思想的語言”[4]150,在帕克斯的筆觸下,維納斯的首次空間轉換成為對殘酷現實的揭露,即:“中心”的美好并不屬于“邊緣”群體。維納斯的第二次位移是在“畸形秀舞臺”與“舞臺背后”間的穿梭。畸形秀舞臺是白人主導的中心地帶,白人商人曾向維納斯許諾:在這里,“人們看你。人們拍手。人們給你金子”[6]37。因此,維納斯幻想自己在這一中心地帶,將以“非洲舞蹈公主”[6]30 的形象成為焦點。然而,來自邊緣地帶的人群很難改變在中心地帶受到歧視與迫害的狀況。舞臺指令提示,當維納斯首次出場時,“站在半明半暗中”[6]66。雖然她已脫離了原有的“黑暗”,但“半明半暗”的舞臺空間預示著她第二次階級跨越的失敗。“非洲舞蹈公主”最終被關在舞臺中央的籠子里,遭受觀眾的譏笑。“邊緣”與“中心”的差異在于“價值較低的社會群體被安置在邊緣”[4]140。作為白人眼中“上帝失敗的作品”,維納斯雖然來到了“中心”地帶,但因價值較低,仍舊被安置在不受尊重與保護的邊緣地帶。當她走下舞臺時,等待她的是更為壓迫的生存空間。她向畸形秀老板乞求道:“給我更多的食物,呃,鎖上我的門,呃,并且給我新的衣服。”[6]91 她不停地埋怨:“在我睡覺的時候,他們醉酒進來。”[6]96 這些表明了維納斯深陷備受擠壓的生存空間。帕克斯通過呈現維納斯在舞臺中央以及舞臺背后的遭遇,再現了邊緣群體舉步維艱的生存空間。劇中的另一處空間位移復刻了維納斯自始至終處于白人男爵控制下的生活圖景。她天真地以為跟隨男爵離開畸形秀后,會獲得尊敬與自由,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但男爵虛偽的愛情不會讓她夢想成真,也不會令其成功進入中心地帶。在男爵多次誆騙下,維納斯再次經歷空間位移,站到了醫生的測量臺上。她被人利用,直至被解剖,從未真正融入以白人男爵為主導的中心地帶。“文化模擬的核心在于提取文化對象中具有共性的抽象元素”[14],帕克斯從眾多非裔女性中提取維納斯作為具有共性的代表,完成對試圖進入中心地帶卻飽受欺辱的非裔群體的側寫。
在抽象空間層面,維納斯對自我“界限”的不斷跨越再現了非裔女性的身份困境。基于符號域的抽象性質,“邊界”不僅能夠被實際地感受,而且也可以被抽象地理解:“符號學個體化的主要機制之一是邊界,邊界可以定義為第一人稱形式的外部界限。”[4]131 維納斯對“身份界限”的不斷跨越勾畫出了以維納斯為縮影的諸多非裔女性的心理困境。起初,維納斯作為來自非洲的異國舞者,對其非裔女性身份保持認同與自信。白人商人對她的許諾使她更加堅信自己在畸形秀的舞臺上可以“一夜之間成為公主”[6]38。但一切幻想卻在長期壓榨與欺辱后逐一破滅。在畸形秀所遭受的身心霸凌成為一段難以抹去的痛苦回憶,這樣的創傷記憶在她身上譜寫的“身體文字會毀壞其建立身份認同的可能性”[9]282,令她對自我身份界限認知逐漸變得模糊。最終,在法庭上,她懇求:“如果我有不好的標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清除它?……我可以洗去我的黑暗印記。我黑著身子來到這里,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白著離開。”[6]123 這時的維納斯已徹底跨越非裔女性對個人身份認同的界限,她憎惡自己的膚色,誤認為傷害自己的白人是“最好最誠實的人”[6]123。盡管她最后短暫逃離畸形秀,但是長久的傷害難以讓她穿回原來的界限,擁有曾經的自信。最終,她被愛情蒙蔽雙眼,默認男爵的冷漠和虛偽,致使身份徹底流散。維納斯自身界限的不斷跨越最終導致她走向死亡。帕克斯在重塑這一故事時,將維納斯認定為一個復雜人物。在與蒙特(Monte)的采訪中,她說道:“我可以把維納斯作為一個受害者,為她寫一個兩小時的個人史詩。但是她是多面性的,她無辜、美麗、聰慧,但的確也是同謀。我所寫的世界就是我經歷的世界……這只是我們現實的一部分。作為黑人,我們被鼓勵狹隘并簡單地解決問題。但我們應該得到更多。”[12]39 這樣具有矛盾感的人物塑造,以及最終朝向消極“界限”的跨越看似令維納斯成為殺害自己的“同謀”,但實際上,在這一戲劇人物的符號域中,她對“界限”的穿越展現了主動與被動并存的復雜性,隱晦地復現了作為非裔女性在遭受殖民者的掠奪與壓迫時所面臨的心理選擇困境。因此,將洛特曼對“界限”的揭示遷移到具體的文本分析實踐時,可以發現劇中人物在心理空間界限穿越的多個節點,進而覺察劇作家已悄然以藝術文本的形式讓非裔族群聚焦到更為深刻的問題上:解決種族問題不應止步于表面,而需要正視歷史的多面性,找到問題的根源,這才是書寫歷史的終極意義。
以洛特曼對藝術文本空間的延展性視角,跨語境分析《維納斯》中的空間性,作品的文化模擬被擴展至更為廣闊的世界圖景。在《維納斯》這一符號域中,以維納斯個人建模為出發點,中心與邊緣的顯著差異與人物身份界限的不斷跨越、相互作用、彼此關聯,擴散地模擬出現實世界中非裔邊緣族群在以白人為主導的中心社會中面臨的雙重困境。劇作家在該空間模擬的引導下,對情節與命運的意義進行了闡釋,實現了有限文本的無限釋放,達成了該段歷史圖景的意義復現與迸發。
結 語
在《維納斯》中,帕克斯通過戲劇形式將維納斯的一生再度引入公眾視野。作為一位非裔劇作家,她承擔了“重建歷史事件,以填補由于排除任何非裔美國人的存在而造成的歷史缺失或漏洞”[15]的使命,創作了這部具有復雜敘事性的現代戲劇。本文將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跨語境地應用于該戲劇文本研究中,發現動態文本觀可以引導讀者和觀眾系統理解該劇中不同層級的藝術結構與象征的協同運作。劇中創新的交際模式有效傳遞了劇作家的個人情感與藝術追求,通過繪制“世界圖景”的空間模擬,再現了非裔群體作為邊緣人的困境,以維納斯為代表的非裔女性身份的離散,實現戲劇文本意義在時空上的拓展,使原有的歷史意義得以衍生和復現。作為“歷史事件的孵化器”,《維納斯》不僅激發了讀者和觀眾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意識,而且鼓勵人們回望歷史,正視歷史,思考歷史的真實性,以實現歷史書寫的最終意義。
參考文獻:
[1]Parks, S. L. The American Play and Other Works[M].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5.
[2]康澄. 文化及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研究[M]. 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6.
[3]Tamm, M., and T. Peeter, eds. The Companion to Juri Lotman: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4]Lotman, Y. M.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McCormick, S. "Witnessing and Wounding in Suzan-Lori Parks's Venus"[J]. MELUS, 2014(2).
[6]Parks, S. L. Venus[M].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7.
[7]Jiggetts, S., and S. L. Parks. "Interview with Suzan-Lori Parks"[J]. Callaloo, 1996(2).
[8]余紅兵. 文化記憶的符號機制初論[J]. 山東外語教學,2019(5).
[9]阿萊達·阿斯曼. 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M]. 潘璐,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0] Tamm, M. "Introduction: Juri Lotman's Semiotic Theory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in Cultural Semiotics, Ed. M. Tam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9.
[11] Kornweibel, K. R. "A Complex Resurrection: Race, Spectacle, and Complicity in Suzan-Lori Parks's Venus"[J]. South Atlantic Review, 2009(3).
[12] Griffiths, J. L. Traumatic Possessions: The Body and Memory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and Performance[M]. Charla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9.
[13]隋紅升,周寧. 《維納斯》對非裔女性身體刻板形象的解構與女性氣質重塑[J]. 當代外國文學,2021(2).
[14]康澄.“空間模擬”思想: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的一種獨特方法論[J]. 當代外國文學,2023(3).
[15]Schafer, C. "Stag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Suzan-Lori Parks's Venus, In the Blood, and Fucking A"[J]. Comparative Drama, 2008(2).
(責任編輯:馮靜芳)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1 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重點項目)“當代美國非裔戲劇中種族困境的數字人文研究”(項目編號:L21AWW00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