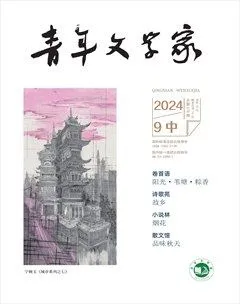我的創作人生
明年這個時候,我能不能出去旅行或者回老家將息,我并不知道。如果把一個個無奈的人生都歸于客觀,說是一個害人的病菌阻擋了彼此前行的道路,那只能說我們地球人已經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而我的生命也啟動了衰退的旅程。
棗樹開花結果不久,長長久久從泥地里睡醒過來的蟬兒動用隨身的樂器,在午后不停地嘶鳴,盡最大能量釋放壓抑的情緒。馬棗與團棗,一個形體苗條,一個形體圓粗,就像年輕男女;成熟后,一個酸一個甜,就像一對廝守多年的夫妻,經常對峙,卻常常留有后路。
小的時候,哪兒會區分什么雄蟬和雌蟬,抓到一個算一個。用棉線縛住它們的細手細腳后,它們再想振翅欲飛,恐怕就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了。小孩子玩心十足,自然沒想到這些到手的小生命是多么來之不易。等從書本中得知,那些會鳴能鳴的都是雄蟬,而雌蟬的樂器構造不完全,根本發不出聲音時,我已快速地長大了。在了解了蟬的“悲涼一生”后,我如鳴蟬一樣,盡做些在悶熱的季節里極其喧囂的事。
其實,人生就是對時光的一段段反射。孩提時,你在老家的泥地里逶迤爬行,從大人的腳印中多多少少還能找到痕跡。等漸漸地長大了,告別了村口蜿蜒的小溪,走出了重重大山,爬過道道危嶺,目睹了各種車輛行駛后留下的轍痕,才知道一次次負重是人生一幕幕重頭戲,而父親的獨輪車只能承載與他體重兩三倍的重量,只能承載兒孫的少年。少年的記憶里有無數夢幻一般的故事,他已經沒有精力牽掛了。最后,他以完全躺倒的方式完成所有在人世間的游戲,雖有種種不舍,祈望晚輩走好山外的每一步卻是由衷的,是發自內心深處的。
要說人生的內容,不外乎是堪稱高貴的思想與普通的實踐。就作者而言,許多許多的時間與光陰都融入了一串串文字當中。說是完成日更也好,說是傾注文學創作實踐也罷,除了天賦外,恐怕更多是磨煉,包括思想上和藝術形式上的繼承與創新。
不管你怎么談論文學,如何勇敢地在文學道路上行走與奔跑,文學女神總是遠遠地站在你的前方,笑盈盈地向你招手,而等你接近她想與她牽手的時候,她又馬上跳開,又站在前面向你發出新的邀請。學無止境,寫作也如此。在清醒地知道了這一情況后,面對自己撰寫出來的作品,只能說與過去的文章相比有進步卻不能輕言有多大深耕,只能說在寫作手段上有所精進卻不能輕言有多么純熟。因此,我本人最多是一個業余級的寫手,說自己的人生是寫作的人生,只是站在老家的樟下山上把自己的身體略微抬高而已,對別人、對這個世界而言,并沒有什么可參考、可借鑒的實際意義。
如此說,一點兒也沒有自謙的意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局限性。等你歇下雙腳,自鳴得意的時候,人家已整理好所有道具,又踏步向前了;等你把習作本陸續上交的時候,人家的創作已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我想,文學創作既是一場無人在現場“加油”的比賽,也是一場并不存在敵我雙方你死我活意義上的競爭,更多是學識上的比賽,才藝上的競爭。而在學識與才藝的背后是文學思想的沉淀,藝術視野的擴大。天有多大,心要有多大,一個人的視野大小常常決定一個作品的藝術生命。反之亦然,一個作品的背后可以準確地看到一個作者有別于他人的思想學識和藝術才能。
沉淀的目的是讓人創新,視野的擴大是促人清醒。
一個來自農村的懵懂少年,在求學和寫作道路上不斷地奔跑,毫不顧忌身邊無數個溝溝坎坎和曲曲折折,想起來都能令自己發笑一陣子。這是不是意味著自己日漸覺悟,知道其中的深淺,也象征著從此以后必有大的作為?我還真的說不清楚。
自二十一世紀伊始,我已經走過二十余年了,其中在簡書平臺上又走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按照目前的態勢,估計還能行走幾個若干年。真到了自己不想寫的時候,再來回望吧,再來總結吧。但愿在那個生機勃發的年代,還有大文學的存在,還有全民文學熱的風潮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