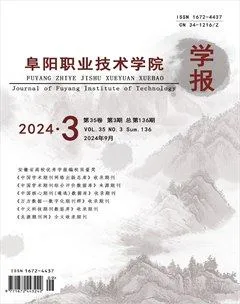中國古典美學“奇”范疇探究
摘要:“奇”作為我國古代美學范疇之一,南朝后在《文心雕龍》中被確立為一種文學風格,后又與儒、法兩家及老莊思想不斷交流融合,以“奇正”開文學批評實踐先河,使“奇”正式成為一種文論范疇。“奇”兼有“美”和“味”的義項,也具廣泛而深厚的互文性,在書論、畫論及人物品評方面均有所涉及,在其隨后的發展演變中對各體文學體裁的創作實踐也產生重大影響。從哲學及美學兩種不同的維度完整全面地把握“奇”的內涵與意蘊,以進一步探索“奇”在古典詩歌以及小說文學實踐中所表現出的美學價值。
關鍵詞:奇;演變;美學價值;美學內涵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437(2024)03-0051-07
“奇”作為中國古典文學重要范疇之一,其含義不斷發展變遷,歷經多重演變,可將之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發展的縮影。范疇研究其意義在于,“范疇研究通過對古代個體范疇的集中性研究,把握其內在演變規律和外在關聯對象,運用‘歷史和邏輯的統一’的思維方法,展示中國古代文論內在的生命力、延展力和粘連性、豐富性,在區別于西方文論的同時,將傳統文論的審美價值傳遞到當代文藝與文化研究中。”[1]與西方強調利用概念以把握理論系統的方式有所差異,我國古典文學研究實踐活動,往往強調個體的領悟與感受,話語體系的使用常包含較多直觀經驗性質的內容。古人借助天地自然,運用觀象思維以山水雄奇比喻文章打破傳統閱讀慣性,提出文章“尚奇”的觀念。劉勰《文心雕龍》提出的“觀奇正”奠定了古代文論“奇”范疇的發展基礎。明代陶望齡將劉邵《人物志》中的“偏至”思想引入文論,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繼承和創新,提出“偏嗜必奇”,逐漸成為后世評價文章的準則之一,因此可以說,“奇”范疇為我國古典文學的發展開拓出一定話語空間。
一、“奇”范疇的美學內涵
“奇”范疇的產生既具有豐厚的哲學淵源,也有著豐富的美學意蘊,其中儒、法、道三家思想的相互交流融合,使“奇”具有了豐厚的哲學基礎,其美學意義便蘊藏于不同時代各類審美形態的內涵闡釋中。
(一)哲學淵源
“奇”含義的抽象化代表著哲學之“奇”思想的興起。“奇”的哲學淵源最初可以追溯到《老子》“正復為奇,善復為妖”[2]246思想中表現出的“奇”,具體即指一如既往地堅持“道”并有所收益,這也是“奇”哲學思想產生的一大前提。老子的“奇”論對于哲學奇正觀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說文解字》將“奇”解釋為具有“異”特征的“異也”和“不耦”兩義,在老子提出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思想中,“奇”即為前者所代表的奇異、驚奇、奇妙的意思。“以奇用兵”意味著沒有兵、沒有戰,實際內涵為“不武”,意為不以兵器示強,武器僅以自衛為前提,實際意義還取“不敢”,即避免不必要的戰爭,提倡哲學中的兵法智慧。在此基礎上先秦兵家提出“奇正相變”,認為要掌握奇正變化的規律,奇正相生,以奇制勝。而文學創作中的謀篇布局與兵家的排兵布陣相類,因此,兵家提出的“奇正相變”為后人“奇正觀”的文論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
老子認為,“奇”有“非道之奇”與“合道之奇”二分。他將“合道之奇”歸入“正”的范圍,批判“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2]241-242的“非道之奇”。《老子》第五十八章“正復為奇,善復為妖”體現了“正、奇”與“善、妖”間的相互轉化,表現出老子的辯證法思想。有“正”即有“奇”,體現出“奇”在老子哲學思想中的存在價值。與此相類,“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中,“正言”往往通過“反言”或“奇辭”體現出來,對于這種用“奇辭”來表達“正言”的“合道之奇”,老子也持肯定態度。
莊子與老子有所不同,莊子主張“齊物論”,萬物歸一,世間萬物的存在都有其自身價值。莊子還肯定得道的“奇人”與“奇語”,“奇人”指形態外貌奇異的人,在內心修養達到道的境界甚或畸人(畸于人)卻“侔于天”時,莊子并不作武斷批駁。“奇語”指一種合道之言,是有道之人“發之于中必形于外”的結果。這里,莊子對“奇人”“奇語”中“奇”的態度表現出其與儒家明顯不同的態度,為后世人們追求個性自由與天性解放提供了有利前提與理論基礎。同時,受莊子哲學思想的影響,“美”與“丑”在中國古典哲學范疇中讓位于表現出具有超越性特征的“奇”范疇。
關于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奇”,各學派說法不一,并且在其內部也呈多向動態發展的姿態。儒家對“奇”的態度有一個調轉改變的過程,儒家崇尚禮法“尊正抑奇”,為維護統治者利益,宣揚正統思想,在價值選擇上首先表現為不取“奇”。儒家認為“奇”是對世俗禮法既有行為準則的背離,從新工藝、新技術上創新從而破壞了傳統禮制,對正統言語思想的打擊以及對中庸觀的種種背離等[3]。直至戰國末年,儒家對“奇”的批評態度才有所松動,出現視“奇”為中性詞來使用的情況。南朝文論批評家劉勰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4]573表現了個人對孔儒思想的肯定。文學領域中,彥和受到法家思想“以正合,以奇勝”的影響,提出“觀奇正”,將奇正關系作為評價文章的標準,因而能夠在此看到信仰儒家思想的他對“奇”旗幟鮮明的肯定態度。但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篇中評價《楚辭》“奇文郁起”“詞賦之英杰”時,既肯定其語言以“奇”為特征,體現出發展創新性,同時也強調要避免“逐奇而失正”(《文心雕龍·定勢》),其對過分追求“奇”的做法持批評態度。
(二)美學溯源
“奇”范疇的美學溯源可以追溯至古人對自然界的高度崇拜。先民睜開雙眼看到世間萬象,誕生了如盤古開天辟地、后羿射日、女媧補天等一系列神話傳說,“夫神話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則逞神思而施以人化……”[5]今人所言的種種不可抗力因素,如山洪、風暴、地震等,使古人產生無盡的恐懼心理,古人便試圖依靠神明,借助占卜巫術諸種方式求得幫助,獲取對于“祥瑞”“星象”“災異”等“自然奇象”的心理慰藉或對此尋求合理解釋。《易傳·系辭下》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6]直至后來產生圖騰崇拜,流傳千古,匯聚而成眾類“尚奇載體”──圖騰崇拜成為古人奇思審美的物質載體。
戰國末期,屈原《離騷》“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7]20“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7]34便具有巫術痕跡,屈原詩歌中所具有的“異采”特色,與儒家官方意識形態規定的“雅正之美”相去甚遠,屈原實指文質方面的奇美,完全脫離儒家經義禮教約束,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篇中對此總結為異乎經典的“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8]四大異彩特點,又為“奇”開辟了不同的審美格局──巫鬼文化拓寬尚奇場域。
兩漢魏晉時期,人物品鑒之風大為盛行,劉邵在《人物志》中以“奇”作人物品評,他認為在品評人物時存有七大陷阱,可能致人誤入歧途。其中提到“觀奇有二尤之失”[9],指在觀察奇才時不能夠很好地分辨出尤妙之人與尤虛之人,“尤妙之人”即“含精于內,外無飾姿”之人,“尤虛之人”即“碩言瑰姿,內實乖反”之人,含徒有其表之意。單看“碩言瑰姿”誤指為奇才,導致“拔奇而奇有敗”,選拔重用了“奇才”卻導致失敗,這種重內在之奇而非形體之奇的尚奇觀念也深刻影響了后起的書論畫論的不斷豐富發展。隨著人們對“奇”認識的加深,品鑒人物之“奇”逐漸延伸至藝術領域,同時,也體現出“奇”的互文性特征。
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大量畫論作品,“‘氣’者‘生氣’,‘韻’者‘遠出’。赫草創為之先,圖潤色為之后,立說由粗而漸精也。曰‘氣’曰‘神’,所以示別于形體,曰‘韻’,所以示別于聲響。‘神’寓體中,非同形體之顯實,‘韻’裊聲外,非同聲響之亮澈……”[10]謝赫在此認為繪畫要旨在于追求神韻,而不求其表露于外形之中,如此才能達到那種奇美的境界──這是首次在繪畫中將老莊玄學“貴無”思想引進藝術領域。繪畫藝術與老莊玄學思想結合從而達到奇美的審美境界,不失為“奇”的又一創新變遷。在六朝書論中出現的“字外之奇”一說,與謝赫“神韻新奇”說類似,都在強調超越形似,實現神韻之奇美。隨著書畫作品風格與內容的日益豐富,書論、畫論思想發展逐漸成熟,“奇”范疇的影響范圍也在不斷擴大、深入。
“奇”作為中國古典美學范疇之一,涉及到中國古代文化形態的諸多方面,同時也逐步影響了古人的文學創作與鑒賞,對后世產生較為深厚的理論應用價值,也為自身文學審美內涵奠定了一定基礎。
二、“奇”范疇的演變
春秋時期,禮樂松動王權式微,“奇”受《孫子兵法》《莊子》《離騷》等作品影響,價值內涵轉向至此發微。《孫子兵法》“以正合,以奇勝”[11]思想打破了“奇”“正”兩相對立的局面,“奇”轉而成為傳統戰術思想“正”的變相形式,體現出“奇”的正面價值內涵,重新確立了“奇正相生”的關系,進一步影響了后世劉勰、鐘嶸詩論中對“奇”的肯定態度。
(一)從社會價值到文學審美范疇的變遷
“奇”至周代開始作為社會價值范疇,此時初涉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演變。周朝為使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實現進一步鞏固,以維護官方統治秩序的正統思想作為主流價值觀,但隨著禮崩樂壞,傳統秩序新變,價值取向開始趨于多元,“奇”作為“正”“常”傳統禮治秩序的對立面出現,沖擊了封建正統思想,被視為處于傳統禮法秩序之外的消極思想,是一種破壞當時社會秩序的負面社會價值判斷。“奇”的價值轉向首先受到《莊子》思想和屈宋作品的影響,“奇”逐漸完成由社會價值范疇到文學審美范疇的轉變。
道家思想與屈宋作品賦予了“奇”一定美學內涵。一方面源于莊子自由浪漫的文風特點,另一方面從莊子個人對當時社會的批評可以看出,莊子對人物品評的角度不拘禮法、大膽創新,促使“奇人”成為超越世俗的理想人格,也體現出撼動世俗的精神力量。南朝文論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篇伊始便有“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4]44《離騷》中奇異浪漫的豐富奇辭表現出濃厚的藝術感染力,被認為是古代奇崛詩風源頭之一,橫絕千代,令后人難以并駕齊驅。如屈辭表現的種種服飾之“奇”,具體有“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7]2、“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7]13,主要借助香草意象運用比興想象,寄托了自身高潔品格。宋玉在《高唐賦》中借《離騷》體現的奇偉藝術想象,“縱縱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12]意象上常取奇事怪物,手法巧用修飾夸張,以山水物色自然景象之奇體現出奇崛的審美趣味。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結合具體文學創作實踐對“奇”作出進一步闡釋,系統地體現在劉勰個人倡導的文學創作與發展的具體要義中。《文心雕龍·定勢》篇“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逐弊” [4]362,提出“執正以馭奇”和“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的文學創作風格及方法要求;《辨騷》篇提到“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4]51的文學創作目標;《通變》中可見到關于“望今制奇,參古定法”[4]354的文學創作發展理念。《文心雕龍·物色》中“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于適要,則雖舊彌新矣。”[4]524此處構成“奇巧”,事物具體可感,為人勾形狀貌。但因創作者的思緒無邊無際,這時如若抓住事物根本,“因方借巧”“即勢會奇”經過巧妙的構思,創作內容依舊能實現歷久彌新,體現出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的辯證文學發展觀。同時關于文學創作的欣賞與批評活動方面,《文心雕龍·知音》篇“四觀奇正”[4]554指出了創作實踐中新奇與平正的辯證關系。“奇”的價值內涵逐漸滲透于文學審美空間。
(二)由局部呈現到整體創作的進一步發展
南朝批評家鐘嶸不滿齊梁腐糜文風,將表現出卓越正面價值的“奇”內涵作為品評五言詩歌的一大標準。主要從詩歌創作方式與風格方面將“奇”與儒家經典中的“正”割離,擴大了“奇”在詩學范疇的內涵,提高了“奇”的獨立地位。
鐘嶸主張少用事,提出直抒胸臆的“直致之奇”,評劉楨“仗氣愛奇,動多振絕”[13],多推崇情感自然流露,不拘個人才性的“奇”志自由抒發;認為張協“文體華凈,少病類。又巧構形似之言。”[14],“凈”字足以見出鐘嶸對少于駁雜繁復,不加雕琢“直致之奇”的審美追求。陸機詩句“準古法”“尚規矩”從而表現出多凝重、詩情繁冗的特點,鐘嶸認為其強調詩歌格律,有損于詩歌自然“直致”,直言道“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15]200鐘嶸主張詩歌在于真實情性的自由抒發,推崇表現個人真情,同時繼承了莊子與屈原、宋玉“奇”觀念,認為“奇”是超脫世俗,甚至推及“雅”的高度,如在《詩品序》中評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15]175贊賞其文辭奇崛、卓爾不群的特點。
唐宋詩論中,“奇”又進一步發展到詩歌創作全過程、各層面的整體實踐要求中,即從詩歌創作方式、風格進一步延伸到詩歌的選材、運思、句法、造語、用韻等方面,由點及面,不斷完善。中唐詩人皎然寫道:“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后,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16]皎然認為詩歌奇句的生成規律具有苦思而得自然的特點,主張創作“慘淡經營”,站在詩歌整體觀上把握煉字、煉句、煉意的多重原則,經過一番苦思冥想,文字實現化工之奇不至陷入詭怪窠臼。“奇”在詩論方面也對詩歌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創作追求由“奇”至“平”的調轉
宋詩前期受樂天、義山影響,后又學韓,最終造就獨特文風。其中詩論以黃庭堅為代表,提倡“遇變出奇”被時人奉為圭臬,遂使整個江西詩派尚奇成風,以致后來形成一味追求“奇崛形式”的單一格局。過猶不及,宋由此轉入“平淡”“自然”的詩風境界。
如陶詩《飲酒(其五)》中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語言初看平淡,但富有奇趣。陳寅恪認為陶淵明“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古今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17]五柳先生思想廣博多元,含有同老莊思想相類于世俗生活中保持完善自我獨立人格之精神,也含有“生命”課題中深邃幽微意蘊之求索,更具有對“自然”哲學思想的深刻體悟。其中五柳先生對于“自然”的追尋,既是尋求帶有“自由”意味的自然,也體現為追求“自然的文學”。保持個人的本性自然,尊崇詩歌貼近人生實際,詩句中常常平中見奇,語言少于雕飾,但意蘊雋永,又合乎性情,自然流露出詩歌“奇美”。
這與王安石“看似尋常最奇崛”有異曲同工之妙,語詞不艱澀,稀松平常間見出語境的淡美,少于雕飾多自然,組句言平意深,煉字可達意勝,不以逞奇當先。如此也在宋朝文論中拉近“奇”與“平淡”及“自然”的關聯,動搖了前期韓孟詩派“奇”“平”失衡的局面,此類以“平淡”“自然”求矯“好奇”之弊直至明代仍有所保留。
三、中國古典詩歌與小說中“奇”的美學價值
為適應維護儒家傳統話語系統的要求,文學創作多表現出具有典范代表特征的“雅正”之美。然而由于作品自身傳播的需要以及內容創新發展的要求,無數文人墨客選擇打破傳統藩籬,對中國古典詩歌產生的“奇美”創作追求便為其中體現之一。“奇”在中國古典詩歌、小說中都表現出一定的美學價值。
(一)“奇”與中國古典詩歌
在宋以前較少涉及對“奇美”的討論,自宋以來,古典詩歌的文學批評才漸出“奇美”風尚。詩歌“奇美”即要求“文”與“意”相得益彰,不以逞奇為美,通過“遇物而奇”“遇變出奇”和“破體求奇”三種方式表現詩歌奇美。
1.“遇物而奇”
“遇物而奇”是指詩人所描寫的自然物象或生活事件自然地引起作者情感抒發,不在于詞藻的奇譎夸飾。創作主體與審美客體間,審美客體對創作主體產生審美感召,因而,創作主體為審美客體作用,創作主體的審美情感受到外界自然環境刺激,形成自然純粹的審美體驗,由此產生創作主體的自然奇思,進一步實現文學創作活動。如杜甫詩歌《子規》[18]209:
峽里云安縣,江樓翼瓦齊。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凄。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詩人客居到一云安縣,江邊閣樓上屋瓦整齊排列,兩邊的樹木郁郁蔥蔥,似乎要將閣樓包裹住,杜鵑鳥兒的啼叫聲不絕于耳。春風輕輕拂過,草木隨風搖落,只叫人覺得此刻的夜色更加凄涼。作客他鄉的人兒哪經得了這番景致,一時間思鄉愁緒涌入心田,從心底開始細細蔓延。可是那鳥兒恍若通得人性,故意傍人低飛,惹人煩惱。詩人描繪自己客旅他鄉,畫面層層遞進,空間層次分明,由低見高、由遠及近、由靜到動,同時調動視聽感官,極富有動感。
因周遭自然景致,觸發詩人個人情志,于是便將這平日間的耳聞目狀、實景實歷、所見所聞所感一一抒寫描摹,映現出一系列自然的真情實感。題為《子規》,但僅于全詩第四句和第八句兩處有所描寫,用墨雖少但詩人客旅愁思卻已化于紙上,遇物而奇,奇景映奇情、美景照美情,表現出詩歌“奇”“平”兩端達到和諧平衡狀態的奇美意蘊。
2.“遇變出奇”
“遇變出奇”則是從文學通變的角度,講究詩歌創作手法的新變,方式上多采用語法顛倒、典故化用、風格新變等以達到詩歌的奇美意境,以求詩歌的情感意蘊與外在形式達到具體而統一的奇美文辭風貌。如杜詩《月夜憶舍弟》[18]146: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避,況乃未休兵。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一句語法顛倒,順句實為“從今夜露白,是故鄉月明”。王彥輔說:“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19]運用陡峭的空間形象和新鮮奇妙具有生命力的詩歌語言,對語法結構進行有意識地破壞,強化詩歌的藝術張力。
一、二句言兵后中原荒涼,唯聽邊疆獨雁哀鳴。五至八句意味深長:一弟分散,與眾弟皆分散,分散而無家,“無家問死生”唯有寄書去,書信尚未到達,況且又“未休兵”,音書絕,死生不可知,詩境自然漸出。再說三、四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倒作使尋常之語不再熟悉,變得新奇陌生。調用話語的阻拒性特征,使人們對平日間素常之物的感受發生二次加深,宛轉曲折,更映襯出濃厚情思。運用語言的陌生化,產生出其中本質性藝術效果,同時倒作后仍保留了詩歌的韻律節奏,錯落有致,延長了藝術的感受性,奇正配合相當,意蘊概出,使得詩歌奇美直瀉無余。
3.“破體求奇”
“破體求奇”主要體現在詩歌的形式方面,是宋詩求奇求變的方式之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宋詩開山祖師梅堯臣,他將散文代入詩歌,以形式強調內容。梅詩通過描寫現實客觀景物,表現個人思想情致的自由抒發,具有日常化、親臨感。如梅堯臣的《魯山山行》[20]: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
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
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
人家在何許,云外一聲雞。
首句詩人抒發自己熱愛山野的志意,連綿的魯山,千峰奇拔,高低起伏無窮無盡。一路走來,奇峰峻嶺變換無窮,獨自沉醉于小徑之中的美景,不知不覺走入魯山深處,迷失了方向。不覺間薄霜漸漸消融,熊開始爬到樹上活動,空蕩的深林里,小野鹿愜意地在溪旁飲水。從遠處傳來啼鳴,可能會有住家在那邊吧。詩人進入山中,情志滿懷,描寫了自己真實的一段游山歷程,將情感、見聞一一巧妙和諧地融于散文化的詩句中。如同一位老友,娓娓訴說這一山路歷程,把這富有美感的自然畫面帶到讀者眼前,詩中的偶句“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又表現出具有律動節奏的技巧美,“奇”而不失“穩”,二者相輔相承,達到一種“奇”而又“穩”的藝術境界。梅詩也同樣具有奇險與平淡于同一首詩內的完整表現,這種開闊的創作思維與創新意識,也進一步開拓了宋詩的審美空間,從而促進了宋詩發展。
詩歌奇美要旨實際不在于肆意浮華的偏澀行文,是一種實現奇美與自然統一后達到的藝術境界。古代詩歌中的奇美之感,可以說是由創作主體與審美客體二者共同作用產生的結果,不單于形式層面獲得美感,實現字句之奇與意蘊之奇兩者間的辯證統一,詩歌內容與意蘊達到平衡尋及界點奇美特征自然俱出。
(二)“奇”與中國古典小說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小說同詩歌、散文相比,可謂“后起之秀”,因而小說中的理論批評范疇常常會從詩文理論范疇借鑒而來,小說批評中的“奇”也來源于詩文理論批評術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及唐代傳奇尚乏現實色彩,對于唐傳奇來說,雖然同前代小說創作相比,已初具文學創作自覺意識,開始不斷向現實深入,但總體上也呈“以幻為奇”,以“奇幻”取勝的創作規律,認為幻奇是小說的主要特點。同時,這一時期主要借小說發揮勸懲世人的教育功能,帶有古典主義色彩的至美境界。
《搜神記》被認為“序鬼物奇怪之事”,蒲松齡《聊齋志異》也有“才非干寶,雅愛搜神”[21]之說。“搜神”意即廣泛搜集神異鬼怪之事,因此其故事情節構思往往與現實生活相去甚遠,具有強烈的奇幻色彩。《搜神記·左慈》描寫一故事:因在曹操舉辦的宴席中缺少吳國鱸魚,左慈當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22]12片刻就從“銅盤”里釣到鮮活的鱸魚,接著又迅即買到魯國的生姜返還,后來又僅用一罌酒與一片肉脯供近郊的百余人大快朵頤了一番,“放乃赍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22]13
再如,《搜神記》第二十卷中《病龍雨》一則講述: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于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22]353。
一位農夫在龍洞祈到雨后,打算去祭祀表示感謝,孫登卻言:“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龍當時背上生了一個大疽,聽到此話,便變成一位老翁,前求醫治,并表示醫好后一定有所報答,孫登將之治愈不久,果然下起大雨。同時,大石中還裂開一口深井,井水清澈湛然。由此可見,彼時志怪小說通過短小精悍的故事,簡單的情節,形成奇妙造意,具有奇幻色彩,騁心游目富有理趣,體現出善惡是非的價值判斷,保留了小說“尚奇”價值。
在此創作基礎上,唐傳奇表現出一定進步性,實現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地位,為后世小說的敘事架構提供了觀照范式,令后世文學的再創作獲得大量素材和藝術啟發。明代胡應麟有語“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23]不同于志怪小說文字簡省的“叢殘小語”,唐傳奇開始具有自覺的文學創作意識,唐中期李復言所撰傳奇小說《續玄怪錄·薛偉》篇,故事情節、敘事結構和敘事技巧多表現出奇美色彩。小說內容先以敘事者的口吻介紹薛偉其人身份,其因病“忽奄然若往”二十日后“忽長吁起坐”,此時敘事視角陡轉,將薛偉“既出郭”以后,人形化魚的游歷過程開始以第一人稱進行詳盡細致的描畫,從“策杖而去”“跳身入潭”,經“河伯宣詔”終“人形化魚”,薛偉化人身為紅鯉痛快地在水里暢游數日后,因“貪食釣餌”,落入河邊釣魚的同僚掌中,雖“大聲呼之”,可只見得“口動,實無聞焉”,最后魚頭在同僚、仆人的眼下被廚司親手斬掉,“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詔爾”,眾人聞后大驚,“三君并投膾,終身不食”,三位同僚決定今后再不吃魚,結尾薛偉漸漸病愈,“后累遷華陽丞乃卒”[24]85-86。
這是一則想象奇特且技巧純熟的傳奇小說,早在前文薛偉開始正式回憶前,已有其自述因病“不知其夢也”,整個游歷過程全部籠罩在夢的敘事下,將夢境帶入現實,似真似幻,虛實難辨,更增強了故事的奇幻性。文中還有如“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茍非其好,則昧通波……恃長波而傾舟,得罪于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于明……”[24]86,這是薛偉化人形為魚身前,河伯告誡它的內容,預敘了化為紅鯉的薛偉終會被同僚擒獲,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使故事到達高潮。作者在此處運用預先敘事的方法設置懸念,又增強了故事的吸引力,暗含諷喻意味。故事情節離奇多設懸念、敘事結構奇幻“引夢入實”、敘事技巧奇特豐富多樣,使讀者身處于完整的小說空間內。
至明中葉神魔小說《西游記》出現后,小說由志怪傳奇一類“以幻為奇”的審美趨向開始向“無奇之奇”變化,從而也促進了近代美學的萌生。
“無奇之奇”的美學意蘊主要體現在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畫上,強調小說人物個性的客觀真實,主要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現出虛擬的小說空間無限向真實世界伸展。“四大奇書”之一《金瓶梅》對日常生活細節上的精雕細琢俯拾即是,如第十五回寫正月十五眾人看花燈一幕:
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兒摟著,顯他那遍地金襖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蔥來,帶著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著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的瓜子皮兒,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簷下掛的兩盞繡球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著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著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這首里這個婆兒燈,那個老兒燈。”[25]
文中對潘金蓮的服飾、外貌、動作、語言作出細致刻畫。潘金蓮走出家門,此時從封閉的家庭空間置身在人群鬧市當中,呈現出人物不同的精神風貌、性格特點,體現小說人物的日常百態,人物塑造更加立體多元。潘金蓮與眾人出門游耍時,同玉樓一起嬉鬧非常,興致盎然,“摟著”“露出”“帶著”“探著”“吐落”“嬉笑”等一連串多個動詞,浮夸的動作表現,令讀者感受到潘金蓮隨意自由、自我張揚的生命狀態以及她潑辣輕浮,喜愛熱鬧的性情特征,順次叫到三位姐姐指看花燈,又顯她俏媚活潑、可愛非常。小說充分重視細節刻畫,將潘金蓮的神情表現、動作舉止進行逐一真實細致的描摹,以細微真切的描寫打動讀者,并且具有日常生活的真實性,以細節描寫實現藝術真實,人物活靈活現躍然紙上,體現出“奇”與“常”間的藝術張力,白描的運用,又巧妙增設出“無奇之奇”的審美意蘊。
參考文獻:
[1]趙玲玲.逸范疇的審美空間[M].廣東: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2.
[2]朱謙之.老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7.
[3]魏東方.中國哲學中的“奇”范疇發微[J].洛陽師范學報,2023(01):25.
[4]劉勰.文心雕龍[M].王志彬,譯.北京:中華書局,2012.
[5]魯迅.魯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2.
[6]周振甫.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257.
[7]楚辭[M].林家驪,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8]劉勰.文心雕龍注:第1卷[M].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46-47.
[9]劉邵.人物志[M].梁滿倉,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22:155.
[10]錢鍾書.管錐編:第4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9:1365.
[1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孫子》注釋小組.孫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7:33.
[12]宋玉.宋玉集[M].長沙:岳麓書社,2001:58.
[13]鐘嶸.詩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10.
[14]徐達.詩品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59.
[15]張懷瑾.鐘嶸詩品評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16]皎然.詩式校注[M].李壯鷹,校注.北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39.
[17]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M].北京:中華書局,1962:358.
[18]杜甫.杜甫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王得臣.歷代筆記小說大觀:麈史·候鯖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2.
[20]朱東潤.梅堯臣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55.
[21]蒲松齡.聊齋志異“聊齋自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2]干寶.搜神記全譯[M].王一工,唐文書,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3]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371.
[24]牛僧孺,李復言.玄怪錄·續玄怪錄[M].田松青,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5]秦修容.金瓶梅:會評會校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