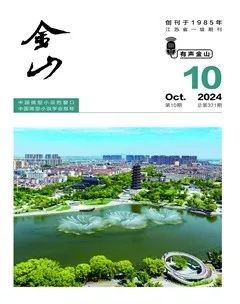侉老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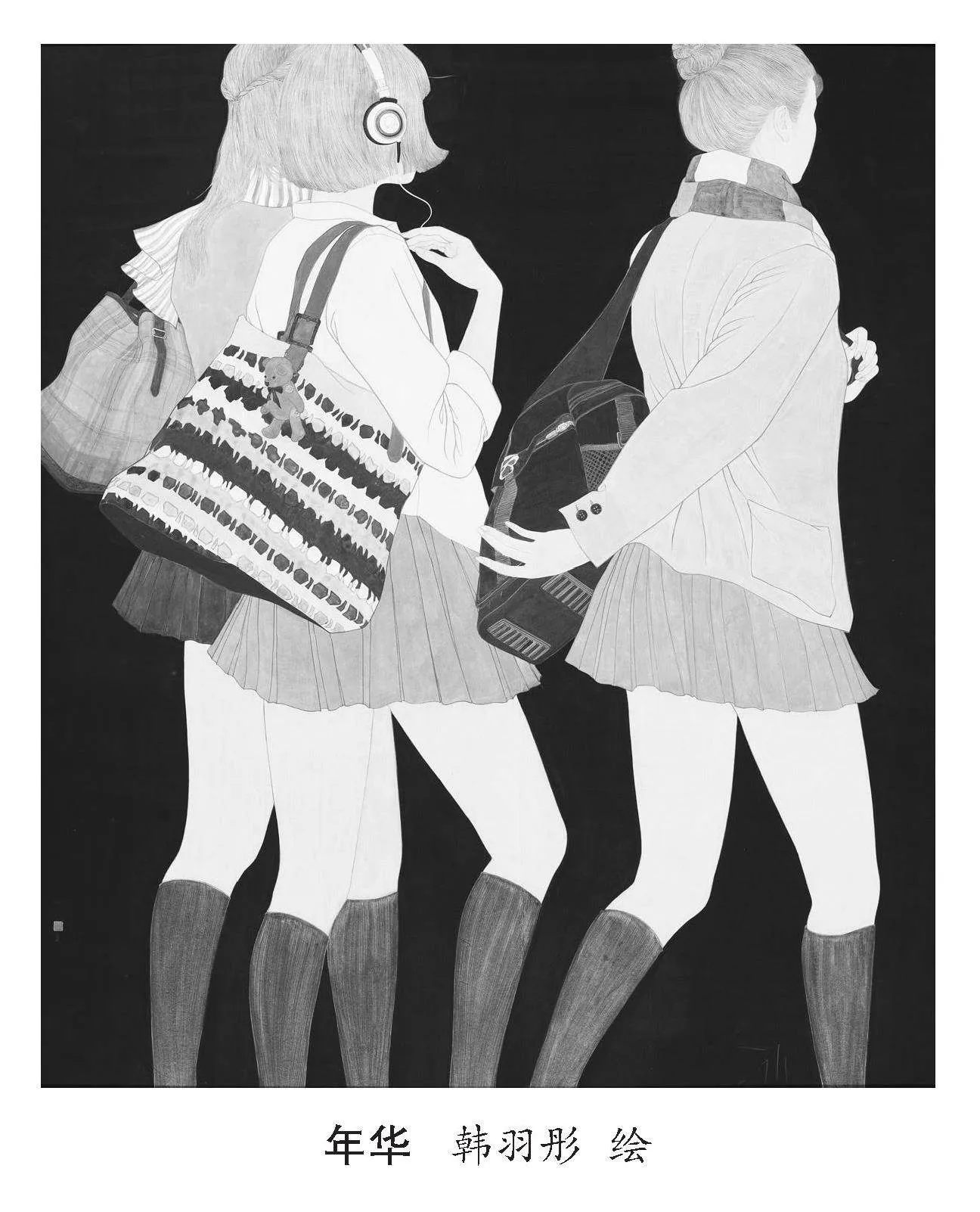
我是一名技術員,工作就是到各地去駐廠,調試設備,運維培訓。一個地方,待上一兩個月,再挪個窩兒。我的人生好似一片羽毛,不知道下一站會飄去哪里。
侉老太,就是我在這座城市當技術員的時候認識的。
這邊老太太買蔬菜,一般不去農貿市場,那里的菜大都量販,或者供應飯店,不讓人零零散散地挑揀。本地人買菜習慣扒去葉子再上秤,萵苣玉米蘿卜,逮到就扒,甚至買生菜白菜也會把外面的老幫子給扒掉,只稱菜心。回頭付完錢,再把剛才扒掉的葉子帶走。
所以,老太太們在市場里買肉、水產品、豆腐,絕不在那里買菜。她們會起個大早,拖著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帆布拉桿車,到市場對面的老街上選一些又便宜又新鮮的菜。
老街上,等待她們的,是一些從鄉下來的菜農,他們用三輪車馱來自家種的蔬菜瓜果,褲腳靴子上的泥巴仿佛在告訴你,這些菜是他們剛從菜地里拔出來的。也有人把自己釣上來的魚提來賣,一條二十來斤的草魚、胖頭魚周邊就能圍著一群老爺們兒看半天。我還見過有老太太來賣梔子花、木香花。菜農們往地上墊一層塑料編織袋,便是一個攤子。
區區一步長的攤位,得要早早地來搶占,有的菜農凌晨三點就來了,遇到雨雪天,就先把編織袋放地上占位置,用碎磚碎石壓好邊角,自己在不遠處的屋檐下躲雨,眼睛焦急地望著黑咕隆咚的天。
到老街上買菜,是要帶一些零錢的,他們大多沒有收款碼,有收款碼的,很多也是兒子兒媳的,他們希望城里人能給現錢。
過了早晨七點,老街上的人越發稀疏,這時候城管就來清理道路了,這條街白天車流量還是蠻大的。
我這次駐的廠子沒有食堂,得自己做飯。我常到老街買菜,但我老是睡過頭,這時,我就會到侉老太那里,買她的菜。
侉老太不是本地人,她咬字重,很多字都帶著鼻音/2d7atM8iMl8KKVG53t2ng==,說話倒也能聽懂。她賣菜,卻不是菜農,她不種菜,也不販菜,她只是挑別人攤子上的菜,再加點價賣出去。
每天一大早,侉老太就推著她破舊的小推車(推車上有一個座子,可以坐上去),到各個菜農攤子上轉悠,精挑細選幾樣她覺得好的菜品,擇好了,等菜農們走了,她就把菜堆放在小推車的座子上,在路口等人來買。買她菜的多是些上班族,她沒擺攤子,城管也不趕她。
因為是“優選”,侉老太賣的菜,自然會比別人要貴一些。雖說貴,那菜棵棵精神飽滿的,瞇著眼買走就行,其實并不吃虧,所以我從不和她問價,貴又能貴多少?一個老太太,雞皮鶴發的,恐怕還指望著這點薄本薄利買米買面過日子。
我和侉老太逐漸熟悉起來,零零散散的,我從她那,也學了些挑菜的秘方——
比如買西紅柿,要看屁股底下的葉子,有五個葉子,也有六個的,有時能見到七個葉子的,葉子越多味越正;帶沙土的黃土豆是面土豆,可以燉著吃,淺色的是脆的,適合炒著吃;洋蔥紅色的辣,白色的甜;挑桃子,腦袋瓜要圓,李子就要挑腦袋瓜尖的,最好帶樹膜;買毛豆要買圓粒兒的,不要長粒兒的;買胡蘿卜,要小腦瓜小尾巴,不然里頭會長檡子;黃瓜也要小尾巴,嫩綠的,不要墨綠的,能有干花最好,鮮花蘸藥多;韭菜要細紅根的,紅根不出水,味兒正;買棗要買灰棗,不要買駿棗;挑大蔥要青白對半,不然容易爛;鐵棍山藥要選帶粉紅鐵銹的;香菜要短稈兒的;萵苣要短粗的,一定不要帶棱,不然空心兒;甚至端午節買艾蒿,都有講究,她教我如何選艾蒿,不要買到柳蒿……
她說的這些竅門,即便你知道了,真挑起菜來,比她還是差遠了。人家在這條街上挑多少年菜了,火眼金睛,無論什么菜,眼一看,手一摸,就跟做質檢似的。
侉老太不高,也不胖,走路手都得撐著小推車,蹲下來又得半天才能起身,腿腳不好,卻總是調侃我瘦得像個竹竿。好些回,我到她那買菜,她都說我:“你光吃菜,不行,你得多吃肉!”她還教過我做一種菜,是她老家的名菜小炒肉,說吃幾頓保管上膘。
不久前,我結束了這里的駐廠任務,公司又把我派到新地方,新廠子有食堂,但很難吃,齁咸,油也大,無論什么菜我都得在菜湯里涮一下才敢放嘴里。我很想念在老街的生活,想念侉老太的蔬菜。
一天,我玩手機,偶然刷到一個視頻,視頻中央竟是侉老太在賣菜,里面配著音樂,沒有人說話,視頻上標著一行字:在這里,千萬不要可憐這些賣菜的大爺大媽。
視頻點擊量很高,下面有很多留言評論。打開一看,有的說他們缺斤少兩,有的說他們的菜農藥超標、濫竽充數,有的說他們阻礙交通、影響市容,有的呼吁相關部門清理整頓,甚至有人說他們家里有好幾套拆遷房,有存款、退休金,閑不住才出來賺倆錢的;也有人借此敘述自己曾經的“奇葩”遭遇。
好像是作文開了一個頭,下面的人各種續寫。說的那些話,和這個視頻,和侉老太,幾乎看不出有任何關系。
唯有一點能確定的是——
那些在評論區說話的人,應該沒怎么去過老街買菜,更不認識那個侉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