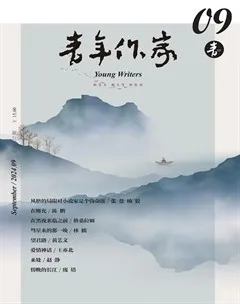我從未親眼見過彗星
我從未親眼見過彗星,最近一次機會是在三年前。公元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倫納德彗星(C/2021 A1)飛抵近地點。在那附近的幾個月,找一個晴朗的夜晚,抬頭就能看見倫納德彗星。如果你錯過了,等它下次回來,需要八萬年。那時候我就開始好奇,在我們無法相見的七萬多年又十個月里,這顆彗星在干啥?
從小喜歡這樣瞎操心。比如,收攤后包子鋪在干啥;放假了,學校小賣部怎么辦;公交車開到終點站,我還要站在那兒看司機掉頭、拐彎,直到汽車消失在車流里,還在想它接下來往哪去。越想越不得了,覺得身邊一切都是圍繞我在運轉,備感責任重大。晚上不敢睡覺,害怕閉上眼睛,整個世界便消失不見。我甚至為這種擔憂找到了“證據”:電腦游戲里有個“加載”的概念,為了節省算力,玩家接觸到的場景都是臨時渲染出來的,看不到的地方,則是一片虛無。誰又敢說我的世界不是由某臺巨型服務器加載出來的呢?
當然,這些荒唐的想法并沒有困擾我很久。我很快知道了“缸中之腦”“車庫里的噴火龍”,遇到網友的類似提問,甚至可以扔出一把“奧卡姆剃刀”揚長而去。刷知乎幫我戒掉了胡思亂想。直到某一天,我在等電梯的時候又聽到了鋼琴聲。
毫無疑問,每個小區的每棟樓里幾乎都有幾個彈鋼琴的孩子。你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是誰,但聽得多了,那些琴聲似乎也漸漸生出模樣來:“鱒魚”是個活潑的胖娃兒、“小星星”走路一蹦一跳、“致愛麗絲”肯定有一條頎長的脖頸……這時候你才發現,一墻之隔的鄰居,竟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謎題。我又開始瞎操心了。我為自己“加載”了一位練琴的鄰居,我讓琴聲在每個夜晚定時響起,我每每留意那些旋律的變化、曲目的更替,琴聲結束的地方,就是小說生長的起點。
只需要分析一顆彗星掠過地球的短暫軌跡,科學家就可以計算出它數百萬年后的命運,誤差以毫厘計。相比之下,我浪費了八九千字,還是沒能得出一個確鑿的故事結局。或許,這反倒是小說存在的意義。在人類只用幾行方程就可以描述整個宇宙的今天,那些我們等電梯時擦肩而過的背影,卻依然是未解之謎。
最后說說小說標題。這個標題源自一部科幻電影,片名普遍譯作《彗星來的那一夜》。研究彗星的時候我曾找來參考,看了兩遍,一頭霧水,又上網研究劇情解析,才發現電影和彗星根本沒什么關系。這時候就想起我那些喜歡釣魚的朋友們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來都來了”——當即拿片名做了小說標題。復制,粘貼,又盯著看了半天,說不出為什么,總感覺“夜”字冰冷而堅硬。最后改成“那一晚”,似乎這樣,整個故事也就柔軟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