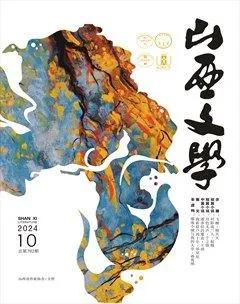紙扎吳
猷州的老街太老了,歲月的犁鏵在老街凹凸滑亮的麻石上不知犁過了多少代多少年,連從巷弄里溜出來的風都呼哧帶喘。
老街中段的拐彎處,有一個鋪面,門楣上懸一塊黑底金字橫匾:吳記紙扎店。門臉兒很小,里面光線不濟,從外面看進去黑黢黢的,門口斜靠著一只扎得極精致漂亮的大花圈,才證明了這是一爿紙扎店。
定睛細看,門檻里面坐了一個白發勝雪的瘦小老頭兒,鼻梁上罩著一副老花鏡,滿臉的皺褶渾似暮秋的老絲瓜瓤,藍咔嘰布褲褂干干癟癟地撐起一個老蝦米似的瘦軀。這老頭姓吳,名伯年,便是這店鋪的主人了,老街人都習慣地稱呼他“紙扎吳”。吳伯年聽了,微微一笑,算是應承,手上卻并不閑著,活計在他指縫里像是一個出神入化的舞蹈精靈。
吳家是猷州赫赫有名的紙扎世家,上至知州大人下至販夫走卒,家中逢了喪事無一不用吳記紙扎店的紙扎品。到了吳伯年這一輩,紙扎活就顯出“時乖運舛”的況味了。他子承父業,把祖業發揚光大得無出其右,都說他于紙扎有異稟,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料子。
可是,有人要砸他這個捧了世世代代的飯碗兒,說是“封建迷信”,給他戴上又尖又高的紙糊的白帽子,雙手綁了,讓小將牽著繩頭游街示眾,小將們一路威風八面地昂首前進,一路還震天價響地敲著銅鑼兒,老街上看熱鬧的人比看猴戲的人還多。那時的紙扎吳還是個毛頭小伙子,性子像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就是不承認有罪,被小將們掰折了手指頭以致冷汗直流,就是不呻一聲吟不服一句軟兒。
瘋勁兒過去了,老街重歸于平靜,市面上卻是一天比一天喧闐繁盛起來,什么樣的店鋪都冒出來了,仿佛黎明的林子里各種鳥兒雀兒比賽著唱歌。只有吳記紙扎店還是個啞雀兒!就有當年掰折他手指頭的人找上門來,又是遞煙點火,又是滿臉堆笑兒,笑了之后又哭哭哀哀一陣,央求他重操舊業,卻是這人家里歿了長輩,急等著“七七”焚化紙扎品祭奠亡靈呢!
紙扎吳其實早就憋不住,技癢難耐了,祖活兒若在他手里斷了那真是忤逆大不孝哩!央告的鄉黨越來越多,他算是掙回了面子,于是狠狠地跺了跺腳,叫道“罷罷罷”,這才順勢而為,把吳記紙扎店重又拾掇開張起來。他一出手的一堂紙扎祭品,讓老街人驚呆了眼睛、驚掉了下巴,這分明是一件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啊!精致得簡直讓主家不忍心付之一炬!有人忽然醒過神來,雙掌合擊,嚷道,敢情你一天也沒閑著,憋著勁在搗鼓紙扎活兒呀?難怪大門關得鐵緊,神秘兮兮的!紙扎吳也不回話,微微一笑,笑里藏了很多意味。
吳記紙扎店的生意越來越紅火了。
歲月就像老街的風,刮了一波又一波,再也不會回來。老街的麻石路愈加凹凸滑亮了。
有一天,吳記紙扎店來了一個盛年艷婦,不言不語地坐在旁邊,不知是盯著紙扎吳還是盯著他手里的紙扎活兒看,眼光直勾勾地簡直定了神兒。紙扎吳原本靈巧如翩翩蝴蝶的手漸漸抖顫起來,后來明顯不大聽使喚了。
第二天,那個艷婦又早早來了,還是靜悄悄坐在一邊,癡怔怔盯著紙扎吳或是他手里的活兒看。
他這只悶葫蘆終于沉不住氣了,甕聲甕氣道,馬翠花!你這是干啥呢?想訂紙扎品祭祀用?
馬翠花一下子黑了臉,懟道,積點口德行不?你咒我呢!想錢想瘋啦?!
紙扎吳鬧了個大紅臉,緊著賠不是,試探著問,那么,你是想學做紙扎活?
呸呸!這回是馬翠花把臉兒暈成了紅綢布,啐他一臉唾沫,我才不學這個呢!陰森森的讓人堵得慌!
那你成天點卯似的泡在這里,你不怕人嚼舌頭,我還怕人說閑話呢!紙扎吳整個傻眼了。
馬寡婦我看上你啦!算你走了狗屎運,不不!是交了桃花運!你年輕那會不就惦記著我嘛!不過,你不準再干這人不人鬼不鬼的活計,得找份正經營生!
紙扎吳剛剛怒放的心猛一下又被寒風吹折了,忿忿道,你若接受我,就得接受我這個紙扎匠的身份!就像我若接受你,就得接受你臉上的那塊大胎記!
他后悔已經來不及了,馬翠花又氣又羞,忽地騰起身掩面跑開,撒下一路似有若無的哭泣聲。他把腸子都悔青了,倒不是因為錯失了一段姻緣,更多的是擔心無意中傷了那女子。事已至此,悔也無益,紙扎吳大腿一拍道,罷罷罷!這世上,光棍難道不是人打的!
沒過多久,老街街口響起了噼里叭啦的鞭炮聲,“佟記紙扎店”隆重開張了!出出進進的老板娘竟是馬翠花。聽說她賭氣嫁給了一個剛從號子里出來的什么“豪哥”。還聽說,豪哥壓根不會扎紙活冥物,全部是從外地進的成品貨,價格就比吳記紙扎店便宜不少。
說也奇怪,吳記的生意硬是沒受多少影響,紙扎吳每天坐在昏暗的門檻里,手掌里跳躍著篾片或是葦稈兒,身邊堆著花花綠綠的各色彩紙,一把剪刀,一把鉗子,一只小電鉆,一捆細鐵絲兒,一盆糨糊,這就幾般簡陋甚至寒磣的家什兒,香車,駿馬,豪宅,別墅,手機,電腦,各種家電家具,奇跡般出現在老街人眼里,讓訂貨的人無話可說,爽爽利利掏錢,讓路過的看客嘖嘖稱奇。
這天夜里,吳記紙扎店的門被“咚咚”敲響,進來幾個穿制服的男子,說是紙扎店的存在,對于猷州即將推行的殯葬改革不利,責令關停,否則嚴懲不貸。紙扎吳眼前恍惚出現了當年小將的影子,他將信將疑,吭吭哧哧地想讓來人出示一下紅頭文件,來人不耐煩了,竟惱羞成怒,叫罵著推倒踢爛屋里的一堆紙扎器物,然后揚長而去。
紙扎吳流了一夜的眼淚,硬生生坐到雞叫。天一亮,他就出門去了縣政府,他要好好“理論理論”。
縣長很年輕,戴著近視眼鏡,一看就是個文化人兒。縣長親自給他沏了一杯茶,坐到他對面,讓他慢慢說。縣長一言不發,聽完他的話,打了一個電話給公安局長。縣長一直把他送到縣政府大樓門口,握著他的手說,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讓你受驚受損失了!三天之內給你結果!
第三天,紙扎吳就聽說佟記紙扎店的豪哥被公安局的人帶走了。他一點高興不起來,很少出門的他故意踅過佟記的門前,見女主人正在店里哭天抹淚兒。
沒過幾天,縣長竟獨自上門看望他來了,再次向他表示歉意。還說,紙扎吳的名頭在猷州比我這個縣長大呢!我已安排文旅局給您申報非遺傳承人,把這手絕活好好保護傳承下去。
太好了!紙扎吳歡天喜地、迫不及待地說,我一個老光棍,無兒無女,我把手藝傳給豪哥兩口子可以吧?讓他們也有一個養家糊口的絕活!荒年餓不死手藝人哩!
縣長愣了一下,隨即開心地連連點頭,可以!可以!您老當得“德藝雙馨”二字。
主汛期說來就來了。一個噩耗傳遍了猷州,縣長在組織抗洪搶險時不幸以身殉職。在縣長的葬禮上,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出現了!一輛農運車突然駛了過來,車廂里滿載各種紙扎冥物,紙扎吳爬出駕駛室,踉踉蹌蹌地蹣跚到縣長的墓穴前,雙膝跪地,駕駛員小心地搬過來一件件美輪美奐的紙扎冥器,紙扎吳一件件地焚化……喃喃道,都夸您是一個清官好官,現在您去了另一個世界,可以好好休息,享受享受了,別太苦了委屈了自己!
縣長妻子感激地付了他紙扎錢,紙扎吳并不推讓,如數收了。他說,縣長一生清廉,不能給他留半點污名!
后來,豪哥兩口子跟在紙扎吳后面學起了紙扎。等他倆出了師,吳記紙扎店就關門歇業了,紙扎吳說他太老了,干不動了,畢竟后繼有人,他死也能瞑目了。
紙扎吳走了,走得很突然,很安詳。“七七”那天,豪哥兩口子給他焚化了一堂紙扎物,那冥器的扎功,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回去后,豪哥就把“佟記紙扎店”的招牌換成了“吳記紙扎店”。
如果你有興趣去游玩猷州老街,一定可以看見這塊店招,這個紙扎店。
【作者簡介】 袁良才,安徽省作協會員。在《清明》《安徽文學》《作品》《芒種》《北方文學》《紅豆》等刊物發表作品若干。作品被《小說選刊》《小小說選刊》《海外文摘》等轉載。出版小說集5部。曾獲 《小說選刊》 雙年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