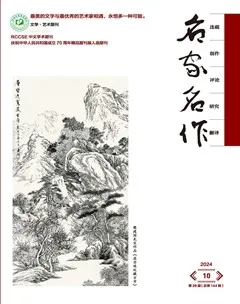論《駛下摩根山》中女性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建構
[摘 要] 阿瑟·米勒是美國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評論界對其作品的研究成果繁華壯觀,其中對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男性角色,女性角色的研究資料相對鮮少。雖然米勒大部分作品都以男性作為主角,但他同樣賦予筆下的女性角色同命運抗爭的生命力。在延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伊里加蕾的差異論女性主義理論,分析《駛下摩根山》中的女性從喪失主體性到重建主體性、從接納自我到守望相助,并最終實現女性主體間性的建構過程。
[關 鍵 詞] 阿瑟·米勒;女性主體性;主體間性;伊里加蕾
米勒在大部分劇作中都將男性作為主角,這導致評論界對米勒筆下的女性角色有了不謀而合的評論。這些評論可大致分為兩種觀點:一是認為這些女性角色相對于男性角色顯得過于平淡和扁平,通常由圣母/妓女相對出現;二是認為米勒作為男性作家,帶著男性凝視的視角,將女性角色邊緣化為被看的他者。而米勒并不這樣認為,他提到筆下的女性角色時這樣說道:“評論家把我的女性角色看得比她們本身要更被動些,事實上她們并非如此。”[1]如同《駛下摩根山》中被重婚行為傷害的女性,她們并未一直沉溺在痛苦中,反而借此直視自身的人性虛弱之處,并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意義。總體來說,米勒劇作中的女性角色,并沒有得到評論界與讀者足夠的重視。本文在研讀前人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伊里加蕾的女性主義理論,通過分析《駛下摩根山》中女性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建構過程,形成對米勒筆下女性角色新的思考與總結。
一、女性主體性的喪失
西方文明總體上是父權制的,這種概念外化于社會結構以及所有文化領域的組織構成,內化為權威的父權意識形態,即女性從屬于男性。在傳統的父權意識形態下,女性成為相對于男性的第二性,成為男性的客體,從而喪失了主體性。伊里加蕾將女性主體性喪失的根源歸結為兩點:一是“父權文化的創建使母親于創世紀初和遠古時代就已消失”[2]-;二是由于女性根據父權文化界定自己,因此相對于男性被定義為匱乏,從而導致女性由極具創造力的主體,變為父權秩序的維護者。父權文化切斷了女性譜系,排除了女性之間的社會性。這樣的父權意識還滲透在一些經典的文學作品中,這樣的文學作品往往以男性主人公為中心,主要以男性的行為特征和情感方式來體現,同時將女性設置為邊緣或從屬角色,是男性事業或欲望的服從與補充。女性讀者往往需要站在男性角度,從男性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甚至從這些角度來反對自己的女性經驗。而米勒恰恰相反,他切實地描述美國社會中普通女性的生活,賦予筆下的女性角色充分的人性,并對這個時代中削弱女性的自主性且“將她們貶低為簡單商品”[3]的方式進行批判。
米勒始終關注時代問題,《駛下摩根山》的時代背景正對應里根時代。在里根時代,對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的信仰再次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膨脹為無邊無際的夢想。在這個夢里,個人的繁榮、自負的妄想和過度的樂觀主義模糊了人們對現實的認知。從各種意義上講,該劇不僅是對里根時期政治文化的診斷和預言,更是對這種文化日后發展的診斷和預言。萊曼是里根時代的獲利者,他既沉浸在里根時代的欲望中,又被其裹挾。于是因為萊曼的欲壑難填,作為萊曼客體的兩位妻子成為犧牲品,成為萊曼游離在規則之外的注腳。
兩位妻子在一開始皆喪失主體性。希奧是萊曼的原配妻子,她是牧師的女兒,她維護且遵守社會規則,兢兢業業地做一名好妻子、好母親。然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希奧無法贏得一席之地,她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萊曼,從而不自主地淪落為客體,成為丈夫的附屬。利婭是萊曼的重婚妻子,她與希奧完全相反,她青春且不遵守規則,她與萊曼一樣是保險從業者,并且在社會叢林中戰勝許多男性獲得自己的地位和財富。從經濟獨立的角度來看,利婭非常有主體性;但從心理機制上來看,利婭無法把握自己的主體性。她與萊曼的結合,源于她的孤獨,于是她下意識地放棄追究萊曼是否真的離婚。在墮胎事件上,利婭陷入了萊曼為她編織的美夢,放棄了墮胎,放棄了對自己身體和人生的掌控權,也失去了自己的主體地位。米勒將萊曼描繪成一位對婚姻制度漫不經心的旁觀者,而希奧與利婭因經濟與心理的主體性喪失,導致兩人沒有得到作為主體應有的尊重,反而被客體化為滿足萊曼需求與野心的組成部分,最終成為重婚事件的受害者。
二、自我身份的認同
伊里加蕾認為,女性要獲取主體性,首先應該回到女性與女性的關系中。在這段關系中互相溝通,重獲女性自己的語言,因為“侵害她與自己以及其他女性的關系,就是重述男性的再現體系”[4]。而女性獲取主體性的第一步,始于自我身份的認同。在傳統的父權社會中,女性的狀態永遠是被動的、沉默的。男性不需要女性的回答,女性被潛移默化地固定到聽從的位置。女性被“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就是排除在語言之外,排除在律法之外,排除在同文化和文化秩序之間任何可能的關系之外”[5]。女性的身份隨著成為男性的客體而模糊了。米勒劇作中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通過自我認同來追求自我的主體性,《駛下摩根山》中的女性尤為如此。
希奧一出場被萊曼稱贊為“圣女”,她穿著合腳的鞋子,鎮定地安撫女兒,沉穩地守候在萊曼的病房外,甚至還有余力給予陌生女人(利婭)積極的情緒傳遞。第一幕第一場戲中的希奧被塑造成完美女性的形象,而重婚這個事件將希奧完美的女性形象沖擊得滿是裂紋,真實的希奧隨著她痛苦地剝開表象展現出來。希奧認同自我身份的方式有兩種:否認與回歸。巴塞爾·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認為當人受到精神創傷時,大腦會趨利避害地進行遺忘,“遺忘的一種方式就是否認當時發生的傷害”[6]。希奧的那段航海旅行的記憶曾十分美好,她一直記得,面對鯊魚的威脅,萊曼拯救了自己。但這段記憶恰恰就是希奧回避的精神創傷,當希奧直面重婚事件的沖擊時,她想起了當初真實的場景:萊曼并沒有努力警示她,萊曼曾經想過殺死她。隨著這個真實回憶的痛苦再現,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希奧否定的瞬間霎時浮出水面,比如萊曼嫌她無趣,比如兩人早已無話可說。此時希奧對婚姻的失望與對萊曼的憤怒到達頂點,她無意識地采取了“回歸”這種防御機制。巴塞爾認為當人感到不知所措時,人會回到一種不成熟的應對形式。希奧面對來自萊曼的傷害,她脫下裙子露出大腿,推翻自己的堅守和信仰,徹底撕破完美女人的外衣,表現出跟一開場完全對立的樣子。在當下的羞辱與痛苦的往事回憶的相互交疊下,希奧正視了自己。在這段婚姻中她與萊曼一樣煎熬,她看不上萊曼的粗鄙下流,真正讓她無法離開的不是情感本身,而是萊曼給予的優渥生活。當認清事實后,希奧打破“金枷鎖”,主動離開了萊曼,以優雅的姿態重獲自己的主體性。
利婭一上場穿著浣熊皮大衣和高跟鞋,與囿于家庭的希奧形成鮮明對比。丹尼爾·羅什(Daniel Roche)認為:“衣服是身體的身體,從它可以推斷出一個人的性格。”[7]在利婭的人物塑造上,衣服 “揭示了人的內在和外在的和諧”[7],向讀者展示出一位在物質上可以實現自己主體性的女性。利婭比萊曼小24歲,她事業有成、老于世故,在與萊曼的這段關系中,她更有可能成為掌權者。然而諷刺的是,在這段關系中她一步步地迷失了自己。她先是沒有墮胎生下兒子,又因孤獨而故意忽略萊曼可能沒有離婚的事實,她將自己從前的工作能力用在了接受謊言、處理謊言上。在直面重婚問題之前,利婭已然失去自我,變成萊曼的客體。與希奧不同,面對重婚的沖擊,利婭沒有暈倒,她迅速起訴,讓萊曼簽署財產與兒子的歸屬文件,游刃有余地捍衛自己的利益,找回自我。利婭通過自己職業能力的展示,以及對自己有能力過上美好生活的信心,將她積極的生命狀態和強烈的自尊心淋漓展現,至此她重新掌握自己的主體性。
三、女性話語體系的建立
傳統的父權社會排除女性之間的社會性,女性之間無法進行真正的溝通,這導致女性之間的關系呈現癱瘓狀態。所以為了“女性之間進行親密無間的對話,彼此有愛”[8],勢必要建立女性話語體系。女性的主體性也是通過她們的話語構成,所以要讓建構獨立的女性身份與話語體系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支撐女性掌握真正的自我,在社會中由他者變成主體,作為主體與另一個女性主體溝通,結成互助的紐帶關系。特里·歐登認為米勒“有能力創造堅強的女性人物”[9],在《駛下摩根山》中,米勒通過四位女性人物展示了女性之間的互助關系,以及女性作為獨立個體在社會中所呈現的力量。
首先是希奧與利婭。這本是一對互相競爭的“妻子”關系,最后峰回路轉成為一對互相鼓勵的女性關系。在這對關系中,希奧首先伸出援手,一開場在等待病房消息時,她安撫了焦躁的利婭。緊接著重婚事件暴露,希奧暈倒,利婭又急切地救助希奧。盡管兩位女性實際上是競爭對手,但她們談話中多次出現“我們”,這個詞表明了她們之間因被傷害帶來的聯系。當她們彼此冷靜后,意識到自己都是重婚的受害者,不應該為萊曼的錯誤買單時,她們繼而彼此鼓勵。關于如何安慰孩子的共同話題,迅速拉近了兩人的距離,她們開始認同對方,并為對方所受到的傷害而憤怒,利婭認為萊曼配不上希奧,甚至為希奧的離開提供幫助,兩人從最初的競爭對手變成了最后的同盟。利婭與希奧之間有了社會性的聯結,自此兩位“妻子”結成了互惠的主體間性女性關系。
希奧與貝茜這對母女更是如此。希奧在一開場理智地安慰女兒,帶領貝茜用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為貝茜提供了一個正面的女性角色模型,貝茜被成功安撫,凸顯了母女間密切且互惠的聯結。面對被傷害的母親,貝茜也第一時間挺身而出。在整部劇中,貝茜都堅定不移地鼓勵、支持、維護希奧。從童年的非洲旅行開始,面對萊曼對希奧的惡意調侃,貝茜堅決地讓萊曼道歉;到當下重婚事件暴露,希奧情緒崩潰,貝茜嚴厲指責萊曼;再到劇終,對于萊曼的挽留,貝茜果斷且強硬地勸希奧離開,無不展示了母女間流動的愛。伊里加蕾在《你、我、我們》一書中曾提到,女兒應該幫助母親,讓母親重獲主體,她認為“我們可以教育我們的母親,也可以相互教育”[10]。在重婚事件暴露后,貝茜表現出比希奧更強烈的憤怒,這種憤怒既是維護母親,也是為自己發聲。貝茜意識到了父親作為男性與她們作為女性之間的不同,女性的作用是“為社會秩序和欲望秩序奠定基礎”[8],父親無視的道德規則與社會契約,卻是以母親為代表的女性的行為規范準則。這個認知讓她前所未有地意識到女性聯結的重要性,也夯實了母女二人最終離開萊曼的決定,自此主體間性母女關系確立。
《駛下摩根山》的舞臺場景設置為醫院,醫院環境與米勒慣用的家庭環境相對,醫院作為公共環境排除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讓讀者以更客觀的視角看待人物。同時,醫院環境也帶來一絲治愈里根時代社會問題的希望。女護士洛根在劇中戲份不多,但她與周圍人物之間是一種主體間性的關系。洛根用她的寬容與愛將劇中所有人緊密聯結在一起。洛根的家庭雖不富裕,但家庭氛圍和諧美好,且對生活的要求低于欲望,與里根時代的氛圍格格不入。她善于傾聽,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時刻給予別人幫助。洛根第一次出現,是在照顧萊曼;并在劇終所有人都離開萊曼時,還陪著萊曼,并給了萊曼一個安慰的吻。萊曼有過名望、金錢、愛情等一切美好的戰利品,但在最后,萊曼失去了這一切,而洛根的吻,給了絕望的萊曼活下去的力量。洛根對萊曼富有同情心的回應,給了萊曼重回正途的指引;她心無旁騖且樂于平淡的生活態度,成為里根時代社會問題的解藥。而洛根的獨立與仁愛,正是米勒對女性主體性以及女性與他人的主體間性關系的肯定。
四、結束語
米勒筆下的女性角色在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中都沒放棄過對主體性的追尋與建構,他的作品超越了時代對性別認知的局限性。尤其是《駛下摩根山》,兩位喪失主體性的女性,通過對男性話語的反思與痛苦的自我審視,從而實現自我認同,最后建立起互助的女性主體間性關系,尤其是良好的主體間性母女關系。女性應該置身于女性話語體系之中,保留自己的身份,書寫自己的歷史,這樣就能“雖然相隔甚遠卻可以彼此擁抱”[11]。女性主體性與女性之間的主體間性的實現,也是促進性別和諧共生,實現多元文化發展的推力。
參考文獻:
[1]羅丹,馬修C.與阿瑟·米勒的對話[M]. 杰克遜: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1987:370.
[2]邱小輕.主體間性與母女關系的社會倫理建構[J].求索,2010(8):116-118.
[3]阿妮塔·薩克塞納. 性別動力與社會壓力:探索阿瑟·米勒的《騎馬下摩根山》中的女性形象[J].綜合研究,2024(5):12.
[4]露絲·伊里加蕾. 性別差異的倫理學[M]. 卡羅琳·伯克,吉莉安 · C.吉爾,譯.倫敦: 阿斯隆出版社,1993:85.
[5]皮埃爾布·爾迪厄.男性統治[M].劉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
[6]巴塞爾·范德考克.不可避免的休克,神經遞質,和創傷成癮: 走向創傷后應激心理學[ J ].生物精神病學,1985:314-315.
[7]丹尼爾·羅什. 服飾的文化: 古代政體中的服飾與時尚[M]. 讓·比雷爾,譯.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4:6,7.
[8]露絲·伊里加蕾.與母親的身體接觸[M]//大衛·梅西,譯.伊里加蕾讀本.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布萊克威爾出版社,1991:44,35.
[9]奧頓,特里. 阿瑟·米勒戲劇中的純真誘惑[M]. 哥倫比亞: 密蘇里大學出版社,2002:16.
[10]露絲·伊里加蕾.你、我、我們:走向差異文化[M]. 艾莉森·馬丁,譯.紐約: 勞特利奇出版社,1993:50.
[11]露絲·伊里加蕾.這不是一個性別[M]. 凱瑟琳·波特 ,卡羅琳·伯克伊薩卡,譯. 紐約: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5:215.
作者單位:山東藝術學院
作者簡介:王思雅(1992—),女,漢族,黑龍江撫遠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戲劇影視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