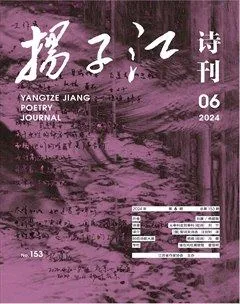鄉野的輪回(組章)
柏水,本名馬健,1995年生于山東臨沂,現居山東濟南。
小河門檻
跨過連綿的山崮,小鎮上的風有了紅瓦的模樣,在夜幕來臨前,留下唯一的記錄。田間的鐮鋤,摩擦出透明的火花,一點點挖掘著干裂的土地,愈來愈深。
鎮子外的小河,雕琢出一座小鎮的歲月,在亂石與泥土中滋潤著往來之物。幾只鳥擺脫了圓形的引力,落于河灘,在泥沙中構造起避人的“門檻”。曾有先生來此隱居,在屋舍之間留下無聲之詩,每一句詩,都是自然的饋贈。
一部分在春秋沉淀而成的絮語,從門的夾縫中脫離,它們躍出虛幻的門檻,重回鄉野,試探著每一處新生的綠意。等到飛鳥歸巢,遠方的路人重返小鎮,那夜幕下的最后一幅畫,成為此刻小鎮上唯一的故事。
縱使四季輪換,那條環繞小鎮的長河,卻終年沒有干涸,它為鎮子帶來生活之外的驚喜,在老舊的渡船旁,敲打出詩語,告訴人們它的歷史。小鎮的命運,從未在門檻之外,那些順流而下的碎石,擊打著來自歲月的鼓點。
酒歌
父親的麥田里住進無數風聲,在赤黃的泥土中與麥苗交換上個月的聽聞。隔岸的河洲上有路人歇腳,他們從偏重的木船上劃開黏稠的日子,在父親還未理解前,抹去了河川的聲音。
村外的石磨旁,有酒香占據了幾間瓦房,云朵外的白鳥,輕點羽翅,將沁人的香味帶離矮房,送到父親的肩頭。他很少獨自偷飲,而是深入河灘,穿織起江流與村落的故事,在喟嘆中與友鄰小酌幾口,裹緊對話的歌調。拋開那些跟隨水聲遠去的古歌不談,清風、明月、麥浪,早已填滿了鄉民的思緒,在無人的時刻,悄悄低吟。
斑駁的水野間,太白的酒歌蔓延到北緯23度的庭院,讓院中的水井拂過石檻,向父親他們言說著歷史清單。現代水票無法阻隔飄蕩百年的鼓點,只能依著酒的香氣,蓋住酒歌里的遺風。
荒原與麥田格格不入,那里不曾有酒香的影子,穹頂之上的詩句,依舊繞不開酒歌的呼喚。父親是山野的看門人,他早已數不清河洲與田間的聲響,不過,酒歌穿透時間的巨墻,使他打開了歲月的巨門。鐘點之外,我們拼接起眼前的村落,酒味再起。
牧羊的老人
山坡上的石楠花,飛越草原,帶來無數閃耀的晨露,花的世界遠離河灘,在羊腸小路旁望著時令。細雨已經將日子打落在花叢中,老人驅趕著羊群,涌入草野的腹地。他用一生的時間,摸索出草原的模樣,卻沒有摸清自己的樣子。
高處的石楠花,是他多年前撒下的枯種,時間將花苞滋養成熟,讓花色在天空下拼湊成詩意的音符。老人日日聞雞而起,放牧著羊群與晨風,在腳步的回響中丈量著與故鄉的距離。他用一根細鞭抽打著生活的暗礁,幫助羊群躲避風雪的侵襲,那墨綠的門扉,總是離他不遠不近,卻無法觸及。
秋末,曠野不再溫順,而是以枯敗的景象面對老人和羊群,自然的法則終究無人能堪破,老人帶著余生的愿景,在生活的殘章中寫下溫柔的一筆。他曾走過雨巷、老街、河港,將過往之事一一拋掉,在草原上重拾生命的影子。遠方的星海,是他懸于胸口的秘密,無人時,他總要將秘事傾訴給羊羔,仿佛完成另一種托付的儀式。
黃昏里的石頭
從城市走入鄉野,踏進一片渾厚之地,碎裂的星辰,無人關注,在黃昏后留下了隱約的影子。他是穿越山河的旅者,放下旅行的包袱,在這座安逸的小村里駐足。
黃昏是他最喜歡的風景,如一扇真實之門,收納著世間獨有的美。黃昏前,他擇一處開闊的河灘,任由眼前的牛羊在黃昏里奔騰、迷狂。風繞著他手中的詞語不停飛舞,將陌生的詞語吹成日落的模樣,在小鎮的河灘上,他遇見了不一樣的黃昏。孤霞迎著時間的舊痕,映照出不一樣的故事,草露成霜、魚游河川,自是沒有皴染的風景。一陣風,勾起石楠花的香味,在溫柔的夕陽下,送來“月神”的簡訊。
短暫停留后,他又要踏上遠方的舊路,由鄉野進入城市,追尋另外的光景。詞語的黃昏,在午夜前浸入大地,那些沉眠的故事,循著旅人的足跡,重新踏上了歸鄉的路途。
深秋經驗學
很少踏入秋的旋律,九月,自有過渡的意旨,將城市的高墻推向一個成熟的季節。及至深秋,眼前的風景不再熾熱,而是以沉穩的色調裝點著周圍的世界。被詩情畫意包裹的秋日,發散著不竭的經驗,人們穿過落葉滿地的林蔭道,體悟著吹在身上的柔風,走進另一個生命的良宵。云深無歸處,深秋的安穩告解著逝去的故人,讓南歸的群雁帶去無法言說的思念。
在城市與山鄉的交接處,秋日完成了一幅色澤鮮明的百景圖,演繹著獨屬于這個節令的榮枯之貌。深秋的風,從未越過幽深的山谷,而是沿著城市的高墻,闡釋著秋日的影子。一些無關乎生活的景致,自會沒入萬物的隱喻。記錄,不過是短暫的永恒,沒有觸及秋日的靈魂。那些在旅途上奔波的人們,喜歡深秋帶來的故事,卻也討厭深秋的凋零。
當思想落入旅途的經驗,被忽視的部分,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轉折。比如,沿途中永不消失的落葉,不斷向下生長的草木,都像一場場沒有預設的電影,遁入深秋,演繹出在世間豐盈的經驗。
蘆葦的思想之歌
水中的蘆葦,躍出云的倒影,宣告著一種新的聲音。雨水介入河灘,打濕萬物,帶去令人顫抖的涼意。關于蘆葦的詩詞,總有哲學的影子潛伏其中,記錄著時令的挽歌。在河灘上靜自生長的蘆葦,鐫刻著鄉野的標識,復現每一處草木的故事。水域外,無數的目光反復打量著這片蘆葦叢,想象的門檻,在此生發。暗香浮動的河岸,總有折返的鳥稍作停留,仿佛要拋下所有的憾事。
荒原的季節,在草木中愈發洗練,蘆葦叢里的思想之歌,在無人的夜晚悄悄生成。生活的窄門,嵌入蘆葦叢,在夜晚敞開,留下諸多隱秘的碎語。當晨曦的光輝又一次照亮河面,一叢叢蘆葦低下了頭,等待另一個挺身的節點。
多年前,先生來到河灘寫生,他迎著晚霞,看到了水中蘆葦的倒影,仿佛一座看不見的小城在眼前浮現。他明白,草木的歷史,難以追溯,凝結出想象的風,在詩人的筆下成為了永恒之物。蘆葦中的思想之歌,無人聆聽,卻在天地間演繹著遼闊的圖景。離開水野時,人們總會看見浮動的蘆葦,卻聽不到關于思想的聲音。
再談歸途
離開鄉野多年,在遠路上總能觸到故鄉的味道,迷人的城市里,余散著荒原的記憶,夾雜著屬于故鄉的風景。一部分來自山野的信物,在半路上隱匿,流淌出憂傷的挽歌。漂泊數年,我們似乎懂得了無風的意義,那些早已復活的歲月,一次次上演著荒原的故事。鄉野的小路,成為不再獨特的符號,裝點著無人觀賞的石楠花、寶鐸草。
異鄉的笛聲,在流水淙淙的夜晚一次次響起,街巷里的石畫、長街上的草垛,在悠揚的旋律中蕩開。雨水的介入,讓歸途有了朦朧之感,鄉土的味道也愈發濃郁。我們離開城市的街衢,找尋屬于鄉野的至真感,卻總在原地來回打轉。
遠處的山林,不再藏有挽歌,而是復現每一處和鄉野有關的記號。古老的山群,守護著少有人踏足的鄉野,也隔斷了兩個文明的交織與碰撞。鄉野的歸途,在輪回中充盈著生活的記憶,我們不再孤獨地返鄉,而是穿過歲月的窄門,和鄉野有了一場新的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