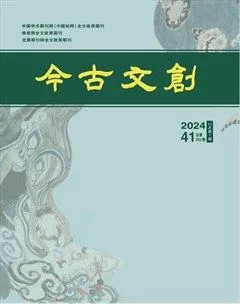蕭紅文學的現象學研究
【摘要】從現象學視角看待蕭紅文學的本質,其文本中的女性意識獨特性、向死而生的生存哲學,以及獨特的小說形式變易特征,均可解釋為是一種意向性活動的結果。作家的生活真實與創作真實之間在文本世界里達成彼此滲入的狀態。同時作品為現象逗留、真理顯現自身提供基礎,通過主觀重塑時間和空間比例,作品成為大地澄明的場域。
【關鍵詞】現象學方法;意向性;蕭紅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1-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2
“胡塞爾起初的目的在于建立一門哲學的方法。‘哲學方法’——這是指通向認識真理的一條道路,一個過程。” ①現象學追問的真理是關于原本性的,進一步說就是萬千世界的經驗都依據這個原本性被給予一定的方式。而“所有在‘直覺’中本原地(可以說是在其真實的現實中)展現給我們的東西都可作為自身被給予之物接受下來” ②,每一個經驗對象與其被給予方式的原本性之間的獨特性都有可以被操作的具體方式。胡塞爾提出了“意識的意向性”功能,即所有的意識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意識具有權能性。人通過映射將對象作為被給予方式加以透視,從而獲取對象所指。
海德格爾認為文學藝術的本質在于通過置造事件為大地與世界的爭執提供場域。所謂事件即胡塞爾說到的對象多樣性現實的一種,也就是在“直覺”中本原地(可以說是在其真實的現實中)展現給我們的東西。具體而言就是文學作品的語言呈現。作家在文學作品中的語言呈現或凸顯為人物、細節,或是場景、情節。而大地即真理,就是一切存在的本源性,世界就是大地即真理的原本性被給予的方式、在事件中獲得表達的具體物。
蕭紅文學世界的獨特性是通過特定事件確立的:包括以蘸滿顏料點染和潑墨的后花園中的自然生靈,冰封的呼蘭河被北風席卷的冰面和彌散在空氣中的雪沫,也包括每一段人物與食物糾結的細節,直至被拉長時間、推到眼前的生死掙扎的描繪。蕭紅文學的語言呈現明顯攜帶著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語調:沉重、低回、堅韌。在時而細膩婉轉,時而鋒芒銳利的話語中,勾勒、渲染出20世紀初中國大地上的革命風暴和裹挾在風暴里的向死而生的個體或群像。
與這樣鮮明的歷史語調并存的,還有一種蕭紅個體生命經驗的情緒情感,這種情緒情感來自蕭紅在世界歷史時間上所經驗到的、卻直觸普遍時間中世界生命體驗的本源意味,因而蕭紅文學既是歷史性的,同時也是現象學式的。
一、蕭紅文學作品的現象學表現層
生和死本是生命的兩面,生之意義的獲得在于對時間的盡力占有,死亡則是占據所有與死者相關、存活下來的人的思想,由此世間億萬生命的意義連貫起來,成為一個整體。這些對生存和死亡彼此互為鏡像的表達,就是蕭紅作品的獨特事件,此類事件共同置造出蕭紅文學的世界,在這個文學世界中,生命的大地意義得以澄明。
(一)生存和死亡互為鏡像的敘事
蕭紅文學創作的時間背景是社會歷史進程中布滿生死挑戰的時代。民族危亡和抗爭爆發出強大的生命意志。這促使蕭紅的文學創作將重心自覺放在社會歷史的本質層面,將生死主題放置在一個浮雕作品凸顯的部分。帶有鮮明日常書寫色彩的蕭紅文學,清晰地寫出了在人與人之間無暇顧及活著的彼此時,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意義。
在蕭紅筆下,活著往往在慢節奏里顯露出死亡的逼迫(小團圓媳婦的活),在鮮活的開場里預演著落寞的散場(王阿嫂的命運)。然而同時也有在死亡面前用拼命嘶吼表達出的生命倔強,在靜靜消亡處(翠姨的死)吶喊出生命的悲壯意義。蕭紅筆下特定歷史時代東北大地上普通人的生存總被死亡窺視著,而同時死亡也被頑強生命的執著挑戰著。蕭紅筆下的生存和死亡敘事具有“存在者之存在成了與對象性相同一的東西”的現象學內涵。
生命的表層是千變萬化的個別,這些個別是蕭紅式的生存之原初性的被給予方式:它們是被饑餓威脅的口腹之欲刺破道德堅守的堡壘,是被本能驅使的繁衍行為擊碎的愛情幻象,是被無知和貪婪玩弄的高尚意義,是被死亡隨意性考驗的生之脆弱和無辜;是向世間冷漠抗爭的倔強和頑強,向日常無聊投擲的盲目逃脫……一場場生死搏殺酣暢淋漓地上演,它們都是獲得生命對象被給予方式的過程。蕭紅對生與死鏡像關系的塑造,使得作品充滿無限的生命張力。
(二)消除性別的女性立場
蕭紅文學創作中的現象學觀照除了盡力為生命以各種形式賦能和賦形,盡顯生命的豐富與深刻外,還有某種既明顯又隱秘的女性視角。之所以說蕭紅文學的女性視角體現得明顯,在于蕭紅的人物敘事聚焦于各種女性的生存現實:月英、金枝、王婆、小團圓媳婦、翠姨、芹、王大姐等形象總體上具有特定歷史時期東北農村婦女被迫害者的統一特征,但細節處每一個角色都努力破除女性悲劇命運形成的當下現實。蕭紅作品準確揭示了女性被迫害的命運之源深及傳統文化的痼疾:父權、夫權、族權的威壓。
值得深思之處在于蕭紅塑造女性形象時淹沒了她身為女性的主觀性。消弭作家個人的性別主觀,便達成一種作家與世界靈魂觸碰的意向性寫作。在意向性寫作中作家與創作對象同時被釋放、獲得自由:作家不被意圖支配,文學形象亦不受作家支配。此種意向性創作產生的文學形象既可能是一個獨特的人物,也可能是一種隱喻結構 ③。現象學意義上的女性角色絕不滿足于引發讀者的哀嘆和悲憫,破除女性作為弱勢存在的社會學意義,她們不僅作為被父權、夫權、族權三座大山壓垮的被動符號,她們還與男性以及自然草木蟲鳥一樣,作為袒露生命未知與蠻荒、人性自覺與麻木的主動符號。對蕭紅作品女性形象的闡釋除了從歷史社會學角度對女性形象意義賦值外,更為直觀與深切的是直逼小團圓媳婦被害過程的驚懼,在馮歪嘴媳婦死去中漸漸察覺的解構意味,以及翠姨死亡里低吟的冷漠、月英死亡前嘶吼出的對救贖的渴望。
(三)小說形式的變易
蕭紅小說“以舒緩的抒情筆致寫自我主觀感受,著重寫意境、寫氛圍、寫印象、寫感受” ④。小說敘事中濃重的散文化、詩化特征是蕭紅將她現實生存體驗升華為文本敘事的極限方式,小說敘事的虛構與散文敘事的真實,以及詩歌語言的蘊藉在同一個文本里完成本源性真實的統一。如同海德格爾眼中凡·高的畫作《鞋》,海德格爾在畫作《鞋》中看到畫中勞動婦女世界及其腳下的大地,這與蕭紅小說中人物用面包蘸鹽充饑折射的生死無期,二者都是現象學層面的藝術真實。
小說《呼蘭河傳》中寫道:
“等我生來了,第一給了祖父的無限的歡喜,等我長大了,祖父非常的愛我。使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夠了,還怕什么呢?雖然父親的冷淡,母親的惡言惡色,和祖母用針刺我手指的這些事,都覺得算不了什么。何況又有后花園!”
而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也寫道:
“父親打我的時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向著窗子,祖父時時把多紋的兩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頭上”“可是從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溫暖和愛。”
《后花園》中寫道:
“六月里,后花園更熱鬧起來了……那簡直是干凈得連手都沒有上過。”
作為小說人物的祖父是有力量的,是“我”的依靠。散文中祖父是無力的,僅是蕭紅相依為命的伴兒。小說中的后花園是人物的活動地,散文中的后花園是蕭紅家園一角,蕭紅筆下的后花園是如詩般的精神棲息之地。冰封的呼蘭河是故事里一座城的坐標,呼蘭河在散文中是蕭紅離家后回望遼闊的鄉土,呼蘭河亦是蕭紅在香港彌留之際詩意向往的靈魂歸處。
蕭紅的小說完成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眾生圖存的語言、心理、行為的虛構想象,那些熟悉的場景也是記刻蕭紅生活色彩、明暗、線條、輪廓格調別致的版畫,這幅版畫是蕭紅的文學文本“置造”的那個統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大地”的力量得以顯現。
二、蕭紅文學作品的現象學意義層
“現象就是作為自顯現的東西顯現自身者。這首先意味著:它作為它自身在此出現,并不是以某種方式在場或處于間接的觀察中,而且不是以某種方式重構。‘現象’是某物的對象存在的方式,而且是一種突現的方式:一個來自其自身的對象的當下存在(Pr?sentsein)。所以,這首先根本沒有規定有關事情的內涵(Sachhaltigheit),這里也沒有任何規定事情的領域的指示,‘現象’的意思是對象-存在(Gegenstand-sein)的突現方式。” ⑤現象學意義上的現實生活的面相不是無差別的平均在時空中的一切行動原封不動地刻錄,文學作品通過語詞提煉出現實生活中行動的典型突現,而不對其加諸任何規定性內涵的流露,只是為現實生活本身的顯現與無差別的現實平常區別開來,由此使現實生活的本相顯現。這些在蕭紅文學作品中可概況為三個方面。
(一)與世界建立的意向性關聯
蕭紅堅持創作要面向全人類的愚昧,這便需要蕭紅具備一種能力,使她的創作能托舉這個形而上的主題。蕭紅通過現實生存考驗獲得了這種能力,即與世界建立的意象性關聯。蕭紅意向性思考和表達的客觀世界不是純粹自存的客體,而是蕭紅的“完全的意象客體” ⑥,在意向性生存實踐中蕭紅自我與世界融合為一個整體,“感知與被感知之物合乎本質地構成一個直接的統一,一個唯一具體的思維的統一” ⑦,這便是其創作最本源的動機和文本意義形成的基礎。蕭紅從何種角度可以認為自己的創作是發現了世界和人類,而又在何種層面上認為自己的創作寫出的恰恰可以表現這個世界和人類?這中間起到轉化作用的是蕭紅的意向性創作活動。
“三月的原野已經綠了,像地衣那樣綠,透出在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須轉折了好幾個彎兒才能鉆出地面的,草兒頭上還頂著那脹破了種粒的殼,發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地鉆出了土皮。”“春來了。人人像久久等待著一個大暴動,今天夜里就要舉行,人人帶著犯罪的心情,想參加到解放的嘗試……春吹到每個人的心坎,帶著呼喚,帶著蠱惑……”
這段描寫中世界本來的存在仍在,帶著蕭紅視角的萬物色彩和敘述力度的世界也在。自然世界的質料就是風、草、樹的無聲生命之力,自然世界的質性就是殼破芽長的暴動,人之于自然亦深藏著同樣的血肉之質料,而那如春的暴動就是人之質性的顯現。
與自己所在的世界建立一種意向性互動模式,促使蕭紅創作把生活的現時感留置在了藝術虛構中,蕭紅的生存體驗在文學語言里被反復琢磨并映射其中,作家自我與角色經驗向時空投射的情感和意志保持著原本的一致。進而形成文學創作成為作家與生存現實世界意向延展與升華。家庭意象、親人形象既是作家現實生活的有機組成,更是她筆下被意向性還原了的世界代表。作品中的后花園是作家精神世界的鏡像反映,作家在現實生存與文學世界之間的調和過程充斥徘徊、挑戰甚至妥協。作品語言顯現作家用思想抵達痛苦當下和幸福目標邊界的方式,使文學創作獲得真正面向全人類愚昧的本質力量。
(二)讓大地澄明的文學世界
按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的解釋,大地是存在自明的獨有,是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渾然整體的寂靜所在,是最直接在眼前的也是隱約不在眼前的部分共同組成的向外釋放的信號。在追趕大地的腳下是無數自我和他者共同面對的眾生面孔,是時空中每個生命喘息的聲音,是無形的靈魂在萬千雙眼中閃爍的叩問波光。大地處于遮蔽的狀態,文學世界通過事件使大地澄明。文學事件是由文學語言建構起來的一切文本有機組件,包括故事情節、典型人物、場景環境,甚至是文學語言本身,而文學事件構置的獨特性就是作家文本風格的獨特性。
蕭紅的文學世界多以行動單線、語言簡約的人物對比、大量密集的環境和場景描繪構建起來,環境和場景的變數巨大而不可控,凸顯生命存在的艱難,個人生存于這個背景中的主觀能動性被弱化,舍棄個人生命的精神和理性力量的驅動,消弭敘述者對人物的判定,為生命大地的本源呈現去除預設的羈絆。與設法讓生命本質涌現和敞開相比,蕭紅更能從藝術作品本源的隱退一維即大地一維塑造她的文學世界。小說《呼蘭河傳》眾生浮世對生命之大地本源意義的呈現靠的是將眾生編織在呼蘭河岸的廣袤土地上。面對自然海德格爾曾提出“回退步”的思想,“回退步在方始想要到達的東西面前回退,贏得同它的距離。對距離贏得是一種間離(Ent-Fernung),是對有待思想的東西之自行切近的開放” ⑧。
呼蘭河用自己的廣博和原始凝神注目這片土地上每一個被敘述者,以此完成對這座城的生命表達:生命大地本源的秘密被人物木然執拗地施暴宣告著,像生命廣闊海面上洶涌的浪波,使未來的不可知性陡增。死去者像大地的長嘶,留存者失去了施虐對象,余下的只有無盡荒涼,二者共同喚起了生命自身的悲憫和等待救贖。
注釋:
①(德)埃德蒙德·胡塞爾著,倪梁康譯:《現象學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8頁。
②(德)埃德蒙德·胡塞爾著,倪梁康譯:《現象學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③彭依伊:《論蕭紅小說的“女體書寫”》,《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第67-75頁。
④沈巧瓊:《從〈呼蘭河傳〉看蕭紅小說的散文化、詩化特征》,《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4年第2期,第183-186頁。
⑤(德)海德格爾著,何衛平譯:《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83-84頁。
⑥(德)埃德蒙德·胡塞爾著,倪梁康譯:《現象學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頁。
⑦(德)埃德蒙德·胡塞爾著,倪梁康譯:《現象學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頁。
⑧倪梁康等:《現象學與實踐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頁。
參考文獻:
[1](德)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M].倪梁康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2]唐小林.論蕭紅小說中的日常經驗書寫——從《曠野的呼喊》《呼蘭河傳》到《馬伯樂》[J].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9,(01).
[3]沈巧瓊.從《呼蘭河傳》看蕭紅小說的散文化、詩化特征[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4,(02).
[4](日)平石淑子.蕭紅傳[M].崔莉,梁艷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5](德)海德格爾.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M].何衛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作者簡介:
高雪潔,博士研究生,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大學文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當代審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