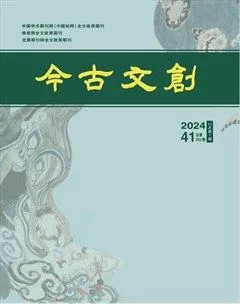女性的覺醒與自救 :從愛瑪的幻滅到卡蘿爾的自救
【摘要】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與辛克萊·劉易斯的《大街》都塑造了“激情而富有幻想”的女性形象。《包法利夫人》中愛瑪沉溺于虛幻的浪漫愛情幻想中不可自拔,在一次次被情人拋棄后,面對巨額的債務最終選擇了自殺。而《大街》中的卡蘿爾有著鮮明的自我意識,在一次次改革小鎮失敗后,看清了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差距,選擇了自救。她帶著孩子離開丈夫,獨自到紐約工作生活。盡管最后卡蘿爾再次和丈夫一起回到小鎮,但她能夠以更成熟的心態看待大街的人和事。
【關鍵詞】浪漫幻想;自我意識;覺醒與自救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1-005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6
《包法利夫人》是福樓拜的代表作。小說真實地展示了1848年后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社會風貌,那時的整個社會彌漫著享樂主義的頹廢氣息,拿破侖戰爭的失敗代表著法國資產階級引以為榮的英雄時代落下帷幕,只剩下一地狼藉的現實生活與一群汲汲營營、貪圖享樂的資產階級凡夫俗子。愛瑪生活在這樣貪圖享樂的平庸年代,沉溺于不切實際的幻想中,三番四次地偷情以追尋理想浪漫愛情,最終落得自殺的悲慘結局。包法利夫人不是一個人,是那個時代眾多女性的縮影。
辛克萊·劉易斯是美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20年劉易斯發表了成名作《大街》。小說的主人公卡蘿爾有著鮮明的自我意識,她渴望實現自己“建設偉大小鎮”的理想。但婚后卻依然只能被迫困于家庭中,更多的是操勞家庭中的內務以及照顧孩子,卡蘿爾才能、個性難以得到施展。在一系列的反抗失敗之后,卡蘿爾決心離開小鎮離開丈夫到紐約工作。
一、被塑造的“激情而浪漫”的少女
(一)愛瑪激情而浪漫的“理想愛情”
愛瑪生活在以享樂頹廢為風氣的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社會中,少女時代在修道院中度過。在修道院,少女時代的愛瑪沉浸在書本中對浪漫理想愛情與奢華貴族生活的描繪中,她看到的是“是戀愛、情男、情女、在冷清的亭子暈倒的落難命婦、站站遇害的驛夫、頁頁倒斃的馬匹、陰暗的森林、心亂、立誓、嗚咽、眼淚與吻、月下小艇、林中夜鶯、公子勇敢如獅,溫柔如羔羊,人品無雙,永遠衣冠楚楚,哭起來淚如泉涌”[1]35。她渴望著自己能夠如同書中的人物一般,住在華麗的古老莊園,身著華美的服飾遙望著一位騎著黑馬的騎士,發生一段浪漫凄美的愛情歷險。在這樣文化的熏陶下,她“愛海只愛海的驚濤駭浪,愛青草僅僅愛青草遍生于廢墟之間。她必須從事物得到某種好處;凡不能直接有助于她的感情發泄的,她就看成無用之物,棄置不顧——正因為天性多感,遠在藝術愛好之上,她尋找的是情緒,并非風景。”[1]35
愛瑪是被人為塑造的“激情而浪漫”的少女,她向往著能夠與像騎士一樣的貴公子發生一段浪漫的愛情冒險。但修道院生活帶給她的只是滿腦子的詩情畫意,是“風雅奢華”的貴族生活,與這套思想感情和愛瑪的現實生活相隔甚遠。她只是一個普通的鄉村女孩,她所具有的浪漫趣味已經超出自身的階級,鄉村平庸瑣碎的生活無法滿足她對貴族浪漫生活的渴望,反而激發了她的不滿,使她更深一步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生活之中無法自拔,這就注定了愛瑪所渴望的“理想愛情”與“貴族生活”注定幻滅,也注定了愛瑪的悲劇結局。
(二)卡蘿爾激情而浪漫的“理想事業”
卡蘿爾出生在美國中部的小城曼卡托,家境良好,父親是當地的法官,母親很早就離世了。童年時代的卡蘿爾是在“博學多聞、和藹可親”的父親的教導和陪伴下度過的。父親會給年幼的卡蘿爾講各種各樣神奇的故事,并且父親不會限制女兒的閱讀范圍,“米爾福德法官教導子女的原則,就是讓孩子們愛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卡蘿爾在父親那間糊上棕色花墻紙的圖書室里,潛心研讀了巴爾扎克、拉伯雷、梭羅和馬克斯·穆勒的作品。父親一板一眼地指著大百科全書書脊教子女們認英文字。”[2]11在這樣的教導下,卡蘿爾的視野更為廣大,不局限在浪漫的愛情小說中。
學生時代卡蘿爾在布洛杰特學院讀書,她富有進取心,興趣廣泛,在學校積極參加各項活動,她打網球,和同學聚餐,參加研究生的戲劇討論會,參加各種社團活動,這些活動涉及她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來她對社會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業在即她拒絕了斯奈德的求愛,確定了自己的建設大街的理想——
“我要到草原上的鄉鎮去工作,以便使它們變得美麗起來。我要去做一個啟迪人們心靈的人。我想最好就當一名教師吧,可是我偏偏不要做像他們那樣的教師。我壓根兒不想那樣渾渾噩噩下去。為什么大家都到長島去興建那么多的花園住宅區,可就是沒有人想到咱們西北部這些寒傖的鄉鎮?他們只知道舉辦什么福音布道會,建立什么收藏埃爾西兒童讀物的圖書館。我可要使每一個鄉鎮都有街心花園和草坪、小巧玲瓏的房子,以及一條漂漂亮亮的大街!”[2]9
從卡蘿爾的宣言中,能感受到她有著鮮明的自我意識,明確自己“建設鄉村”的理想。卡蘿爾的理想是并不是如愛瑪一般建立在“理想愛情”之上,而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價值是什么。盡管卡蘿爾的理想也帶有巨大的非現實性,可已經和愛瑪的愛情幻想著有巨大的差別。
二、婚后生活——幻想的破滅
(一)愛瑪的一步步墮落
愛瑪是為了體驗理想中的愛情嫁給包法利的,她把書本中男女主人公的浪漫愛情轉移到包法利身上,期待能夠過上自己心目中浪漫風雅的生活。她渴望的是“住在城里,市聲喧雜,劇場一片音響,舞會燈火輝煌,她們過著心曠神怡的生活”[1]40,可是卻很快發現婚后的一切和自己想象中的生活完全不同。愛瑪看到丈夫的平庸——“查理的談吐就像人行道一樣平板,見解庸俗,如同來往行人一般,衣著尋常,激不起情緒,也激不起笑或者夢想。他不會游泳,不會比劍,不會放手槍。有一天,她拿傳奇小說里遇到的一個騎馬術語問他,他瞠目不知所對。”[1]39他們生活上越相近,精神上越遙遠。于是她期待著幻想著邂逅另一個男子,他一定和平庸的包法利不同,他想必漂亮、聰明、英俊、奪目。
侯爵府的赴宴徹底將愛瑪在書中看到的“理想生活”照應到現實。她看到了上流社會奢侈的生活——意大利風格的美麗城堡、華美精致的餐廳、瑰麗耀眼的服飾、燈火輝煌的舞會,還有來來往往的精致貴族,每一個細枝末節都在她腦子里生了根。再對比自己貧窮寒酸的小房屋,更加讓愛瑪心碎和怨恨,現實留給她的只是“生活好似天窗朝北的閣樓那樣冷,而煩悶就像默不作聲的蜘蛛,在暗地結網,爬過她的心的每個角落”[1]40。
羅道爾夫的出現正好滿足了愛瑪的激情與愛情幻想。他多金、有趣、英俊,愛瑪無法克制地投入這個情場老手的懷抱中,輕易地被羅道爾夫哄騙到手,緊接著陷入了婚外情的墮落之中,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不可自拔。在羅道爾夫這類人心中,他們要的只是享樂,一旦觸碰到到利益和麻煩,會立刻拋棄情人,揚長而去。而愛瑪沒有看到羅道爾夫的虛偽與無恥,她燃燒著自己的欲望,沉浸在自己的激情中,幻想著能夠在羅道爾夫身上獲得“理想的愛情”,過上“理想的生活”,認為這樣的婚外情就是自我價值實現的方式。可是羅道爾夫還是拋棄了愛瑪,親手打碎了愛瑪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然而,萊昂再次出現在愛瑪身邊。她再次投入萊昂的懷抱中,用盡全力緊緊抓住這段她“失而復得”的“浪漫愛情”。她頻繁出入萊昂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她不惜借債來維持與萊昂的奢靡生活,此時的愛瑪已經完全迷失在了自己編織的夢境中,直到萊昂又一次拋棄了她,而巨額債務卻逼迫上身。愛瑪求助無門,走投無路而服毒自盡,結束了短暫悲劇的一生。
歸根結底,愛瑪將對浪漫愛情的虛幻想象投射在情人身上,實際上是渴望著理想般的貴族生活與浪漫奇幻的愛情,她終究是希望情人能帶來不同于粗鄙現實的理想生活。可是從一開始她的幻想就是虛幻的,所謂的浪漫愛情是建立在奢侈享樂的物質生活基礎上,建立在虛偽風流的情人身上,這樣的生活超越了愛瑪的階級,變得可望而不可即,引誘著愛瑪飛蛾撲火般的渴求,到頭來只能是一場空。
(二)卡蘿爾的自我意識與各項改革的失敗
卡蘿爾首先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她接受肯尼科特求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肯尼科特對戈鎮的描繪、鼓勵她來改革戈鎮的話語滿足了她內心實現自我理想的需要。肯尼科特評價戈鎮:
“老實說,在我所見過的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間,我敢說唯有戈鎮人最富有進取精神。布雷斯納漢—你知道嗎—鼎鼎大名的汽車大王—他就是戈鎮人。他就是在那里土生土長的……再說戈鎮也是個怪漂亮的市鎮。就在市鎮附近,有許許多多美麗的楓樹和北美復葉楓林,還有兩個美極了的大湖!而且現在我們已經修建了七英里長的混凝土人行道,并且每天都在建設中!許多小市鎮人行道上還鋪著木板呢,可我們戈鎮早已變了樣兒,一點兒都不假!”[2]22
正是在肯尼科特的描繪與邀請中卡蘿爾選擇了與他一起回到戈鎮,期待能夠在戈鎮實現自己改造小鎮的理想,實現自我的價值。但是當卡蘿爾跟隨肯尼科特來到戈鎮后,卻發現和她理想中的小鎮模樣相差甚遠——
“戈鎮和他們一路上所看到的無數村莊簡直毫無區別,只不過占地面積較大而已……在戈鎮這里看不出有什么莊嚴的氣派,恐怕也不會有什么前程遠大的希望。只有一座高高的紅色谷倉和教堂屋巔上閃閃發光的尖塔,鶴立雞群似的俯瞰著全鎮。總而言之,戈鎮只能算是昔日開拓邊界時的一塊營地。戈鎮的居民一跟他們的房子一樣單調乏味,跟他們的農田一樣平淡無奇。”[2]38-39
卡蘿爾對戈鎮失望極了。盡管戈鎮并不是卡蘿爾想象中的模樣,但她還是愿意去改造它并為此付出努力。為了實現自己“學以致用,造福社會”的理想,卡蘿爾開始嘗試各種方式。
首先,參加婦女讀書會來改造小鎮。卡蘿爾寄希望于讓婦女讀書來改造戈鎮。她逐個上門拜訪婦女讀書會成員中有錢有勢的太太和她們的丈夫,希望能夠募捐資金來改建破舊的市政廳大樓,但是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拒絕了她,沒有人支持她。這一改革計劃最終失敗。
接著,卡蘿爾建議修建收容所改善窮人的生活。她建議修建一個收容所來幫助鎮上的那些住在破爛棚屋里的孤兒寡母和老人們,但婦女讀書會的成員們紛紛反對卡蘿爾的建議。她們認為已經足夠幫助那些窮人了,比如讓窮人來漿洗衣服與幫助植樹、滅蠅等,并且支付給他們報酬。于是卡蘿爾的改革計劃再次失敗。
最后,卡蘿爾準備成立戈鎮戲劇社,希望通過創造美的藝術形象去感化戈鎮的人們,以達到改造戈鎮的目的。在導演戲劇的過程中,卡蘿爾傾注了滿腔的熱情和渾身的力量,然而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卡蘿爾將其對于理想的實現投射到改造小鎮的一系列活動中,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后,她看清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她無法和一成不變的小鎮相契合,于是決定逃離到紐約,開始新的生活。這一舉動具有高度的自覺性,是卡蘿爾最后的自救。
實際上,卡蘿爾和愛瑪的婚后生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作為妻子,她們都被冠以夫姓,被視作丈夫的附庸,沒有獨立地位,陷于家庭瑣事之中,并且不論是包法利還是肯尼科特,他們都無法理解妻子的想法,也沒有深入妻子的內心,他們共同的為生計而奔波,較少關注精神生活。愛瑪將理想生活寄托在情人身上,沉溺在幻想和欲望中,自我欺騙,自我麻痹,最終墮落至深淵。而卡蘿爾相比起來更加理性,她同樣富有激情和幻想,同樣幻想著能夠實現理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后她看清了小鎮的瑣碎、庸俗與沉痼,于是選擇逃離。她沒有一味地沉浸在幻想中無法脫身,更沒有寄希望于情人。所以從始至終卡蘿爾比愛瑪都保持著一份清醒和理智。
三、幻滅與自救
愛瑪的服毒自殺宣告了其“理想愛情”徹底幻滅。當她被情人再一次拋棄,當她不惜欠下高額債務去維持奢靡的生活,當她被法院傳票勒令限時歸還債務,當她走投無路時,留給她的不過是一條絕路,她只能自殺。從始至終,愛瑪所追尋的理想愛情都是一場虛幻的泡影,只有她沉溺其中不愿醒來。愛瑪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是享樂頹廢的社會風氣,是腐朽人靈魂的宗教布道,是資產階級糜爛的欲望與汲汲營營的茍且以及都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沖擊一步步將以愛瑪為典型代表的女性推向深淵。
卡蘿爾在意識到無法在戈鎮實現自我價值后,選擇逃離,離開丈夫來到紐約,獨立工作和撫養孩子。這是卡蘿爾最重要的轉變,她的離開彰顯了真正的獨立精神,不僅是在經濟上,也同樣是在思想上的自主獨立。事實上,離開到紐約后的生活認識才使得卡蘿爾真正地覺悟與成熟,她發現其實大城市中的人們同樣思想保守、價值狹隘,充滿了等級關系,與戈鎮居民并無兩樣。她真正意識到“大街”的無處不在,雖逃離了“柵欄圍繞”的草原小鎮,卻依然受限于現實社會的各種規則。[3]50紐約兩年的工作生活使卡蘿爾徹底地認清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也使得卡蘿爾放下不切實際的幻想,腳踏實地地面對生活。
同時,肯尼科特前往紐約尋找妻子,也試著去理解妻子,最后卡蘿爾選擇和丈夫一起回到戈鎮。這一次的回歸也代表著卡蘿爾的徹底醒悟,代表著卡蘿爾對家庭的重新接納。
卡蘿爾回歸戈鎮是一種頓悟后的“理性”選擇,以更加“成熟”的心態在社會規則的框架下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她已經理解了戈鎮的社會規則,并以這一套標準來要求自己,在區別他人和融入他人的雙重關系中漸漸獲得平衡,努力融入現實社會。[3]50她的回歸不僅僅是妥協,更是有意識地去尋找到一種平衡點,她意識到女性想要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想要實現自己價值,就必須學會在自己和社會之間找到一種和諧的模式。
愛瑪的人生是一場絢爛而破敗的幻滅,從未覺醒的她沉浸在虛幻的激情中,終究是黃粱一夢,夢醒后一地的狼藉和債務纏身。卡蘿爾在看清了現實的真相后,沒有如愛瑪般自我沉溺與欺騙,而是選擇離開,獨自工作和生活。盡管卡蘿爾最后選擇了和丈夫一起回到小鎮,但能以更成熟的心態看待大街的人和事。這不是代表著她的妥協,而是代表了卡蘿爾有意識地尋找著理想和現實中的平衡點,這也是卡蘿爾身上的藝術魅力所在。
參考文獻:
[1](法)福樓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2](美)辛克萊·劉易斯.大街[M].潘慶齡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3]葉興,周亞瓊.成長小說視角下卡蘿爾的螺旋式人生[J].江蘇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10(1): 49-51.
[4]汪火焰,田傳茂.鏡子與影子——略論福樓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J].外國文學研究,2001,23(1):72-77.
[5]王宇琪,楊東英.女性主義視角下《覺醒》和《大街》的比較分析[J].新楚文化,2022,(05):34-38.
[6]楊海鷗.論《大街》中卡蘿爾的實用理想主義[J].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理論研究),2010,(03):10-13.
[7]王穎.《包法利夫人》愛瑪的自我存在[J].文教資料,2017,(9):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