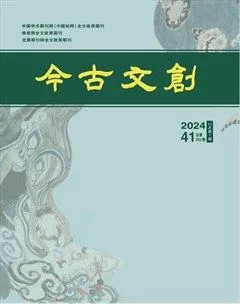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孫子兵法》功利戰爭觀研究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頻繁的戰爭,使孫子對戰爭本質和規律的認識逐漸深入,在其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中表現出國家本位的功利主義戰爭觀。“利戰”思想是《孫子兵法》的主體思想,具體表現為“安國利主”的功利戰爭觀,“非危不戰”的理性戰爭觀,“上兵伐謀”的謀略至上思想。從根本來講,無論是慎戰備戰的理性思想,還是用勢用間的重謀思想,其最終目的都是使國家利益最大化。
【關鍵詞】《孫子兵法》;戰爭觀;功利主義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1-006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8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兼并盛行,戰爭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頻繁的戰爭刺激著中國古典兵學的萌生發展,戰爭觀也在戰爭實踐中逐漸深刻化,系統化。可以說,先秦時期中國古代戰爭觀的基本特點就已初步成型,確定了后世戰爭觀的發展方向。《孫子兵法》作為中國古代兵家的開山之作,表現出兵家在戰爭實踐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學派的獨特戰爭觀。
一、“安國利主”的功利主義戰爭觀
古往今來大大小小的戰爭都與“利”密不可分,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爭奪是戰爭的主要驅動力。周朝以前,由于缺乏倫理道德的束縛,為爭奪自然資源和生存空間而頻繁爆發的部落戰爭常常是血腥暴虐的,黃帝擒拿蚩尤后“(剝)其□革以為干侯,使人射之……充其胃以為鞫(鞠),使人執之” ①。后羿被寒浞等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②。部落首領們為了鼓舞士氣,常假借神的旨意彰顯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如天降預兆、戰前占卜算卦,以鬼神天命掩蓋本質上對“利”的追求,這一時期所謂的“天命戰爭觀”實際上是以爭奪經濟與政治資源為主要目的的“功利戰爭觀”。
周公制禮作樂后,提出 “惟德是輔”的敬德保民思想,在兵事上規范了戰爭的基本倫理道德,春秋時期的爭霸戰爭在禮法的束縛下表現出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但從根本來講,無論是“尊王攘夷”的口號,還是“奉旨勤王”的旗幟,都只是給不義的爭霸戰爭披上一層尊禮守法的外衣,其本質仍然是以逐利為目的的暴力戰爭。春秋中后期至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王綱解紐,諸侯霸主們紛紛撕下“禮法”的外衣,在利益的驅動下頻繁發動兼并戰爭,毫不掩飾對權利的追逐和渴望。盡管有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家們四處奔走,宣揚“仁政”“王道”的民本主義思想,但有戰爭實際操縱權的君主將領們,顯然更傾向于實行“霸道”的功利主義戰爭觀,以雷霆手段派遣士兵四處征戰,兼并土地,擴大領土。即使嘴上說著“撫民”“保民”的話,也只是把它當作“勞民”“馭民”的政治手段,以免造成民心不穩,國家內憂外患,動蕩不安的局面。因此,思想家們的“民本戰爭觀”在春秋戰國時期并未得到實現。
“利”作為戰爭的價值核心和實際驅動力,始終主導著中國古代戰爭的興起、發展和結局。無論戰爭的發動者們借著天神的旨意還是披著尊王的外衣,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利”。在中國古代軍事戰爭史上,最先肯定功利主義戰爭觀,宣揚“利戰”思想的是春秋末期的兵圣孫武。孫武直言:“兵,利也,非好也”[2],承認“利”是戰爭的首要目的。其軍事思想著作《孫子兵法》雖然篇幅不長,但精練地反映了孫子理性的功利主義戰爭觀,“利戰”作為中心思想,起到統領全書的重要作用。《孫子兵法》中“利”共出現52次,“軍爭為利”[2],“兵以利動”[2],“非利不動”[2],“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則止”[2]等言論反復強調“利”的重要地位。
《孫子兵法》中“利”的主要對象是國家和君王,表現出“國家本位”與“君王本位”的功利主義戰爭觀。有學者將“民本”作為《孫子兵法》的主體思想,認為《孫子兵法》“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③,其中愛卒、愛民、善待戰俘等觀點“閃爍著人本思想的光芒” ④。但聯系上下文整體分析,以上這三種行為無不以“利”為前提,表面上是以民為本,歸根結底其內核還是以利為先。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2]是軍中將領馭下的手段,“愛而不能令……不可用也”[2],愛卒的根本目的是令卒、用卒,關心愛護士兵,獲得士兵的尊重與愛戴的根本目的,是在戰場上能更好地命令、指揮士兵,是能驅遣士兵“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2]。讓士兵完全服從于將領的命令,為戰爭的勝利,國家和君主的利益付出一切。為激發士兵的潛能和勇氣,可以將士兵“投之亡地”“陷之死地”[2],以此提高戰爭的勝率。由此觀之,在孫子看來,戰爭取得勝利的價值遠高于士兵的價值,無論用什么手段,最終目的都是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使國家取得戰爭的勝利,實際上是以取勝為目的的功利主義思想。
“民”在書中共出現10次,《始計》篇“令民與上同意也”[2]一句,之所以是“民與上同意”而非“上與民同意”,是在令百姓去主動順從君王的意志,聽從君王的旨意,服從君王的調遣,百姓的意志與意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主的命令與決策,百姓只需要無條件服從君主的一切決策,實際上是在強調君王的絕對權威性。“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2]這句話突出的是懂得用兵規律的將領在戰場上的重要性,將領的優秀與否決定了一場戰爭的勝負,決定了百姓與士兵的生死,決定了國家的安危存亡。將領的才能往往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2]。將領承擔著國家和百姓安危的重擔,只有掌握用兵作戰的規律,做好全勝的準備,才能保護士兵和百姓,才能保全國家,保住疆土。“勝者之戰民也”“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專一”“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2]中的“民”都不指百姓,而是指士卒。“愛民可煩”[2]是說愛護民眾的將領往往會被民眾牽制,給敵人可乘之機,“愛民”在這里顯然是被否定的,孫子認為將領應當時刻保持理智與冷靜,以戰爭的勝利為一切決策的前提,為了確保戰爭的勝利,將領可以舍棄一切,包括士兵和百姓的生命,戰爭的勝利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2]中的“人”也指民眾,保護民眾而有利于君主的將領是國家的珍寶,“唯人是保”的前提是要符合君主的利益,是要“令民與上同意也”,最終目的還是落到保護國家的根本利益上。
“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2]的“善俘”行為,常被認為突出表現了孫子以民為本的人道主義思想。但從《作戰篇》的整體結構來分析,善俘的出發點還是“利”。開篇孫子列舉軍隊出征前的龐大軍費開支,“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2],尚未出征便日費千金,軍隊出征后,行軍路途與作戰時所耗軍費更甚,為避免面臨“久暴師則國用不足”[2]的窘境,孫子提出兩點建議。其一是速戰速決的“速勝論”,作戰時間拖得越久,對國家的損耗就越大,“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2]行軍打仗最忌拖延遲緩,在外耽擱一日,國庫的負擔便加重一日,戰局便有可能出現動蕩,因此速戰速決有利于節省國家錢糧,增加軍隊勝率。其二是以戰養戰,取用于敵的計策。孫子認為糧食可以從敵國獲取,“智將務食于敵”[2],“因糧于敵”[2],從敵國獲取敵軍的糧草,既減輕了本國軍費開支的壓力,同時也緩解了本國糧草長途運輸的壓力,減少運輸途中人力物力的損耗;戰車也可以從敵國搶奪,“車戰得車十乘以上”“取敵之利者”[2]要加以獎賞,以此類推,“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2],敵國的戰車可以搶奪并收編到我軍戰車中,敵國被俘的士卒也可以加以善待,并收編到我軍士卒中,提高我軍戰斗力,“是謂勝敵而益強”[2]。因此,整體來看“卒善而養之”在這里強調的并非是孫子的民本主義思想,而是以戰養戰,取用于敵的國家本位功利主義思想。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孫子始終將國家的安危排在首位,國家的生死存亡高于一切。為達到“安國利主”[2]的目的,將領可以使用一切詭道計謀來獲取戰爭的最終勝利,表現出兵家區別于儒墨道的功利主義戰爭觀。受到周禮敬德保民思想的影響,孫子的戰爭觀也不同于原始時期的血腥暴力戰爭,具有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理性色彩。
二、“非危不戰”的理性主義戰爭觀
李澤厚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提出,《孫子兵法》表現出區別于道家和法家的“對待人生世事的極端清醒冷靜的理性態度”。所謂理性態度,就是“一切以現實利害為依據,反對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愛憎和任何觀念上的鬼神‘天意’,來替代或影響理智的判斷和謀劃” ⑤。兵家較之原始部落和周禮,對戰爭有了更為理性的認識,不再受鬼神觀念的束縛,重視戰爭中人的作用。
孫子認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2]君主和將領為確保戰爭的勝利,要事先探明敵情,盡可能詳細地了解對方的詳細情況,如糧草存量,士兵狀態,調兵部署情況等。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2],對敵方動態情況的了解越詳細,我方獲勝的概率就越大。但敵情的獲取,不能依托于祭祀鬼神、占卜、祈禱等迷信手段,也不能根據日月星象草草推驗而得,必須“取于人”,從了解敵情的人身上獲取情報。而了解敵情的人,即由我方培養,送到敵營中獲取情報的間諜,間諜在兩軍作戰時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敵軍的駐扎位置,行軍路線,軍隊情況,甚至于軍隊布防,將領謀劃,都可以通過間諜之口得知,預先布防應對,大大提高我軍的勝率。在鬼神觀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孫子明確指出戰時占卜祭祀的非理性特征,以及可能對國家生死存亡造成的嚴重后果,強調人在戰爭中的主觀能動性和決定性作用,表現出理性主義色彩。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2],孫子的理性主義戰爭觀還表現在他對戰爭危害的清醒認識。“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2]興師遠征是個勞民傷財的大工程,十萬的軍隊不僅需要勞動七十萬百姓荒廢田地,沿途運輸物資,而且“日費千金”,這樣算來一年就是幾十萬金的花銷,有時甚至要“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2],軍隊長時間在外奔波駐扎,衣食住行皆要消耗國庫錢財,如此計算,耗費在戰爭上的錢財簡直難以估量。這樣勞民傷財的興兵作戰,若是幸運地取得勝利,收繳敵軍物資,開拓我國疆土,還能稍微彌補戰爭的損耗。可往往情況是“修櫓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2]耗費幾個月的時間打造攻城器械,又犧牲掉三分之一的士卒去攻城,城池卻依舊攻不下來,平白耗損資源不說,如此大規模勞民傷財卻毫無所獲,沉重地打擊了國家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
為趨利避害,減少戰爭對國家的危害,孫子提出“慎戰”和“備戰”思想。“慎戰”即君王和將領要謹慎發動戰爭,“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2],是否發動戰爭取決于國家的利益、勝率和形勢,沒有利益不要行動,不能取勝不要用兵,沒到危急關頭不要輕易發動戰爭,時刻以國家根本利益為主,三思而后定。君主和將領必須保持清醒冷靜的理性態度,切不可暴躁易怒,情緒激動起伏大,所謂“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2],主帥在情緒的刺激下草率發動戰爭,不僅會使士卒大量犧牲,也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亡國不可以復存”[2]的巨大災難。孫子的“慎戰”思想實際上也是建立在國家本位基礎上的利戰思想。
如果說“慎戰”是站在戰爭發動者的角度分析戰爭的最佳時機,那么“備戰”就是站在戰爭承受者的角度,思考敵軍發動侵略戰爭時,我軍如何打贏保衛戰,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孫子認為,贏得保衛戰勝利的秘訣就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只要能做到“有以待”“不可攻”,國家就能立于不敗之地。所謂“有以待”“不可攻”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其一要提高警戒,做好敵軍隨時入侵的準備,時刻保持引而待發的高度戒備狀態。要安排好士兵巡邏,即使在休息時也不可徹底放松警惕。要充盈國庫,儲蓄錢糧軍械,以備不時之需。其二要不斷提高國家軍事實力,增強我軍威懾力。士卒要勤加操練,做到能征善戰,訓練有素,隨時能上陣殺敵;將領要勤習兵法,有勇有謀,做到“通于九變之利”[2],在戰場上氣定神閑,指揮若定。要預先備好作戰方案,“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2],隨時根據地形地勢特點和政治外交形勢調整作戰方案;君主要勵精圖治,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使城池堅固,國庫充盈,裝備精良,具有“先為不可勝”[2]的實力,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2]。
孫子的理性主義戰爭觀,突破了原始天命觀的束縛,強調將領在戰爭中的決定作用,警示君主和將領謹慎發動戰爭,戰時要始終保持清醒冷靜的理性態度,非戰時要做好備戰工作,使國家立于不敗之地。
三、“上兵伐謀”的謀略至上戰爭觀
中國古代兵書大致分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后戰。” ⑥治兵與治國不同,治國是長期持久的工作,要以正當合理的統治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而兵事往往是成敗一夕之間,因此戰場上講究權謀,要出奇謀以致勝。《孫子兵法》是兵權謀類軍事著作,其中示形任勢、虛實奇正、用間先知等思想都表現出謀略至上的戰爭觀。
“形勢”是兵力的部署與運用,將領在戰場上要靈活機動地運用“形勢”,取得勝利。分開來講,“形”是軍事實力的建設,“勢”是在“形”的基礎上,正確運用軍事實力以取得戰爭的勝利。錢基博注:“形者,量敵而審己,籌之于未戰之先。勢者,因利而制權,決于臨戰之日。” ⑦“形”是戰前根據敵方情勢,做好我方軍事建設,“強弱,形也”[2],軍事實力強弱是確定的。“勢”是戰時根據戰場上利害得失,做出及時決策應變,“勇怯,勢也”[2],士兵表現的是勇是怯是隨機的。“形”有先定之數,形勝在己不在敵,戰事未始,以敵我雙方之“形”就能基本判斷出戰爭勝負,具體來講“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2],田畝數量決定糧食產量,糧食產量決定兵員多寡,兵員多寡決定軍隊戰力,兵多糧足者勝,這就是戰前可見之“形”。孫子將“形”巧妙地解釋為“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2],在山澗上積水是“形”,決水就是“勢”。將領在戰場上管理士兵,分配部署兵力,指揮作戰,士兵以“激水之疾”“鷙鳥之疾”[2]向敵方迅速猛烈發起進攻,這就是“勢”。孫子將“勢”比作“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2],從高山上滾落的石頭速度極快,威力巨大,戰場上善于借“勢”的將領,往往能使軍隊如滾石般勢不可擋,一戰而勝。
“形勢”又可分為“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種,前兩者是治兵方法,管理很多人如同管理很少人,指揮很多人如同指揮很少人。后兩者是用兵方法,兵力部署要奇正相生、虛實相生、變化無窮。李零先生認為“奇正”和“虛實”的區別在于,“奇正”是點上的兵力配置,“虛實”是面上的分散集結 ⑧。中路走大軍“形以應形”,側路出奇兵“無形以制形” ⑨。即為“奇正”之法,調動大軍避實擊虛,隱實示虛即為“虛實”之法。孫子認為,對敵軍要避實擊虛,出其不意,我軍要隱實示虛,千變萬化,使敵人“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2]。戰場上敵我雙方的虛實并非一成不變,“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2]因此,將領要掌握并運用戰爭規律,敵眾我寡時,使“我專而敵分”[2],逐個擊破。要抓住瞬息萬變的時機,“攻其所必救”“乖其所之”[2]來扭轉戰局,掌握主動權。
如果說“形勢”側重軍事實力的建設與運用,那么用間與先知就是對軍事情報的探查與利用。孫子認為間諜在戰爭中起著重要作用,“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2]不了解敵我軍情就難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戰前探察軍情不能求神問卦,要依靠間諜,間諜探得的情報能使我軍料敵于先,謀敵于前,占得先機,極大提高我軍勝率。孫子將間諜分為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五類,介紹了不同間諜的不同用法,并對用間的君王和將領提出條件和要求,只有“圣智”“仁義”“微妙”的人才能用間,對待間諜要堅持“親”“厚”“密”[2]的原則。“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2]善用間諜是“兵之要”[2],是“人君之寶”[2],孫子對間諜與情報的重視實際上就是對“智”與“謀”的重視,準確的情報可以大大減少士兵的損耗,巧妙使用計謀遠勝于一味蠻力進攻,所謂“上兵伐謀”[2]者,謀略的使用往往可以大幅度提高作戰效率,實現我軍利益最大化。
四、結語
《孫子兵法》是孫子在春秋戰國時期頻繁的戰爭實踐中形成的,對戰爭本質和規律的獨特認識,表現出不同于原始戰爭的理性色彩,和區別于儒墨道等學派的利戰思想。“利戰”思想是《孫子兵法》中其他一切思想的最終指向,慎戰和備戰思想的提出在于減少國家損失,形勢與間諜等謀略的使用在于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歸根結底,《孫子兵法》集中體現了孫子國家本位的功利主義戰爭觀。
注釋:
①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18年版。
③藍永蔚:《〈孫子兵法〉時代特征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④孫喆:《略論〈孫子兵法〉中的人本思想》,《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26期。
⑤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08年版。
⑥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⑦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⑧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中華書局2006年版。
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參考文獻:
[1]孫武,曹操,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北京:中華書局,1999.
[2]銀雀山漢墓簡竹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3]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5]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M].北京:中華書局, 2006.
[6]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 2006.
[7]李零.孫子古本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8]楊丙安.孫子會箋[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9]施芝華.孫子兵法新解[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10](日)服部千春.孫子兵法校解[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11]于汝波.孫子兵法研究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
[12]褚良才.孫子兵法研究與應用[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13]郭化若.孫子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4]龔留柱.《孫子兵法》戰爭觀諸說駁論[J].濱州學院學報,2010,26,(05):57-62.
[15]龔留柱.《孫子兵法》與先秦軍事倫理思想的發展[J].濱州學院學報,2010,26,(01):1-6.
[16]程遠.先秦戰爭觀研究[D].西北大學,2005.
[17]李桂生.先秦兵家研究[D].浙江大學,2005.
作者簡介:
闞尉航,女,漢族,遼寧大連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