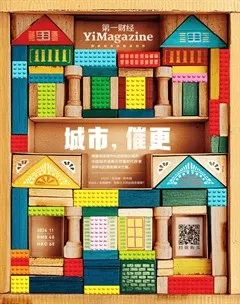城市到底在“更新”什么?

如果說城市是一臺長期運轉的“超級機器”,那它難免也要面對各種故障和零件老化。針對規劃用地變化、建筑物日久失修、生活居住環境亟需改善等需求,政府和城市治理機構在為城市尋找一系列解決方案。這些領域里的各種嘗試,人們通常稱之為“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城市在更新什么?
“城市更新”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949年美國的《住宅法》中,指拆除老城區危房和貧民窟,然后在這塊地上建造現代化的高層住宅、商業街區和交通基礎設施。
全球各地城市更新主要開始于“二戰”之后—從重建被戰爭摧毀的城市開始。為了應對城市擴張,英國在1946年就出臺了《新城法》,成立能夠強制征地的國企開發公司,以支持全國76個城市的更新需求。之后的30年里,英國多了32座新城,平均每座城市人口超過5萬。政府為此不斷修改法律,提高開發項目的最高借貸限額,為新生的城市修改行政體系。這一時期,不止是英國,各個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建筑師、意見領袖們都富有激情地討論“什么是理想生活”,拆除他們認為過時的老建筑,興建大型集合住宅和地標建筑。
1958年,荷蘭海牙舉辦了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討會,旨在向美國城市規劃師介紹歐洲的戰后重建工作。美國的專業人士當時急于借鑒歐洲經驗,試圖像歐洲人一樣,在市中心劃出人行步道,而不是為汽車規劃道路,為區域和建筑規定更精細的多種用途。
參會者還進一步探討了城市更新的意義和定義:小到城市居民對自有房屋的修理改造,大到城市基礎設施的更新換代,“有關城市改善的建設活動”都可以被看作城市更新。
但根據1965年美國城市規劃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當時的城市更新也有局限。1949年至1964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事關城市更新的所有支出中,只有2%用于重新安置當地居民,過半被征收的土地因為資金不足、無人開發中荒置,另一半則被政府低價出售給了私人開發商,在規劃上也是種族隔離的作派。
“許多清理區(波士頓西區就是一個例子)之所以被選中,并不是因為那里有最糟糕的貧民窟,而是因為它們是建造豪華住宅的最佳地點—無論城市更新計劃是否存在,這些住宅都會被建造。”美國經濟學家、政府顧問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在其著作《聯邦推土機》中辛辣地批評。
這個觀點可能有些過火,但另一位規劃學家切斯特·哈特曼(Chester Hartman)剛好研究過波士頓西區的意大利人聚居區—這個地方被城市更新管理局判定為貧民窟,結果表明,項目結束后,71%的白人居民搬到了當地“更優質的住宅”里,但需要支付的租金漲了70%。
1970年代,全球城市更新策略又迎來變化。1970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住房和城市發展法》,更加強調保護社區,提高居民參與度。各國政府整改城市中心的居民區和工業區使得人口外流,居民失去工作機會,老城區空置,于是,再次開發市中心、振興產業成了政府的新目標。
1980年,英國政府通過《地方政府、規劃和土地法》,社會資本自此登上城市更新的舞臺。該法案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就工程合同公開招標,并建立開發公司,政府和私營企業共同持股。他們的任務說白了只有一項:吸引人們回到城市。
美國學者、城市規劃師尤金妮·L·伯奇(Eugenie L. Birch)在2007年的著作《土地政策及其后果》中指出:21世紀,人們對城市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經過政府和開發公司多年運作,城市重新成為人才和資源的代名詞;市中心不再是貧困和犯罪的溫床,人們反而盛贊這些地方擁有歷史文化遺產和強大的社區。
在中國,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合肥、蘇州、常州等城市,都開展了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拆遷”這個詞,也是伴隨一代人的城市時代記憶。

如今,廣義上的城市更新涉及城市重建、舊城改造、城市再開發、城市復興等范疇。它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復雜,城市更新的手段也不再局限于建筑物拆改,而是轉向采取更多維度的方法。
近200年來,城市更新的背后大多有政府的身影,它們從公共利益出發,主導或發起不同的項目。但傳統政府背景的城市更新機構正變得更有綜合性。
中國香港的市區重建局就是一個綜合了各種城市更新職能的法定機構。它的前身為1988年成立的香港土地發展公司,2001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市區重建局由此誕生。市區重建局可以與業主談判,以合理市場價收購其房產,作為法定機構,也有在限制條件下直接征用土地以加快香港市區重建進度的權力。除此之外,市區重建局還要修繕老房子,改善市區環境,推進居民的安置及補償、重建規劃及文物保護等事務。
同一時期,在日本也誕生了類似的組織,名叫“都市再生機構”(以下簡稱“UR”)。UR是獨立行政法人,歸日本國土交通省直轄,自負盈虧。UR的前身是“日本住宅公團”,曾負責開發“團地住宅”—類似于中國的公房。2004年它更名為“都市再生機構”,職能也不再是拼命建公寓樓,而是管理名下住宅租賃,并參與各大城市更新項目。由于兼具政府背景和公司兩種屬性,在復雜的城市更新項目中UR負責統籌各個利益相關方。

現在,更多利益主體期望直接參與街區事務。幾乎所有城市更新的決策過程,都涉及到公開聽證會、咨詢會以及街區活動。“街區也認識到,讓私營部門參與街區振興工作很關鍵。(在城市更新中)街區發展委員會處于戰略地位,這個組織可以爭取到當地居民的支持,從而讓項目贏得公眾的廣泛認可。”伯奇寫道。
在城市更新這個領域,一個組織或機構可能早已無法推動一個利益關聯廣泛的綜合項目,每個國家、每座城市都面臨不同的問題,政府、企業和居民力量等多方之間總是在不斷角力。
城市更新,不止是政府的事
城市更新并非政府一方的工作與責任。這類項目常常面臨建設時間長、啟動資金高的困境,為緩解財政壓力,政府會嘗試引入市場領域的合作方,另一方面這也是為了將建設規劃工作交給更專業的人來做。全球主流的城市更新模式是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與企業等社會資本合作。
PPP最初出現在基礎設施建設中,許多早期的鐵路系統就是私人公司與政府合作建造的。現代PPP則發源于英國。在1992年,英國政府提出了PPP最具代表性的方法—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即“私人融資活動”。它指的是利用私人資金和專業知識,在公共設施等的設計、建設、維護管理和運營中,由私營部門主導提供公共服務。此類項目中,政府不再負責公共設施的建筑工程,而是通過長期合同,將建設和運營任務外包給私營部門。
英國倫敦國王十字街區(King’s Cross)城市更新是典型的PPP項目。國家和地方政府、鐵路公司、房產開發商合作推動了該地區的城市更新。
國王十字地區曾經是倫敦物資交換的門戶,自維多利亞時代開始,它就是英國的重要的工業運輸中心。但鐵路運輸的衰退讓這里變得蕭條。國王十字車站也位于這個區域,它和圣潘克拉斯站(St. Pancras Station)連接了這里與英國中北部幾個重要工業城市。

1996年,國王十字街區迎來了轉機。英國政府決定將鐵道線“High Speed 1”(HS1)的終點站從倫敦的滑鐵盧車站改為圣潘克拉斯車站,使其與英國國內鐵路網絡“無縫連接”,英國政府也希望此舉成為國王十字地區更新的起爆劑。HS1上運行的“歐洲之星”列車,將穿越英法海底隧道,進一步連接倫敦和歐陸地區。
當時,英國政府持有國王十字車站和圣潘克拉斯車站及周邊部分地區的土地產權,另一家公司Exel(后被敦豪公司收購)也擁有國王十字區域內大量土地,其他地權由一些小業主分散持有。
中標HS1建設工程的是倫敦和歐陸鐵路公司(LCR)。當時LCR是一家私營財團,2009年時它因經營不善被英國政府收購。英國政府向LCR注資數十億英鎊,LCR還獲得了HS1沿線地塊的開發權以及國王十字街區周邊物業的開發權,而LCR需要將街區更新項目的一半凈利潤返還給政府。隨著HS1建設的推進,LCR慢慢從單純的鐵路建設公司轉變成了物業開發和資產管理機構。
2001年,LCR委托房產開發商Argent負責區域的整體開發,這兩家公司在2008年聯合Exel公司共同成立了國王十字中心有限公司(KCCLP)。到2014年時,KCCLP這家公司成了國王十字地區土地的單一所有人,這意味著基礎設施建設變得更便利,供熱、供電公司不再需要疏通復雜的產權關系。同時,該區域的城市更新有了更多的資金來源,比如KCCLP接受了澳大利亞最大的養老金基金之一AustralianSuper的投資。

KCCLP承擔了與各級政府、組織溝通的職責。除了需要從政府拿到開發許可,他們還要與負責遺產保護的組織溝通區域內歷史建筑的改造問題,與居民組織溝通以獲取當地人的信任。之后,通過“以點帶面”策略,KCCLP于2002年吸引了中央圣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在國王十字地區開設新校區。它所帶來的人才又吸引了不少大公司入駐,Google和路易威登就把英國總部搬到了這個區域。
PPP模式讓國王十字地區重新煥發了生機。通過政府和開發商的協調,區域內各類主體的利益得到兼顧。在二十多年的城市更新過程中,國王十字街區引入了近2000套新住宅、近10萬平方米的零售空間和50萬平方米的辦公空間。從2010年到2022年,國王十字街區的辦公室的平均租金提升了約一倍。
綜合問題的開發樣板—TOD
交通是城市更新的一大驅動力。“二戰”后,隨著私家車普及和高速公路網擴展,特別是在美國,不少城市逐漸向郊區擴張,中心呈現衰敗趨勢。城市的無序蔓延讓基礎設施服務變得低效,同時浪費了土地資源,也讓城市居民更加依賴駕車出 行。
當人們開始反思私家車帶來的城市問題,“公共交通引導發展”(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的思想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師彼得·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看來,TOD理念強調通過高密度、多功能的土地開發策略,建設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統,減少居民對汽車的依賴。
日本的許多城市長期踐行TOD的發展模式。數個鐵道線路交叉的樞紐區域是城市問題集中爆發的場所。交通樞紐的建設往往基于“過時”的規劃方案,隨著城市人口增多,常常出現用地緊張、基礎設施老舊等問題。在城市更新的語境下,TOD的模式仍舊發揮著作用:升級車站的同時,推動周邊可步行范圍的城市更新。日本鐵道公司的典型做法是,拆除自己在原有街區所有的舊建筑,引入全國連鎖品牌以及自家公司旗下的業態,這樣更容易保證收益。
東京澀谷站周邊區域的城市更新就遵循TOD模式,地區建設由鐵路公司主導。澀谷站于1885年正式開通,隨著線路增加,它逐漸成為東京最大的交通樞紐之一—共有4家鐵路公司的9條線路在這里交匯,平均每天有超過300萬人在這里上下 車。
在澀谷站慢慢發展為交通樞紐的同時,這里也出現了軌道交通、巴士系統換乘動線復雜,以及縱向移動的客流量劇增等問題。車站外,澀谷大十字路口已經成為東京的標志性景觀,緊鄰大十字路口的八公廣場往往人滿為患。同時,軌道和高架隔斷了城市空間,行人想要穿行車站的東西兩側并不容易。
澀谷站周邊區域更新的契機是鐵道“地下化”。為了緩解JR山手線的擁擠,日本政府于2001年規劃了新地鐵線“副都心線”,并且為了與東急東橫線實現互通,決定將地上的東橫線轉移至地下,釋放東橫線的車站和軌道用地。同時,在澀谷站前區域重新規劃空中人行動線和地面巴士樞紐。2005年,政府認定澀谷站周邊地區為“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這意味著,行政部門對該地區的容積率限制更加寬松。
開發商在必須動腦筋圍繞車站做文章的時候,總能想出一些最大化利用有限空間的辦法。東急集團在這輪城市更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改良軌道交通的換乘體驗,他們還積極參與不動產開發。
2003年,隨著東急東橫線“地下化”工程開展,東急集團旗下的綜合商業設施東急文化會館停業了。當時這座8層建筑已經運營了近50年,設施老舊,陷入虧損。9年后,東急文化會館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全新的商業設施—約40層澀谷Hikarie,高樓的地下是東急東橫線與東京地下鐵的換乘通道,地上建筑涵蓋了商業、劇場、辦公等各種功能,展現出名副其實的“立體城市”概念。
開業后的18天內,澀谷Hikarie就吸引了220萬人拜訪。打響這第一炮后,東急集團計劃在20年間在澀谷站周邊新建SHIBUYA STREAM、Shibuya、Scramble Square、Shibuya Sakura Stage等10個商業設施。
除了東京,中國香港也擅長TOD項目。在TOD項目中,中國香港政府首先以車站建設前的市場價格將站點周邊土地的開發權出售給港鐵公司(Mass Transit Railway,MTR),港鐵再與私人開發商聯合開發該地塊。當地鐵站修建完成后,沿線的地產價值提升,港鐵再將部分產權出售,獲得的利潤通過分紅和持股升值的方式還給政府。
TOD常常和其他“人本主義”的城市更新思想一起出現,強調城市的公共空間,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21世紀的城市更新基本以人為主線,比如混合用途開發、公園導向開發、阻止城市衰退的復興主義、社區參與規劃等,各種流派互相影響和促 進。
但和其他理念相比,TOD的成功有很高的門檻,不僅取決于當地是否有足夠高效、能夠聚集人流的公共交通服務,車站周圍設施的初期建設成本投入也很大,需要合理規劃、長期維護。在這個背景下,一些更輕量化的做法開始出現。
輕量化的微型更新
在日本,團地改造項目為這類微型更新提供了一些經驗。日本的團地類似于中國的公房老小區,是日本在戰后為工薪族開發的標準化集體住宅。截至2020年,根據日本政府國土交通省統計,日本全國共有2900個團地住宅小區,其中過半的房齡超過30年,居民也呈現高齡化趨勢。這些團地住宅基本沒有商業和交通配套,很難打動年輕住戶,空置率很高。
曾經負責這些團地開發的獨立行政法人日本住宅公團,也就是如今的UR,也由此開啟了讓團地重生的序幕。原拆原建的做法最為簡單直接,但《日本公寓重建法》規定,每個小區必須有8成所有者通過決議,并重估設計、成本、所有權等問題,才能推進重建計劃。考慮到UR管理著70多萬戶團地住宅,這將是一個漫長而難以協調的流程。
UR不得不尋找讓這些“存量房”更有價值的解決方案。他們找到了無印良品居住空間部門,朝著年輕人會喜歡的方向重新設計住宅內部裝潢。截至2024年10月,雙方已經合作改造了68個團地住宅小區,其中91%的小區全部租了出去,3/4的住戶年齡在40歲以下。這個合作還會延續到UR管理的團地的公共空間里,無印良品會改造店鋪,舉辦市集和工作坊。
幾乎同一時期,一些輕量化的城市議題解決方案也在美國實施。2007年到2013年,時任美國紐約交通局委員珍妮特·薩迪-汗(Janette Sadik-Khan)開啟了一連串“搶街”行動。薩迪-汗自稱是社會活動家簡·雅各布斯理念的繼任者,主張保護現有的社區生活和小尺度街道。她認為,通過簡單的道路規劃—讓市中心多出幾條步行街,就可以提振街區人氣和商業,減少紐約可怕的交通擁堵。
薩迪-汗的任期內沒有任何復雜的大工程。只需要幾十萬美元,讓工人帶上障礙物、油漆和熱塑塑膠,放上露天長椅,就能迅速在街道上設定邊界,建成一個“步行廣場”。將周末的街道禁車,行人就會自發“占領”路面鍛煉身體,孕育各種社區和商業活動。
2009年,紐約交通局下發的交通禁令給時代廣場改造開了個頭,42至47街區禁止行車,整個時代廣場多出了近1萬平方米的步行區域。2011年的數據顯示,時代廣場行人受傷人數、車輛事故和犯罪率都明顯下降,底層商鋪每平方米租金漲了一倍,躋身全球十大零售商圈。
回到中國視野,成都市玉林東路社區的“巷子里”項目也是個值得討論的案例,因為它走通了一條鮮有前例的路子:增建從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一樓延伸出來的新空間,并且因為容納了咖啡館、畫廊、文化活動場所等,社區活力被重新激活。社區黨群書記楊金惠主動向社會公開募集專業人士,找到了一介建筑的創始人張唐,他們一起調研居民需求、艱難籌集款項,落成了“巷子里”。
最初,楊金惠想利用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周邊的空地,做一些適宜殘障人士的改造,由武侯區殘疾人聯合會提供啟動資金。但在居民會議上,大家拒絕接受建筑外觀改造方案,理由是要投入資金,卻沒有為他們的生活著想。楊金惠意識到,她需要一位分析社區現狀、聆聽居民需求的“社區規劃師”。
張唐的經驗起了作用。她不停地找居民聊天、走訪調查,一點點調整思路,種種問題隨之浮現:社區定位中包含藝術文化,卻沒有公共藝術空間;許多流動人口是年輕人,但“15分鐘步行圈”里沒有他們喜愛的小店;一些本地居民找不到合適的交流場所,難以建立對社區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巷子里開業初期,張唐利用外部客流打響知名度,邀請成都10家獨立咖啡店的主理人、藝術家們輪番前來駐場。等客流穩定后再考慮雇用人手。巷子里無需向社區支付租金,收益來自場租和零售分成,但若商業活動和社區活動撞了時間,場地會優先給社區用。這種做法也錯開了外來人群和社區居民,使彼此的生活軌跡不受影響。
巷子里獲得了2020年公共建筑·空間類的日本優良設計大獎(GOOD DESIGN Award2020),如今已運營4年。這些成果說服了社區繼續聘請張唐和一介建筑改造其他場地。誰都沒想到,一塊可以改建的空地,會牽扯出這樣一個完整方案。
但是一個有活力的街區也離不開持續的運營與管理。2020年,日本東京下北澤BONUSTR ACK項目開張,這是個小型商業街,運營公司散步社和土地持有者—私營鐵路公司小田急電鐵簽訂了20年協議。散步社創始人有著社會創新媒體和獨立書店的運營經驗,為了說服有意思的個人小店入駐,這家公司甚至用店家能承受的預估店租倒推建設成本,不停地舉辦經營經驗分享會。等到街區建成開張后,每隔幾周,他們都會在街區空地上舉辦市集,吸引新的訪客。憑借在成本控制與街區文化營造平衡點上的創新,這個項目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社區運營者與開發商的注意。
同樣,在中國,有持續運營能力的機構正成為城市更新參與方看重的重要力量,地產開發商將可以填充進開發項目的運營方式稱為“內容”,開始尋找更有性價比的“會做內容”的企劃者與運營者。但更多地方政府與機構一方面希望讓社區獲得更多關注與活力,卻又面臨缺乏持續運營的人力與資金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具備城市規劃、項目企劃、設計能力、運營管理能力等綜合技能的專業社區營造組織陸續出現。在日本,這類機構已有先行者—“都市再生推進法人”就是日本城市更新進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基于日本20 02年頒布的《都市再生特別處置法》,市、町、村級別的行政單位可以指定有能力和經驗統籌各個利益方的公益團體或公司為“都市再生推進法人”。在政府機構和私人開發商難以觸及的部分公共區域,這些組織會起到補充支援作用。
即便街區“升級”成功,士紳化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這個說法首次出現于1960年代前后的全球城市貧民窟拆除浪潮之中,指的是城市更新進程中,廉價街區因為設施升級、先進規劃理念,在短時間內房價升值。針對士紳化,常見的批評是城市更新造成生活成本上升,讓富裕居民擠走了原住民。
從社區團結的美好故事到“急速士紳化”模板,美國紐約的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只用了10 年。“高線”之名源于一條曼哈頓下西區荒廢已久的城市貨運鐵路高架橋,它途經城中貧困的老工業區。2001年,社區居民拿出改造方案說服政府沿鐵路造一個可以深入街區的公園,讓社區組織運營。2009年,高線公園和紐約人正式見面,成為城中熱門地標,但居民們并未走進去,吹捧它的是富人階層、游客和在周圍上班的人。2016年,高線兩側的房價比東邊兩個街區高出20%。
圍繞高線公園的爭議迄今仍在繼續,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完成“升級”的街區與城市。有人喜愛那些經過雕琢的生活方式與新的商業機遇,也有人感慨原住民的流失,更有人憤懣,一種以城市更新“副產品”形態展現的社會不公在陸續涌現。
現代城市面臨著越來越復雜的綜合議題,越來越多組織、機構與個人開始在城市更新決策中擁有一席之地。有人看到了更多新的利益,也有人看到更多新的機會,城市更新的議題也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