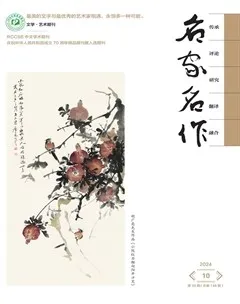淺析童年的“消逝”現(xiàn)象
[摘 要] “童年”作為一種社會結(jié)構和心理條件,不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一種信息環(huán)境改變的結(jié)果。進入21世紀,高速發(fā)展的網(wǎng)絡時代已來臨,立足于重新審視這一思想所內(nèi)含的文化精神在新時代的意義和價值,回顧過去:通過回溯電影相關的兒童群體進行總結(jié);面對未來:分析新媒介技術環(huán)境下童年“消逝”揭示的問題及其表征與原因。
[關 鍵 詞] 兒童電影;兒童本位;“童年消逝”;技術時代;童年存在
一、“兒童本位”的缺失
“兒童本位論”指以兒童為中心,將兒童本能的生理、心理行為作為創(chuàng)作的動機,最初起源于文學概念。自人類誕生起,兒童便已經(jīng)存在。但直到12世紀,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中仍未涉及兒童形象。希臘,以獨特的希臘油畫藝術首次展示了兒童形象,但兒童的存在仍被看作為一個轉(zhuǎn)瞬即逝的過渡階段。隨著希臘畫其他題材的消失,羅馬又回到了不展示兒童形象、不出現(xiàn)兒童特征的階段,兒童在圖像上也消失了。
反觀影視藝術,在執(zhí)掌影視與影視文學的成人世界中,兒童同樣被忽視。影視藝術中的“兒童本位論”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階段。1949年以前的兒童影片經(jīng)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從單純娛樂到認知教化的發(fā)展階段。在兒童影片的萌芽時期,無意識的影片創(chuàng)作使兒童形象走入影片,兒童電影以“非兒童本位”的體式出現(xiàn)在大眾的視域中。影片將“兒童”作為獨有的形象工具,利用自身的脆弱性,使影片帶有濃厚的教育色彩。通過兒童的行為展現(xiàn)成人的想法和成人的世界,表現(xiàn)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和給國人帶來創(chuàng)傷記憶的革命浪潮。五四運動作為兒童教育改良成熟的標志,身為文化先驅(qū)的作家便轉(zhuǎn)向關注兒童文學,提倡本位論,對發(fā)展兒童文學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他們的出發(fā)點仍是社會關懷,從關懷社會、關懷人的角度去關懷兒童問題、兒童文學,從站在社會成人的角度關心兒童及兒童文學。于1925年和1926年分別拍攝的影片《小朋友》和《小情人》通過對兒童形象的塑造,映射出成人化世界中所存在的社會問題,態(tài)度鮮明地反對封建腐朽道德文化的沉渣。選用兒童形象對故事情節(jié)進行渲染,站在社會成人的視角批判成人世界中的遺產(chǎn)制度以及對再婚婦女的歧視問題。
1931年,蔡元培做了題為《電影與教育》的演講后,郭有守依據(jù)《電影檢查法》領導組建的電影檢查委員會以保護中國兒童身心健康的名義,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禁演有害兒童身心健康的進口與國產(chǎn)電影,共計禁演影片17部。這是電影史上首次轉(zhuǎn)向注重電影對兒童身心健康產(chǎn)生的影響。1932年,中國兒童電影思想體系日漸成熟,標志著“兒童本位”與電影藝術的融合。郭有守以恩師蔡元培為旗幟,和陳瀚笙聯(lián)手,聯(lián)絡蔡元培門生故舊、官員、大學校長、著名影人共計90人聯(lián)名發(fā)起并在南京成立“中國教育電影協(xié)會”。蔡元培擔任主席,他在成立大會上的《開會詞》強調(diào)了電影與兒童的關系;強調(diào)了電影“對于教育實屬有莫大的影響”;強調(diào)了電影里的動作對兒童的影響最大;強調(diào)了“壞的影片,如淫戮之類,宜禁止放映”。影片《小女伶》作為“中國教育兒童電影協(xié)會”成立后放映的第一部有聲兒童影片,以小琳的兒童視角完成敘事。影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小琳有著如浮萍般漂泊的童年,自幼被迫賣到戲班學戲,最終學成歸來,實現(xiàn)了與家人的團聚。
人們從成人化、意識形態(tài)化的立場中走出來,走入以兒童為立場、以童趣美學為指向的影像敘事。在文學藝術作品中,19世紀初“配合一切革命斗爭”的兒童觀,到20世紀初以“五四運動”為標志所孕育的“以兒童為本”的兒童觀,再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幼者本位,尊重兒童個性為人性基礎”的兒童觀,“兒童本位”的缺失不斷走向新的“重塑”,在不斷重拾自我的道路上長足發(fā)展。直至今日,對兒童電影的本質(zhì)意義和本質(zhì)問題,學界仍眾說紛紜。如何將意味深遠與童趣童真交織糅合,如何實現(xiàn)成人之所感與兒童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的契合性發(fā)展,成為激發(fā)兒童電影的潛力、迸發(fā)兒童影視藝術活力的制勝關鍵。
二、新媒介技術下“童年”概念的相關思考
美國媒介研究學者馬克·波斯特提出“用媒介形態(tài)表征社會形態(tài)”。“第一媒介時代”指單向播放式的大眾傳播時代,即傳統(tǒng)媒體時期。“第二媒介時代”是互動的分眾傳播時代,其本質(zhì)特征是雙向溝通和去中心化。[1]
(一)媒介變遷與“童年的消逝”
關于“童年”的研究,從20世紀后半葉開始受到學界重視。波茲曼對童年概念逐步消解這一事實,態(tài)度是消極悲觀的。中世紀時期,被稱為“沒有兒童的時代”。16世紀,隨著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問世,童年的概念誕生,隨之產(chǎn)生“新成人”的概念,首次區(qū)分了兒童與成人。印刷術創(chuàng)造了一個全新的符號世界,將文字和閱讀作為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兒童需要長期的學習后才能有獲取知識的能力,其和成人之間的界限愈加清晰。兒童概念被普遍認可和接受,成為社會準則和社會事實。印刷術問世后的50年間,被稱為“童年的搖籃期”。童年概念自這一時期開始有具象化的表現(xiàn),波茲曼將這一時期的童年定義為“嬰兒期在掌握語言技能后結(jié)束,童年期從學習閱讀開始”。自1850—1950年,“童年”作為一個社會概念進入發(fā)展高峰階段后,繼而開始瓦解消失。當電視成為人們閑暇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時,兒童得知了本屬于成人世界里稱之為“秘密”的信息。童年概念自發(fā)明到進入含義豐富、具象化的頂峰階段再到被瓦解,波茲曼高呼:“童年正在消逝。”媒介產(chǎn)生于人類的需求。[2]在媒介的發(fā)展與變遷中,以社會媒介學的視角觀察這一歷史演變脈絡,可分為口語傳播時期、文字傳播時期、印刷傳播時期、電子傳播時期。
口語傳播時期是人類傳播活動的第一個發(fā)展階段。中世紀仍是一個以口語溝通為主要信息傳播方式的媒介社會,人際交往和群體交往也建立在口頭傳播的基礎上。[3]文字的學習和使用成本高,文字和書寫文化僅局限于上層社會。兒童和成人之間獲得信息的方式毫無差別,通過同一個認知渠道獲取信息,分享相同的文化世界。成人沒有“秘密”可言,兒童也沒有從“兒童視角”來認識世界。因此,沒有“兒童”的概念,成人和兒童之間也沒有分類。
文字傳播時期是人類傳播活動的第二個發(fā)展階段。口語和文字在媒介發(fā)展與變遷中是歷史最悠久的兩種媒介傳播方式。進入文字傳播時代,本應通過口語表達的信息,需要“編碼”成文字后經(jīng)過“解碼”的過程傳達給成人。此時,兒童需要經(jīng)過長期大量的學習,才能擁有這種“讀碼”“解碼”的能力,兒童與成人世界之間的信息也不再共享。文字的出現(xiàn)使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之間有了區(qū)分,“兒童”的概念因此誕生。
印刷傳播時代標志著文字閱讀成為主導性的媒介,它的出現(xiàn)象征著中世紀以口語文化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時代結(jié)束,以文字閱讀為主的信息傳播時代由此開啟。自古登堡發(fā)明印刷術以后,在歐洲便普遍運用。印刷媒介推動的文明進程使人們越來越重視羞恥感。成人將自己的“秘密”隱藏起來,用特定的符號來教化兒童,使他們成長在良好的道德環(huán)境中。[4]在社會化閱讀實踐中,閱讀成為一種群體的協(xié)作式的知識建構活動,讀者的互動因此可以突破時空限制[5],更進一步強化了童年與成人之間的分割線。
在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傳播時代,電視文化代替以往的媒介傳播方式引導著整個社會向娛樂化方向前進。“童年”作為在媒介變遷的社會中逐漸顯現(xiàn)的概念,自電子媒介時代開始,概念逐漸消逝。在電視誕生之前,電報的廣泛運用和圖像革命的開啟,已預示性地表明“童年”概念趨于消逝的發(fā)展路線。電報的出現(xiàn)使信息變得無法控制[6],圖像代替文字的媒介傳播方式逐漸興起,自文字時代伊始抽象的語言文字逐漸過渡為漫畫、圖畫廣告的形式。電視的出現(xiàn)代表著影像革命的開始,社會傳播結(jié)構發(fā)生巨變,視覺圖像成為敘述和訴諸情感的主要方式。
當學術界的關注點放在即將面臨消亡和轉(zhuǎn)型的理論對象上時,它所激起的強烈反響是可以預見的。如今,“電子媒介”以多樣的形態(tài)充斥著時間和空間,并形成飽和的媒體環(huán)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兒童群體接觸媒體的年齡和使用的狀態(tài),重新塑造了新一代兒童群體的童年形態(tài)。技術的發(fā)展是單向度前進的,兒童群體過早地社會化、成人化似乎已成為無法避免的事實。現(xiàn)如今的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特征,社會形態(tài)也日漸媒介化。因此,造成當今社會中“童年消逝”現(xiàn)象的原因有兩類:一類是媒介原因;一類是社會原因。
首先,造成“童年消逝”現(xiàn)象的媒介原因主要是由于信息傳播媒介的多樣化。波茲曼對技術演進帶來的媒介環(huán)境的更迭對童年所產(chǎn)生的影響,態(tài)度是消極的。種類過于繁多的信息傳播媒介,大量地擠占了兒童的文化空間。約書亞·梅羅維茨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認為:“電子媒介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媒介本質(zhì)的功能是通過改變物質(zhì)社會的‘地理場景’來對他們產(chǎn)生影響。”[7]兒童群體在網(wǎng)絡時代中被手機、iPad這些智能電子產(chǎn)品所構成的媒介環(huán)境所裹挾。面對豐富的程序和信息,他們用手指輕觸屏幕便可使自己處于任何一個地理場景中,進入信息世界獲取任何信息。在新媒介的籠罩下,兒童與成人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兒童接觸網(wǎng)絡愈加“低齡化”的今天,他們可以模糊地感知成人世界的情緒,把自己置身于成人世界的境遇中,過早地接觸成年人世界中的信息。波茲曼在書中提道:“當兒童有機會接觸到從前秘藏在成人信息的果實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被逐出兒童這個樂園了。”[8]其次,是社會原因造成的“童年消逝”現(xiàn)象。其一,將孩子送去學校讀書,是每個人必須遵守的責任也是必須履行的義務。但家長普遍過于焦慮的情緒,使兒童在成長階段承受著過多的學業(yè)壓力,他們的童年失去了無憂無慮的本質(zhì)。而學校制度雖然為學生的學習成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兒童本應外化為行動的心理狀態(tài)和想法。其二,一方面兒童在成長階段會吸收外界環(huán)境的行為并轉(zhuǎn)化為自己個性的一部分。在成人環(huán)境下,成人的言語和行為會被兒童無意識地“吸收”,導致兒童自身的腦力發(fā)育與心理發(fā)育不同步,原有的語言學習習慣被打破,加速了童年消逝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社會對兒童群體的評價和對成人的評價趨于一致,忽視了兒童的特殊性。用成人化的標準評判兒童優(yōu)秀與否,兒童被過早地要求進入到成年人的世界,這進一步加速了童年消逝的現(xiàn)象。
(二)技術時代下“童年”命運的爭論
童年概念的產(chǎn)生、發(fā)展及消逝是隨著人類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遷而不斷發(fā)生變化的,“童年”在消逝的同時也是概念重構的過程。隨著技術時代的到來,技術輻射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所影響的群體應包括社會整體。但因兒童群體自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和“可塑性”,因此備受關注。傳統(tǒng)媒體時代通過直接經(jīng)驗的傳達獲取知識和信息。相比于傳統(tǒng)媒體時代,技術時代下的兒童群體所處的媒介環(huán)境有集成性、交互性、實時性的特點。在數(shù)字媒介的環(huán)境下,兒童在大量碎片化、多元化的信息中不斷切換。兒童成長的客觀環(huán)境也遠遠超出其個人的直接經(jīng)驗范圍。因此,我們無法用一個固定的概念去闡釋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童年。在新的媒介環(huán)境中,環(huán)境發(fā)生著改變,在環(huán)境中衍生出的童年概念的形態(tài)也將有所改變。
童年不會消逝,而是伴隨著新事物的產(chǎn)生以另一種別樣的形態(tài)存在。在如今數(shù)字化時代下,它的意義在于以一種客觀的視角重新看待技術與童年之間的關系,思考技術帶來的反思與批判。
三、結(jié)束語
無論是從童年存在對個人成長的必要性還是情感價 值取向的角度思考,童年的存在都是必須的。不可否認,每一時期的兒童概念和兒童理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局限性;但從兒童出發(fā),尊重兒童、發(fā)現(xiàn)兒童、凸顯兒童本位意識儼然成為共識。雖然,童年的概念隨著技術的發(fā)展不斷展現(xiàn)出新的形態(tài),成人視角與兒童視角如何達成和解,童年概念不僅不會隨著印刷時代的離去而消逝,相反,它將伴隨著技術時代的發(fā)展衍生出新的形態(tài),在成人世界中找到新的定位,生成新的童年,迸發(fā)出新的審美形態(tài)和創(chuàng)作范式。
參考文獻:
[1]陳奕,鐘瑛.新媒介素養(yǎng)研究的變遷、熱點和趨勢[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44(5):161-168.
[2]溫志宏.媒介變遷及其中的新世界[J].中國圖書評論,2022(6):55-62.
[3]李特約翰.人類傳播理論[M].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4]石建偉,曹倩.童年消逝:一場成人的自我哀嘆[J].少年兒童研究,2021(11):65-72.
[5]李武,謝澤杭.社會化閱讀的概念生成、發(fā)展演變及實踐影響[J]. 現(xiàn)代出版,2022(5):60-67.
[6][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艷,吳燕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29.
[7][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8][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M].吳燕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