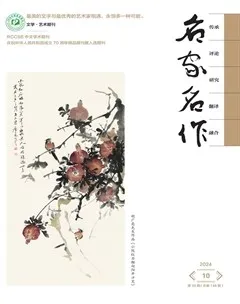唯象學指導下距離感審美對中國古代科學的影響
[摘 要] “李約瑟問題”自提出以來就受到各界學者的廣泛熱議,引起了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激烈討論。在承認該問題合理性的前提下,嘗試從美學視角切入尋找問題答案。表面上看,中國古代審美的“距離感”特性導致深度認知的缺乏,然而,這種植根民族性格的審美偏好實際上受到了“象思維”的極大影響。“象”學的整體性、關聯性使得中國古人生活在一幅“循環論”而非“因果論”的、“天人合一”而非“主客二分”的、展現出“象—意境—意”的變動敞開過程的世界圖景中。這種 “審美化”的形而上學假設和認識論與西方近代科學及其現代性邏輯客觀上有距離,是“李約瑟問題”回答的一個可能。不過,我們依然不可忽視這種“象思維”的重要地位,尤其應在現代哲學與美學背景下重新發掘人的感性經驗,在現代科學史的視角下以“博物學”的框架重新編寫中國古代科學體系。
[關 鍵 詞] 唯象學;李約瑟問題;博物學;象思維;認識論審美化
一、“李約瑟問題”與美學解釋的可能性
“李約瑟問題”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專家李約瑟博士在該領域提出的中心問題,也是關涉中國古代科學、西方近代科學革命乃至整個科學史書寫的重大課題。之后的近百年間,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此進行了異彩紛呈的解釋,也在提倡文化多樣性、科學普適性的今天煥發出新的生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
根據董英哲、吳國源、王揚宗、劉鈍等學者對學界公認的“李約瑟問題”的轉述,我們對該難題采用如下規范性表達: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后16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獲取自然知識并將其應用到人的實際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為什么近現代科學(以自然的數學化為顯著特征)只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等)文明中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并非只有在大眾中廣泛流傳的后半部分,而是基于前一問題的背景下,由于前后發展狀況的顯著差異而自然引起的追問。這從某種程度上反駁了“無意義說”,后者認為追問沒有發生的事情(逆事實陳述)是荒謬的,倘若我們能夠看到這一難題的兩個部分,也就不可能割斷兩者之間的天然聯系,而可以發現該難題的合理性和研究價值。
2000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舉行了“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問題座談會”,該問題事實上是“李約瑟問題”相關性極高的延伸討論。正反雙方的辯論基本上概括了學界解決該難題的思考角度,其中,吳國盛教授指出了雙方論證的焦點和核心分歧所在。當正反雙方都認同“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這一問題取決于“科學”的定義,定義“寬則有窄則沒有”時,爭論焦點事實上在于我們定義寬窄的依據和意圖是什么。因此,該難題實質上是“中心與邊緣話語權之爭”,從“科學”的三個定義(現代性與非現代性、收斂性科學與發散性科學、數理傳統的科學與博物學傳統的科學)來看,中國始終處于邊緣,因此按照三個前者來定義“科學”則得出“無科學”,按照三個后者來定義“科學”則得出“有科學”。因此,“李約瑟問題”的解決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承認問題合理性—比照有無雙方的各項指標—確定原因”的過程,而是涉及話語權爭端、科學中心論/進步論與普適性、文化多樣性、歷史觀的辯證法、思維模式、邏輯語義、認知圖式與概念框架、家國情感等多方面因素的復雜問題,因而面臨被消解成為“偽問題”的風險。
本文為探討該現象出現的原因而預設問題合理性,嘗試從美學的角度探討“李約瑟問題”,在比較語境下尋找中西文化中客觀的差異,從審美的距離感入手,引入基本的意象思維及“象”學概念探討這種距離感審美產生的根源,采用吳國盛教授對中國古代科學“天、地、農、醫”的分類,用美學地理觀重建“地”學一脈,用美學的天地經驗統一世界途徑和價值系統,論證注重廣度的博物學、注重“象”的唯象學給中國古代帶來的科學后果。
首先需要指明,我們尋求的美學解釋只涉及人對物(主要聚焦自然美)的觀察與鑒賞,人文化成的藝術創作之美與“李約瑟問題”并無直接關聯,游離于我們的討論范圍之外。想通過藝術創作領域的距離感審美推出“中國古代無科學”是強詞奪理、只關注表面聯系而未抓住事物本質的荒謬做法。具體而言,第一,藝術美與自然美有時不可混用。例如,針對“移情”概念,費肖爾、立普斯更側重對事物的觀照和自我情感的移注與投射,沃林格則明確指出在《抽象與移情》中自己探討的只是藝術美的領域,無涉自然美。第二,距離感在認知上的錯誤運用也并不代表其在藝術創作上需要被貶抑,相反,這是文藝作品令人沉浸、欣賞、享受的常見方式。例如,山西長治法興寺被稱為“宋塑菩薩之冠”“最美菩薩”的塑像,在正殿拐角處靜矗,其鳳眼低垂,目光正好落在轉殿禮佛的人身上,菩薩像創作與觀賞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場距離感轉變的象征與隱喻,這也與我們所要探討的遠距離審美有所差別。
二、距離感審美綜述
宗白華在《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往哪里去》一文中引用了泰戈爾的論斷,精準點出了中國文化“距離感審美”的特性:“世界上還有什么事情比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更值得寶貴的?中國文化使人民喜愛現實世界,愛護備至,卻又不致陷于現實得不近情理!他們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學權力的秘密,而是表現方法的秘密。這是極其偉大的一種天賦。”古賢也早已總結出此道,即逼近褻玩會破壞事物的美感,只有遠望方可體察其情意:周敦頤所謂“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張大復所謂“蘭之味,非可逼而取也……令人覽之有余,而名之不可;即善繪者以意取似,莫能肖也”大抵如此。
朱光潛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無言之美》一篇中曾多次提到,對現實世界全然真切的言語描述會破壞其美感,使之索然無味。例如,“世間許多奧妙,要留著不說出;世間有許多理想,也應該留著不實現。因為實現以后,跟著‘我知道了’的快慰便是‘原來不過如是’的失望”,“無言之美何限?讓我這種拙手來寫照,已是糟粕枯朽”等。這亦可視為宗白華言“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的另一種表達,結合通常所說的“得意忘象”的思維模式(將在后文詳述),我們可以明晰所謂的“距離感”并非只在物理意義上,而是一種與事物本然拉開距離的認知方式,是給事物以“開顯”生發自身的空間的認識、是覆蓋由展現出的“象”到代表著終極奧秘的“意”的全過程的觀察。而這種由“象”至“意”的轉變又并非審美的主體起主導作用,而要“退居其后”將其融入更遼闊的整體世界圖景中方可實現,這就是“無言”和“遠觀”的目的。
隨之而來有兩個疑問,首先,我們在前文已明確,從美學角度解決“李約瑟問題”需要明確區隔“認知”與“創作”兩個領域,藝術創作上的夸大、想象、留白等手段實在與“李約瑟問題”相距甚遠,那么此處我們再次引進藝術創作方面的理論不是前后矛盾了嗎?誠然,本篇中心意旨在創作領域美(或藝術美而非自然美)的研究,通過美術、文學、戲劇、音樂、雕塑等多種藝術形式中“流露”與“含蓄”的差異歸納出“無言之美”更能引起美感的觀點。且說“美術是幫助我們超脫現實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亦在明確其論域只在美術意志在“理想界”的一面。但朱光潛并非就美術言美術,而是闡發了中華文化中基本思維方式習慣于“無言”的特性:“本文論無言之美,只就美術一方面著眼。其實這個道理在倫理、哲學、教育、宗教及實際生活各方面都不難發現。”即使朱光潛先生不言明,我們也能夠發現在各具體創作(或廣義的實踐)領域追求“無言”所體現出的“距離感”的偏好。
其次,這種特性似乎并不是古代中國所獨有的,以朱光潛所提到的雕塑拉奧孔、啞劇布景等為例,我們得以窺見西方對于“無言”也甚為推崇,僅從經驗常識來談亦只怕是人類審美之共性。倘若實情如此,這一理論就無法解釋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也便不能成為“李約瑟問題”的一個合理解答。對此,我們仍然采用朱光潛在《談美書簡》中的提法。根據近代美學家的分類,作為審美主體的人有旁觀型和分享型,其中純粹旁觀型的人不易產生移情和內摹仿活動,在觀察中傾向于物我分離(亦即尼采所說“日神精神”);而純粹分享型的人容易產生移情,在觀照事物時達到物我兩忘的狀態(亦即尼采所說“酒神精神”)。筆者結合西方哲學傳統認為,這種人格的分異并非不同文化形態本質的分野,卻受主流文化的塑造和引導。古代西方并非天然缺乏分享型個體,只是一以貫之的形而上學傳統極大張揚了日神精神(旁觀者)并壓抑了酒神精神(分享者)。而談及“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傳統”一題,筆者贊同吳曉明教授的論斷,即西方哲學以“形而上學”(metaphysics)為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與對立,立足于此種“真”與“不真”的分別歸屬,并最終是由一切存在者的“第一因”最高存在者定向的。詞源法考察也證明了這一點,即把“metaphysics”拆成“meta”和“physics”兩部分,意為“超越物理學的”“超越感性世界”“與感性世界分離的”。這種“形而上學”的學術風格顯然具有高度的宏觀性、抽象性、博學性和思辨性,讓“迷狂沉醉”的原始酒神崇拜逐漸失去理論和信仰上的存在基礎,從而造就了西方世界整體上的“旁觀型性格”。而中華文化則是一個審美溢出的、“分享型性格”的典型代表,后文將詳細論述這種與事物本身拉開距離,而在概念圖式中帶有移情性質主觀建構的“唯象學”,這也正是筆者解答“李約瑟問題”的最終進路。
三、博物學與象思維
“距離感”表面上是一種“遠—近”二元對立的方向關系,然而不論是朱光潛先生提示的在各個領域均有體現的“無言”,還是“距離感”本身對其背后深層原因的暗示,都要求我們針對認知方式背后的哲學指導思想進行深入探討。倘若我們肯定這種天然的聯系,即往后一步是為了看到全面的景觀,不用言語描述注重感受神韻是為了看到背后的萬千繁復之相,那么就有理由認為指導著整個“距離感審美”的科學形態是在放棄“深度”的同時拉開了“廣度”的博物學,其思維模式則是“唯象學”(象思維)。
吳國盛教授認為對中國古代科學進行“李約瑟范式”化的分類是有失偏頗的、“輝格史”的做法,而針對“李約瑟問題”的引申——“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肯定回答,需要采用博物學的視角。博物學又稱“自然志”(natural history),注重對具體事物而非一般本質的探究,強調采集、命名、分類而非觀念演繹,著眼于唯象描述(著重“natural”部分)、作志著史(著重“history”部分)而非追究本原和理性知識。即在一個審美意味更濃重的認知過程中,終極追求是將新觀察到的事物和現象歸入浩如煙海的“百科全書”之中(博物學),并始終保持世界圖景的統一和諧和價值觀念的穩定連續(象思維),而非與現代科學相適應的高度系統化、形式化的理論知識。
具體而言,“天、地、農、醫”四部分都體現出鮮明的“描述而非推演”的特點。中國古代的“天”學“是天界博物學、星象解碼學、政治占星術、日常倫理學”,即“忠實地記錄天象”以期獲得指導日常生活的秘密;“地”學是在記載地表現象的基礎上賦予現象以構建世界圖景和價值系統的意義;“農”學“是關于栽培植物和馴養動物的博物學,也是農業生產技術的博物學”;“醫”學包括“觀物取象”“辨類比象”的分類學譜系和藥用博物志。
其中,“地”學部分則有著更加突出的審美性質,地理學、氣象水文、物候災害、動植物、礦產資源等內容都被包含在內。最早的博物學著作《詩經》雖被今人賦予哲學、思想教育等多重價值,卻從根本上屬于博物學的范疇;孔子有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正是《詩》所描寫和傳達的主要意旨。相比《詩經》雜陳天地萬物的書寫,被李約瑟稱為“考察著作”的《尚書·禹貢》分劃九州、五服,則更有“中心清晰、邊緣模糊”和“自我中心化”的天下意味。后世的《山海經》《水經注》《海內華夷圖》《元和郡縣圖志》等均展現了地學博物學的翔實記錄。劉成紀老師曾談到,由于現代的美學研究(主要有康德、尼采的界定)使美的論域大大擴展,并非局限于個體自由和藝術,而是相當于“人的世界經驗”這一層級的概念——既然知識只是人的感性經驗,那么世界的整體面貌就會天然的帶有“直覺、投射、想象和圖像”的審美屬性。這種“人的世界經驗”的審美屬性在“地”學的“祥瑞與災異”現象實錄中則體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古人嚴格遵循“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學預設,結合流年時運、農業收成、國祚興衰等多重現實生活的要素,將地理現象分為“祥瑞之兆”和“災異之兆”。
博物學體現了古人對于現象歸納匯總的強烈興趣和一以貫之的“史志”傳統,為今人展現了一幅豐富多彩的世界圖像。那么,這種看似自覺的整體性考察方法、看似本然如此的聯系觀究竟從何而來,后者——作為來源的哲學預設和思維模式又如何影響了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呢?要解決這個疑惑,需要追溯至“象思維”的發生。
總體而言,“象思維”源于《易》的形而上學假設,注重描述事物本身而不強調概念框架和邏輯推演,是“一種既關涉真理又與其相游離的構成性框架”,而非“可供思想者共同執守的實體性真理”。
根據上述對博物學的分析,我們明確了古人“觀象”的目的并非審美,而是對世界的追究和探問。然而,即便如此,其詩性、感性的表現形式和達取真知有效性的缺失卻是客觀存在的,筆者認為這也正是“李約瑟問題”的一個解答。結合劉成紀老師的三層分析,我們可以直觀地呈現出象思維與現代科學發軔因素的距離。
象思維在中國哲學中擁有原發和主干地位,其本意雖不在審美,但其奠基畢竟在美學這種感性學,而西方現代科學需要的是極度理性和冷靜的推演。
象思維以關聯性思維為展開形態,以景觀呈現為表達方式。誠如李約瑟本人所言,“概念與概念之間并不相互隸屬或包含,它們只在一個‘圖樣’中平等并置;至于事物之間相互影響,亦非由于機械的因之作用,而是由于一種‘感應’”,“在中國思想里的關鍵字是‘秩序’和‘圖樣’。符號間之關聯或對應都是一個大‘圖樣’中的一部分。萬物之活動皆以特殊的方式進行,它們不必是因為此前的行為如何,或由于他物之影響;而是由于其在循環不已之宇宙中的地位,被賦予某種內在的性質,使它們的行為身不由己”。
誠然,我們并不能說中國古代沒有“因果”的觀念,相反,這種“周行不已”的“因果”在農學、醫學各種領域都有顯現。例如,中醫的“望聞問切”就是一種查病因、尋病根的追本溯源的思維方式體現。然而,仍以中醫為例,其診斷并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暫且不論這當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庸法)的“對癥下藥”,而是從身體作為一個各器官與精血聯結的循環系統、一個與天地聯結的“天人合一”系統的視角進行診治,因此,這種“因果”是包含在宇宙“循環”中的“因果”,中國古人認為沒有脫離了世界整體圖樣的單一的機械論的“因果”,后者恰恰是西方現代科學所需要的“因果論”的思維方式。在易學象思維指導下的“循環”中,萬物普遍聯結相互制約,以一種抽象的“感應”作用構成有機世界,沒有明確的、單獨成組的推動力和受動者,而是因為處于世界的某個位置而發生行為,亦即所謂“以象表示天地萬物所處的空間方位及其運動變化的時間過程,顯示世界聯結為一個整體”的“整體思維”。
象思維并非我們靠字面意思理解到的“唯象學”,即只關注現象而不發掘背后深意,而是本身也以叩問天地萬物奧秘為目的的。然而目的如此,實現手段和效果卻走向了極化的審美,這也是中國古人的探尋不能真正發現世界的真相,“更多是在外部的撫摸或旁敲側擊”的重要原因。
象思維主導的認知過程大致呈現為“象—意境—意”的層層深入。首先,“象”是認知的起點,《易傳》提到包犧氏“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創造了“八卦”——看似有歸納抽象的過程、而在事實上仍屬于形象層面的圖式。這就是通常所謂“觀物取象”的過程。其次,將自然界個別事物的“象”相互關聯,直至再現一個情境式的圖式;而這其中必然包含主體對于自然界事物關聯的主觀理解,盡管這并非人們刻意為之,但認知活動本身就離不開主體的加工,這一作用在古人身上體現得則更明顯。李約瑟對于“五行”學說的分析指出:“符號性關聯越精密幻構,則它整個的系統距離對自然的科學觀察也就越遠了。”即一種相互關聯的“意境”式的認知,只能在模糊與精確之間徘徊不定,既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具體特定的現象而模糊(參見“距離感審美”),又因為并未引入系統化、理論化的抽象概念而難以走向具體事物上之后,亦即表現出“在整體上僅止于意義撫摸、猜測或想象的癥候”。再次,自然的‘人化’走向關鍵性一步“得意忘象”,劉成紀老師稱“意”為“混合著天命、真相等諸多本質主義性質的象的內在性”,在《易》中“象”的體現即卦象,而“意”的體現即《易傳》的卦辭爻辭。不論今人如何認為這一過程是異想天開、主觀臆斷、感情投射、只抓住表面聯系而并未進入深層次的認知,在古人的眼中這都是發現世界真意的偉大嘗試,是極具感性審美效果的認知活動,即“以象來表達事實、真實,獲取真意,從而把握事物的本質,此時,‘象’的存在意義被轉移到‘意’上,就可以舍棄‘象’而只取‘意’了,即所謂的‘得意而忘象’”。
此外,針對象思維我們還有一些需要澄清的誤區。象思維是“以直覺與體悟為特征的‘象思’或‘原思維’,乃‘從象出發,在象的流動與轉化中,并最終通過超越象,以達到思維的目的’”,根源于“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學假設;也因此其雖明顯有別于“概念思維”,卻亦并非單薄的“形象思維”。根據朱光潛的定義,“形象思維”是把從原始的感性認識(包括感覺、映象、觀念或表象)所得來的各種映象加以整理和安排來達到一定的目的。別林斯基和費肖爾開始采用“形象思維”來解釋“想象”(imagination),這也開啟了現代哲學中將“形象”指為“對象的心靈映象”的傳統,主觀色彩濃重。然而經過前文的討論,我們發現中國傳統的“象”事實上并無過分的情感投射,根本上仍然是“對象事物本身外顯的形式”,只不過古人進行了更精煉化的形象加工而已。強調這一點意在肯定其在博物學資料數據忠實收集、宇宙觀與世界觀獨特建構的重大貢獻,只是在尋求“李約瑟問題”的解答時,我們仍然需要客觀分析其與現代科學邏輯的差別。這并非站在科學中心論立場上貶損象思維,如某些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科學“前形式”“前運算”“前理性”“前思維”的論斷;而應當從差異而非歧視的角度指出中西科學的體系化不同,如林可濟老師提道:“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先后順序,不像西方科學那樣先從研究最簡單的機械運動形式開始,然后再遵循簡單到復雜的原則與順序,再到物理、化學、生物等運動形式;而是一開始就可以在研究復雜的生命運動形式的農學、醫學中取得卓然的成就。”
四、對于“李約瑟問題”特色他解的反駁及結語
(一)對馮友蘭內求說的反駁
馮友蘭先生在1921年發表過一篇名為《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的論文。他對該文中心意旨進行了簡要概括:“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自然科學,是因為中國的哲學向來認為,人應該求幸福于內心,不應該向外界尋求幸福。近代科學的作用不外兩種,一種求認識自然界的知識,另一種是求統治自然界的權力。西方近代哲學的一個創始人笛卡爾說:‘知識是確切’;另一位創始人培根說:‘知識是權力’。這兩句話說的就是這兩種作用。如果有人僅只是求幸福于內心,也就用不著控制自然界的權力,也用不著認識自然界的確切知識。”
筆者認為可能的反駁主要有兩條進路。第一,此處的“內心”難以成為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內心”,且除“陽明心學”一派“發明本心”認為世間道理不假外求之外,其余理論框架并未將內心與世界做關涉緊要的區隔,又何以認為中國哲學不尋求自然界的確切知識和權力呢?第二,假使我們認可“求幸福于內心”的觀點,認為中國哲學教導人們將自然界探索得一清二楚并非必要,也難以從中推出缺乏近代自然科學的結果。畢竟,于內心追求幸福與向外界追求真理并不截然對立。
如前所述,中國哲學并非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也并非沒有向自然界尋求真相的嘗試;與之相反,中國古人包蘊萬象的博物學已經足以說明其在此領域的一切決心與成就。導致“中國古代無科學”的是“認知的審美化”,在認知目的上中西并無本質差異。
(二)對魯品越實用文化說的反駁
魯品越教授結合哲學與經濟方法,認為中國古代的“生存型實用文化”是沒有產生近代自然科學的緣由。為了應對黃河流域嚴峻多變的自然條件,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形態的中國在上古時期產生了以宗教幻想為主導的文化,通過巫術儀式祈求神靈降恩,但在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十分早熟地轉向了實踐理性,而高度世俗化的宗教成為中國主導型價值,產生了“生存型實用文化”。而這種文化具有“淺層次性”,即“當社會的全部智力資源都僅僅關注具有眼前實用價值的知識,將使人們對于客觀規律的利用停留在淺表層次,不能發現縱深層次規律——因為對深層次客觀規律的抽象探究超出當時實踐需要,沒有直接的應用價值”。因為注重生存與實用,所以沒有對遠離實際需要的好奇心,因而也缺乏了對深層規律研究的動力源泉,最終沒有產生以關懷精神世界宗教活動為原動力的自然科學探索。
筆者認同尋求生產力解釋的科學方法,但仍然認為中國古代缺乏自然科學的縱深進展不完全是因為沒有實用需要,而是像思維主導下的審美溢出對于認知的影響;不是早已遠離了宗教幻想、完全受實踐理性主導,而應該看到尤其在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浪漫的文藝作品與世俗生活結合并深刻影響了日常實踐與科學探索。
我們停留在現象世界的描述中不愿打破這種美好的朦朧感,這是詩一般的傳統呀!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哪里是一種全然追求實用的文化形態能夠表現的呢?不同歷史時期中國人想象未知、發揚浪漫、追求遠方的藝術體現各有差異,但總體來說“象思維”主干發展出的道家支脈集中體現了浪漫主義傳統。李澤厚有言,道家比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別更抓住了藝術與審美的基本特征,即“形象大于思想;想象大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盡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莊子泛神論的哲學思想與對待世界的審美態度完美結合,將“象思維”引向了無限的超驗領域,使之真正具備了形而上學的特色。這種“原始思維”色彩的遺留將中國古人的思維方式由“整體表象”上升躍進為“整體思維”,主導著中國古代的科學世界,這也恰是美學對“李約瑟問題”作出的回答。
參考文獻:
[1]潘吉星.李約瑟文集[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2]劉鈍,王揚宗.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3]威廉·沃林格.抽象與移情[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
[4]朱光潛.談美書簡:給青年的十二封信[M].北京:中華書局,2018.
[5]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6]馮友蘭.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宗白華.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往哪里去[J].唯實(現代管理),2015(12):22,36.
[8]吳曉明.再論中西哲學之根本差別[J].中國社會科學,2023(5):57-86,205-206.
[9]吳國盛.博物學:傳統中國的科學[J].學術月刊,2016,48(4):11-19.
[10]劉成紀.中國早期哲學的象思維及闡釋學、美學引申:兼論闡釋對象的確定性等問題[J].學術研究,2021(11):12-28,177.
[11]賈向桐.意象思維與中國古代“科學”:兼論楊振寧對“李約瑟問題”的解答[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4(5):18-24.
[12]劉成紀.論中國美學的天下體系[J].探索與爭鳴,2018(8):109-117,144.
[13]魯品越.生存型實用文化與李約瑟問題[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4(1):73-80.
[14]田松.科學話語權的爭奪及策略[J].讀書,2001(9):31-39.
[15]林可濟.重新審視“李約瑟問題”:從中西文化哲學差異的視角[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29(11):91-96.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哲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