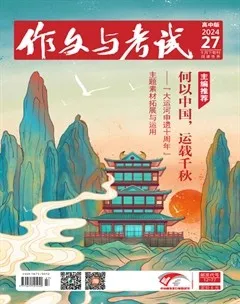古巷深處
在那條被時光輕柔撫摸的古巷深處,彌漫著一種難以言喻的迷離幽香,它似檀木的沉穩,又摻雜著桃酒的甘甜,于細雨之后,更顯醇厚。白石階上,水珠輕舞,映照著門前大紅燈籠的暖光,光影交錯間,仿佛能窺見往昔的溫柔與繁華。
杏花微雨,細細密密地織在油紙傘上,又悄然滑落,輕拂過行人的衣袖,留下一抹淡淡的墨綠,宛如不經意間繪就的青蓮,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泛起層層漣漪,觸動著心底最柔軟的部分。這一切,都像是古巷低語,訴說著千年的故事,讓人沉醉,不愿醒來。
閉上眼,耳邊似乎響起了悠遠的琴音與笙歌,它們穿透了細雨的簾幕,交織成一首古老而又神秘的歌謠。那聲音,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如同舊唱片在老式播放機中緩緩轉動,帶著歲月的痕跡,讓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那份懷舊與浪漫之中。
說起來,這巷子里還有家小酒樓。外邊看著不大,里邊倒五臟俱全。每次有人路過,店前招客的伙計立刻叫住那人:“老板,進來喝幾盅?今兒有新書嘞!”只要客人點頭,他便熱情地拉住客人的手,掀開門簾便是一聲響亮的吆喝:“賓客一人,安排個6號座。六六大順!”緊接著又是一位小伙,肩上搭著白手巾,卷起袖子,露著樸實的笑容將客官引入座。他一手扯下肩上的白手巾,一邊干凈利落地抹著木桌,一邊對客人笑道:“您今兒可真是趕上時候,正巧咱這新來了個說書先生。哎呦那書說的,能把這書里頭的事兒講得跟演在這臺上、瞅在您眼里一般!”
酒樓的說書先生姓林,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小伙,身著素色大褂,腳踏老布鞋,有時也會手持一把折扇,單手彈開,緩緩搖動,吹得額前幾點碎發輕揚,頗有點驕傲的味兒。一張口,就像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京中有善口技者”,大火燎原,海浪翻騰,萬馬策奔,刀槍亂鳴,能將書里的場景像是播連續劇般呈現在人們眼前,實是令人心生佩服。
若還有閑工夫,便去盡頭那棵長得最高的杏樹下坐坐,陪陪那座矮小的石墓吧。巷里的人都知道,那里埋的是一只狗的魂魄。
他們說,狗叫杏核,是一條小土狗,從別處流浪來的。
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巷里人第一次見它時,它正難受地嗚嗚哭咽。路過的人看了看才知道,有個杏核卡在狗的喉嚨里。那人把杏核從它口中摳出來,后又給了它點兒泡湯饅頭。本以為它待幾天就會走,沒想到它這一待,就是兩年。巷里的人都稀罕它的聰明伶俐,就一起養著它。因它曾被杏核卡喉,便取了個名,叫作“杏核”。
兩年后的一天夜里,杏核突然又叫又跳,聲音在靜寂的夜里聽來異常刺耳。巷里人被吵醒,剛惱火著拉開門,還沒瞅著杏核,便聽見巷子里響起一聲急里透焦的哭喊:“來人啊,我家書意被偷了!”原來是一家娃兒被偷了。街坊們聽了,再也顧不得什么,隨手抄起石頭木棍,便一股腦兒沖向巷子口。
前方,孩子的嚎哭聲里摻雜著狗的嗷叫與嗚咽。人們趕到一看,卻是杏核死咬著賊的腿。那賊疼得眉毛都擰一塊去了,對著杏核的頭又踹又踩。杏核大概糾纏那賊有一會兒了,身上有好幾處傷口,血粘住的毛發無力地垂在半邊瞎眼上。
那夜,眾人合力救下了被拐的孩子。孩子被安全送回,杏核卻沒活成。這塊碑,便是孩子父母為杏核立的。這地正巧有棵杏樹,足以為這小魂靈遮風擋雨了。
那個被杏核救下的孩子,叫林書意。現在已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愛說書,穿素大褂,老布鞋,有時手持一把折扇。
某一天,杏花碎瓣伴著微雨飄落在油紙傘上,沿著邊緣,忽地墜下,“啪”地一聲清脆,打濕撐傘人的純青衣袖,墨綠沒有在上面暈成蓮花,倒頗為驚奇地染成一棵杏樹之形。傘下,說書人立在小小的墓碑旁,平日里口若懸河的他,此刻卻道不出一字。
過了一會兒,他摸出塊手帕,蹲下身,擦了擦小小的墓碑。傘的上方,碎花飄搖,落在墓碑上。
細雨斜墟落,古巷有真情。
(指導教師:馬善德
編輯:關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