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鬼的被鬼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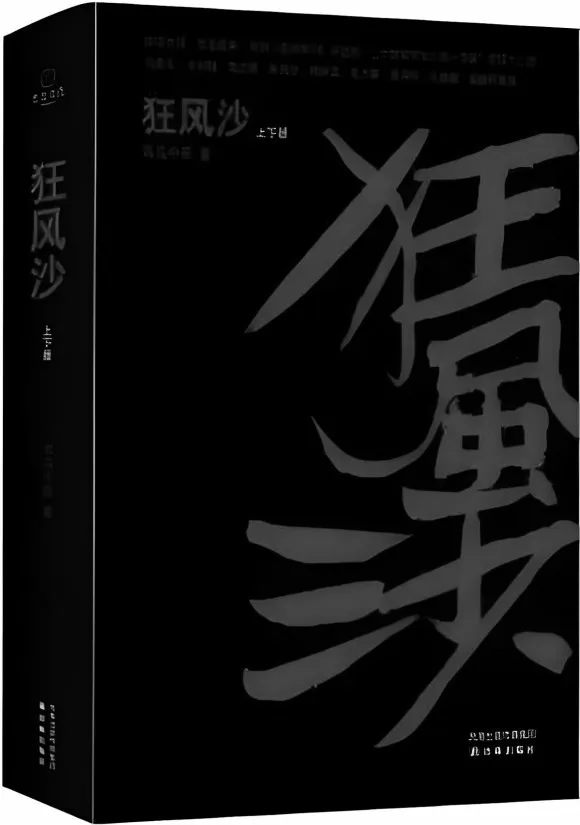
已故中國臺灣著名作家司馬中原最有名的作品是《狂風沙》,這部以民初北伐為背景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奠定了司馬中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我偏愛他的鄉野傳說系列,這是20世紀60年代在《皇冠》雜志發表的小說。這個系列的第一篇是《火葬》,寫一個可疑的尸變故事。在小說結束前,作者一一指出尸變事件中看似詭異但其實有跡可循的細節,并對讀者說:“你們愛聽中國北方鄉野上的傳說嗎?我當然可以把那些小說娓娓地告訴你們,不過,同時也要告訴你們,那些古老的傳說,多半都是這么來的。”就這樣,司馬中原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凄慘、恐怖、鄉土迷信色彩極為濃烈的精彩故事”,迷倒了好幾個世代的讀者。
鄉野傳說系列長短不一,有一期就登完的短篇,有分兩三期連載的中篇,還有一個長篇。此外,根據《皇冠》的新書廣告,還有好幾篇沒在《皇冠》刊出,直接結集出了單行本。創作如此豐富,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司馬創作生涯的巔峰。
鄉野傳說告一段落后,《皇冠》改版,司馬仍繼續寫作這一類的狐鬼傳說,但改名為“秉燭夜談”。后來,“風云時代”出版社把司馬中原的小說重新整理出版,“鄉野”和“秉燭”兩個系列混雜不分(還有幾篇不屬于這兩個系列的)。如果以創作時間來排列區分,更可看出作者寫作風格的轉變。“鄉野”和“秉燭”題材相差不大,我還是比較喜歡20世紀60年代的鄉野系列,也許是個人喜好,也許是讀這些小說時的環境所影響。我讀這一批鄉野傳奇時,正是船民怒潮洶涌的日子,身邊發生的事、身邊的人講述的一個個荒誕不經、無可考證的故事,都和司馬筆下的鄉野傳說如此相似,只是場景從中國北方的遼闊大地換成了越南東海的茫茫汪洋。
兩位名家筆下如出一轍的詭異命案
鄉野系列的作品水平參差不齊,唯一的長篇《荒鄉異聞》平平無奇,只能算是加長版的《路客與刀客》。鄉間神棍驅狐作法的段落也和其他中短篇的描寫大同小異,無甚新意。事實上這個系列中最好的作品都和狐鬼無關,例如《橋頭奇案》,偏僻的小地方出了一件命案,現場是一條旱河的橋頭,死者身首異處,兇器是一柄沾了血的大芟刀,刀柄卻緊緊地握在死者手里。作者在讓小說中的知縣偵破這宗奇案之前,借他人之口講了另外兩個雖不相干但同樣奇異的案子,增添了神秘的氣氛。橋頭奇案的案發情形是這樣的:死者馬老實一早去田里芟草,長柄的大芟刀扛在肩上。他走到橋頭,看到干旱的橋底下一只癩蛤蟆正要吃掉一只放屁蟲,卻有一條蛇要來吃癩蛤蟆。放屁蟲趁亂脫身,還順便向那條蛇放了個含有劇毒的屁,意外救了癩蛤蟆,癩蛤蟆卻反過來仍要追捕放屁蟲。旁觀的馬老實不齒癩蛤蟆恩將仇報,本能地手持芟刀刀柄朝橋下的癩蛤蟆捅,架在他脖子上的鋒利的芟刀一下子把他的頭整個砍了下來……知縣在現場搜集到放屁蟲、癩蛤蟆、青草蛇等,才破了這樁奇案。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中也出現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命案:兆矮子兆青身首異處倒斃在溪邊,旁人猜測他“發現了溪里有魚或者別的什么東西,藏在石頭縫里,便用草刀的長柄去戳。他肯定是用力過猛了,也沒注意到鋒利的刀刃正對著自己的后頸,一下戳空,一個拖刀從后面把自己的腦袋斬了下來”。《馬橋詞典》的故事發生的時代,大約也就是司馬寫作《橋頭奇案》的時候,兩位名作家筆下如出一轍的詭異命案,本身就是一則傳奇。
迷人的說故事能力
又如《紅絲鳳》,以一家老字號當鋪為背景,作者好整以暇,先鋪陳了一個不相干的故事:窮畫家到當鋪典當自己的畫,卻在識貨的老朝奉愿以重金受當后,決定把畫送給朝奉,分文不收飄然而去。引起讀者的興趣后,才轉入主題的紅絲鳳玉瓶——從陌生來客典當瓶子、老朝奉鑒賞后以重金受當,再由老朝奉說出這個瓶子的來歷。鬼斧神工的制作過程當然是虛構的,但在司馬中原的筆下,讀者不由得相信了真有那樣一件(小說里說是一批八個設計、名稱各異的瓶子)。之后小說的情節急轉直下:老朝奉承認自己看走了眼,花重金收回來的瓶子其實是幾可亂真的贗品,他當眾把瓶子摔碎后引咎辭職。但故事還沒完:一年后客人回來贖回瓶子,當鋪的人不知所措,只好把老朝奉請回來。老朝奉不慌不忙,變戲法似的拿出一只完好無缺的瓶子。客人驗收離去后,老朝奉才說出真相:瓶子是真的,而且還有一種特性——擲地即碎、見火即融。他就是利用了這個特性,當眾把瓶子摔破以免被人偷去,再用火把它融合回復原狀。
《紅絲鳳》一波三折,高潮迭起,加上司馬中原迷人的說故事能力,是鄉野系列中的精品。
顛覆傳統才子佳人故事的悲喜劇
另一篇《轇轕》的情節沒那么復雜,它寫的是兩個家族的恩怨糾葛,仿佛老套的才子佳人故事。小說中曹家少爺曹敦文和白家閨女白小鳳雖彼此傾心,卻因為曹母有心作梗,以悲劇收場。作者透過一個個無以考究的傳說來試圖找出這兩家結怨的原因:曹家祖上起大墳用白家的童男童女陪葬;曹家的人在白家的澡堂里失蹤;曹家人私下傳流言說白家女性是克夫的白虎、是臭骨頭……曹敦文甚至質疑:“也許當年魏武帝曾經殺過的人里有人姓白?或是曾經坑過四十萬趙卒的白起,也曾殺過姓曹的?”

其實不用追溯那么遠,小說結尾處,曹母退回了白家送來的婚帖后,司馬中原只用了不過百字就說明了她不愿和白家結親的原因:“幾十年前,她(曹母)做姑娘的時候,在小門小戶的姬家村,她的庚帖也曾在白家長房的香爐下面壓過。如果當時白家不退帖,哪里還有白姨奶奶這個妖精?她跟小鳳的父親在上元節的花燈會認識而且有了情,白家侮辱她,她就把這恥辱報在小鳳的身上。”不讓兒子娶白家的閨女,固然是做母親的私下算計,其實就連一開始曹敦文和白小鳳在上元節的邂逅,背后也是媒人王大腳在穿針引線,一方要盡力撮合,另一方卻早已拿定主意要她成不了事。司馬中原以冷靜的筆觸,顛覆了傳統才子佳人的悲喜劇,刻畫出鄉間眾生的世故與愚昧,穿插其中的離奇傳說都只是煙幕而已。
自己也相信了狐鬼傳說
這就是鄉野傳說系列的作者可貴的地方:那個時期的司馬中原,狐鬼故事再怎么駭人聽聞,他仍然能將現實和虛構區分開來,知道那些都是民間傳說:“你不信嗎?信的人可多著咧!”(《火葬》)“打一開頭,我就沒聽信過這樣荒誕的故事。”(《打鬼救夫》)“不必去聽信那些無稽的說法,但它總是一種象征。”(《山》)“并沒有誰親眼看見,只是屬于靈異世界里可信可疑的傳聞罷了。”(《狐的傳說》)他了解并同情傳述那些故事的人:“古老的北國鄉野上,有多少這樣愚呆的、可悲憫的、終生浸在酸苦和盼望當中的靈魂。”(《路客與刀客》)“說它是愚昧也罷,焉知那不是激發人運用思維、展現智慧的根源。”(《打鬼救夫》)
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司馬中原自己也相信了那些狐鬼傳說,并且言之鑿鑿地轉化成他自己的經歷,他忘記了在第一篇鄉野故事的結尾所提醒讀者的那句話“所有古老的傳說都是這么來的”,忘記了他曾經希望那些傳說“飄回古老的霉跡斑斑的歷史,永不要再流淌入下一代人童年的夢境”(《狼煙》)。抓鬼的終于被鬼抓去了,他的鬼故事愈說愈怪誕,也愈遠離文學,愈失去它原本的魅力,再不能吸引我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