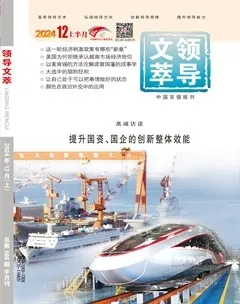有些事總能感動你

無論世道如何變化,只要尚有一絲善良未泯,有些事總能感動你。
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殉國后,日軍不許士兵觸碰張烈士,由軍官處理遺體,又以棺木禮葬之。第五戰區部隊與敵激戰兩晝夜,死傷兩百余,終于在陳家集尋得英烈墳冢,開棺奪骸,并連夜運往重慶。途經宜昌時,全市下半旗,十萬軍民恭送靈柩至江岸。其間,日機三次飛臨上空,祭奠群眾無一退卻。日機一彈未投,盤旋而去。
1942年3月,中國遠征軍在緬甸開始與日軍作戰,5月,中英盟軍全面潰敗。18日,在郎科地區指揮突圍戰斗中,戴安瀾將軍身中兩彈,因無藥物醫治,傷口化膿潰爛,26日,殉國。當時緬境內無木棺,將軍馬革裹尸還。7月6日,當衣衫襤褸的戰士們護送將軍的靈柩回國時,云南省騰沖縣臨時縣長張問德率數萬衣衫襤褸的縣民下跪迎靈,觀者無不愴然淚下。
西遷路途艱險,聞一多曾在給父母的信中用“此生從未嘗過之滋味”直言旅行團生活之苦,并用“前五日皆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宿,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來還原生活的狼狽。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西遷時,告訴留守的牧場管理人員,萬一敵人逼近首都,余下的牲畜,可遷則遷,不可遷則放棄,絕不怪他。“敵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見軍事情形不佳,就把這些牲畜用木船運過江。由浦口、浦鎮,過安徽,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運。這一段游牧的生活,經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的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踏上了它們長達幾千里的征途,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而且走一兩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旬抵達重慶。我于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它們,仿佛亂后骨肉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領導這次牲畜長征的,是管牧場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時的月薪不過八十元!”據羅家倫回憶:“一九三八年深秋黃昏,我由重慶沙坪壩進城。司機說前面來的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學的,停車一看果然是,這些牲口經長途跋涉,已經是風塵仆仆了。趕牛的王酉亭和三個技工須發蓬松,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我的感情震動得不可言狀,看見這些從南京趕來的牛羊,像久別的故人,我幾乎要向前去和它們擁抱。”
陳納德于1937年應邀來華擔任中國空軍顧問,1940年秋,其擬制的“空中外籍兵團計劃”終于得到羅斯福總統的贊賞與有限度的支持,遂在美國組織了一支援華外籍兵團,通過各方籌資,招募空勤地勤人員600名,編成3個飛行分隊。1941年8月1日,陳納德在昆明正式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愿航空隊,對外號稱“中央飛機制造公司”。陳納德除了在緬甸開展裝機訓練,還在云南空軍軍官學校授課,建立巫家壩機場訓練基地,為中國造就了一批新的訓練有素的空軍骨干。飛虎隊及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戰場共摧毀日機2600架,擊沉擊傷220萬噸以上的日軍商船和海軍艦只,擊斃66700名以上的日軍。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陳納德因與美國國務院對華政策產生分歧,毅然辭職回國。齊邦媛的《巨流河》寫到了他在重慶向市民告別時的情形:“陳納德在重慶的告別儀式幾乎是空前絕后地熱情感人,兩百萬人擠滿了街道和臨街的門窗,他的座車無法穿過人群,人們手推著他的車子到歡送廣場,全城傷痕累累的房屋上掛滿了各種旗幟,許多繡著飛虎的隊徽。這一年陳納德52歲。正因為他來到了神秘遙遠的中國,脫離了美國正規軍的律令,以近乎闖蕩江湖的個人魅力,聚集了千百個同樣的好漢,用驅逐機的戰術解救了地面上無數苦難的生靈。”
司馬遷寫《李將軍列傳》記李廣事:“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天下盡哀,皆因“彼其忠實心誠信”。
匹夫賤士,一念所結,便可感風雨,動天地。
(摘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