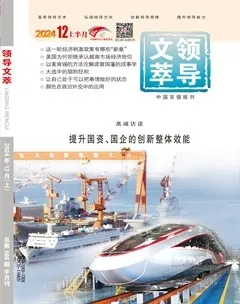顏色在政治外交中的應用

中國在政治上對顏色的應用歷史悠久。最早將顏色與政治聯系起來的當屬華夏始祖炎、黃二帝。以色為號使得華夏民族的重色觀念初具雛形。中國先秦人們對顏色的喜好在《禮記·檀弓》中可見一斑:“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先秦先民對顏色的重視由黑深到淺白,逐漸演變為赤,即紅色的過程。
至秦始皇掃六合統一天下,秦始皇對黑色的偏愛使黑色再次成為社會主色調。《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中提道:“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黑色成為在各種重要場合中使用的最高級別的顏色,表明統治者已注重將色彩運用到政治領域中。
顏色在政治層面的應用在漢朝達到第一個高峰。劉邦起兵反秦,為得民心,假借顏色之說制造輿論為自己壯大聲勢。《史記·高祖本紀》就有“赤帝子殺白帝子”之說。因戰國時期秦處西方,“五行”之說視西方為白為金,所以引文中的白帝子為秦朝。劉邦借赤色代指自己,暗示百姓自己受命于天,必將取秦代之。可見紅色在其伐秦攻楚時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覷,并由此成為漢初最為尊貴的顏色。隋唐以后,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中國士大夫的品官服色等級正式確立。這一時期紫色為高官所服,貧苦百姓著白衣,所以才有了唐代詩人劉禹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詩句。
及至唐代黃色成為皇家權力象征。唐玄宗天寶六年(747)采納太常卿韋滔的諫言,將乘輿的案褥、床褥、床幃和御袍都統一為黃色,以求身份相符;唐高宗時期,黃服在百姓和百官中被禁用,黃色正式成為皇家專有色彩和王權象征,并沿用至其后所有封建王朝。在東方文化中,諸如此類的政治與顏色互構的例子不在少數。顏色在政治領域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政治進程;反過來,政治活動中對顏色的應用,決定著民眾對顏色的認知,從而形成相應的顏色觀念。
在對外交往中,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夫人隨訪能為相對嚴肅冰冷的國際關系增添一份暖意。成功的夫人外交有利于拉近兩國關系,能夠更好傳播友好信息,為整體外交工作增色。各國第一夫人在外交中對顏色的巧妙應用能很好地彰顯其國家魅力和表達隱含的政治意圖。
在夫人外交中,不恰當的顏色選擇也會將兩國外交置于尷尬境地。2015年1月2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攜夫人米歇爾出訪沙特阿拉伯,吊唁剛剛離世的國王阿卜杜拉。米歇爾身著寬松艷麗的藍色外套,沒有戴頭巾。未遮頭發的裝扮令沙特網民一度認為此舉是美國第一夫人不滿沙特阿拉伯女性著裝待遇而對沙特女性著裝提出的公然挑釁。
沙特阿拉伯不僅因其富饒的石油資源而聞名,也以女性穿長袍戴頭巾而令世人印象深刻。米歇爾的藍色相對于沙特女性的黑色長袍而言過于艷麗,又因未戴頭巾遮臉違背了沙特阿拉伯的傳統習俗,被視為不尊重該國文化。可見米歇爾錯誤的顏色搭配,使其開展的夫人外交未能獲得期盼的效果,反而適得其反,得不償失。
毫無疑問,首腦外交作為最高級別的外交形式是國家交往中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無論是雙邊或多邊政策的制定,還是經貿往來、人文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良性的首腦外交。夫人外交最初以首腦外交的附屬形式登上國際政治舞臺,后因其獨特的柔性魅力逐步成為外交關系中不可替代的一種力量。因此,在夫人外交活動中準確合理地利用顏色的輔助作用,既體現出對他國文化、習俗、傳統的尊重,也顯示出作為第一夫人自己的涵養與智慧。
(摘自《讀懂外交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