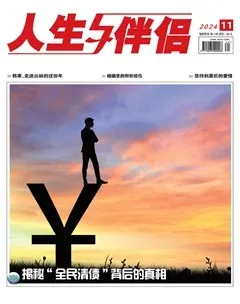韓寒,走進叢林的這些年
2014年,《后會無期》上映拿下6億,韓寒坐穩了新身份。
導演之外,他還順手為同名主題曲填了詞,“當一艘船沉入海底,當一個人成了謎……”被鄧紫棋唱成了年度金曲。
而后,“作家”韓寒悄然隱去,十來年里他不再有新書面世,畢竟他自己都說“雜文這東西很雞賊。”“如果不能超越《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就先不寫了。”“寫來寫去,最后都是發泄情緒……我就毅然把它給停了。”
面向公眾的表達從文字變成影像,韓寒成熟了許多,也沉默了許多。
他的博客最后更新的時間定格在2014年,微博主頁空空如也。偶爾出席活動講兩句,網友評價大多也都是“不太韓寒”。
十年倏然而過,如今那艘沉船有了名字叫“里斯本丸”,倒是韓寒真成了個謎。
他的現狀如何,又是否與當年全然兩樣,一切都成了薛定諤的貓,讓人看不清楚。
蹺著二郎腿,穿著借來的黑夾克,長發遮住半張臉,2000年,17歲的韓寒就這樣出現在央視《對話》的演播間。
在他正式入場前,現場火藥味已濃。
臺上兩名教授銳評完“韓寒現象”,話筒傳到觀眾手里。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問及如何看待韓寒,扎著馬尾辮的大姐淡淡說道:“我覺得韓寒現在是這樣,他可能是土雞變鳳凰。”
一番揶揄之后,主持人這才笑盈盈地把韓寒請到臺上。
這段訪談的后半段,為今天的中文互聯網上貢獻了諸多名場面。至今還有不少短視頻冠以“少年韓寒舌戰群儒”“韓寒高能一挑五”的標題在網上瘋傳。
但實際上,拋開這些口頭上機巧和節目花邊不談,當時臺上兩位教授的解讀倒還算中肯。
其一說,“韓寒其實很害怕他說的話是正常的,他試圖創造一種另類文化……他必須這樣表演。”“韓寒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被媒體、被出版業、被他的書、被他說的話堆積起來,我們所理解的就是被這些堆積起來的韓寒,而韓寒也在不斷往這些堆積物上添磚加瓦。”
另一位則引用了諾獎得主江崎玲于奈的原話——偶爾偏離正軌,走進叢林,你會得到驚人的發現。順帶點了韓寒一句“不是完全偏離”。
像是告誡,也像是預言。
至少站在今天,我們回顧韓寒在新世紀里頭幾年的表現,他在做的,無外乎上面兩件事——持續“韓寒化”和“走進叢林”。
換句話說,就是把“叛逆”進行到底。
復旦給了他特招錄取的機會,他不要,他說“復旦請他去當教授,得看自己有沒有時間”;博客上掀起“韓白大戰”,他寫《文壇算個屁,誰也別裝逼》掃射京圈文壇一眾大佬……
反教育、反主流、反權威,80、90一代深惡痛絕之事,他總能摻上一手。用野路子掀翻學院派、少年提著大寶劍行走江湖的戲碼,精準挑弄到粉絲的痛點和爽點;這很韓寒。
然而,韓寒并非天生離經叛道。
為暗戀的女孩苦練長跑,以特長生身份考入同一所高中;上課寫《三重門》七門功課亮起紅燈,不想被開除從而選擇主動退學……
至少在受到大眾媒體關注之前,這些故事堆積出來的韓寒,頂多算主流視野中的“問題少年”,離后來媒體筆下的“文化英雄”“反應試教育斗士”還差著好遠。
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一層層標簽、一場場輿論緊貼過來,你推我就之下,少年韓寒“走上神壇”。
青年們需要精神偶像,媒體需要批判對象,與其左右為難,不如繼續這種無意識的“反叛”表演。
畢竟一個17歲的少年,突然被卷入洪峰,每日面對著同樣激烈的批判與崇拜,后面的路怎么走,是個問題。
同是80后非典型作家,如果韓寒學大冰,他的作者簡介上應該這樣寫:韓寒,作家、賽車手、導演、歌手、演員、雜志主理人、餐廳老板、電競選手、投資人……
這些職業不僅韓寒都干過,而且大多成績斐然。
當作家,韓寒自然不必多說。16歲出道,17歲一篇《杯中窺人》驚艷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眾評委,寫的書從《三重門》到《1998:我想和世界談談》,10年間光是版稅就賺了至少4000萬。門戶網時代,他在博客寫雜文,輕松博得一個“博客流量之王”的頭銜,點擊量至今無人超越。
當賽車手,他孤身北上,在北京的頭兩年燒光《三重門》第一筆版稅50萬,一度窮到連“房子都快租到山里去”了。但在27歲時,他已是中國職業賽車史上唯一一位場地和拉力的雙料年度總冠軍,站在中國職業賽車賽事最高峰,成績傲人。
當導演,他10年里拍了五部片,除了《四海》敗北,其余四部表現不俗,其中《飛馳人生2》更是拿下33億票房,而他自己持股過半的亭東影業,估值遠超20億元。
盡管當年申請退學時,辦公室一幫老師最擔心的是韓寒“將來靠什么養活自己?”
當然,成功與成名,韓寒靠的不只有才氣,還有一場場“廝殺”,這些在今天都很難復制。
2006年,文壇前輩白燁發表了一篇博文《80后的現狀與未來》,評價郭敬明與韓寒時一褒一貶,傾向明顯。提到韓寒的作品,他這樣寫道:“他的《2004通稿》,我看了之后很吃驚,里面把他在中學所有開設的課程都大貶一通,很極端,把整個教育制度、學校現狀描述得一團漆黑,把所有的老師都寫成是誤人子弟的蠢材和十惡不赦的壞蛋。”并說韓寒之流“只進入了市場,尚未進入文壇”。
白燁撞上了槍口。24歲的韓寒,正值“舞刀弄槍”的青年時代,直接一篇《文壇算個屁,誰也別裝逼》,拉開了2006年最精彩的文壇大戲。“別湊一起假裝什么壇什么圈的,什么壇到最后也都是祭壇,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我早說過,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一個人,頂多帶一武功差點的美女,只有小嘍啰才扎堆。”
幾番交鋒下來,白燁招架不住,他的圈內好友紛紛下場幫腔。隨后《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導演陸川和父親陸天明、作家解璋璽、高曉松等文藝圈人士也都參與了這場“倒韓”接力賽。
韓寒白天賽場飛馳,晚上博客鏖戰。一個人對一群人,優勢仍在韓寒。文字犀利直白,若干臟話加持,情緒拿捏到位,網上的年輕人站在了韓寒這一邊。
其中最有意思的還屬高曉松,知道文字上和韓寒斗狠勢必吃虧,于是另辟蹊徑,直接一紙狀書把韓寒告了,理由是“《三重門》引用了他的歌詞沒授權”。不過他還是挨了韓寒一句:“高曉松告韓寒這事情,古人早有定論,那就是,‘高處不勝寒’。”
這場后來被載入文壇史冊的“韓白大戰”,最終以白燁關停博客、韓寒大獲全勝收場。
而經此一役,韓寒也找到了手感。他的射程之內,郭敬明、余秋雨、趙麗華、陳凱歌、鄭鈞、李敖等人均未能幸免。
而真正讓他影響力再上一個臺階、從“叛逆少年”走向“公民韓寒”的,則是他面朝社會政治領域的轉向。
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危險但回報率很高的選擇。但踩著鋼絲,韓寒依然很穩。
談抵制法國貨,他寫“時尚愛國青年都等著上級思想部門發新專輯呢,結果一聽,我靠是張精選集。”
談取消校服,他寫“把幾千個學生弄成一個樣實在是顯得非常愚昧。”談“文化管制”,他寫“眾所周知,保護青少年從來是我們國家進行‘文化管制’的最好借口。”
不止于此,在當時顯著的公共社會事件中,幾乎都能聽到韓寒的聲音,不偏不倚,極度危險但又恰到好處。
當然,也有人視韓寒介入公共領域的轉變是一場“豎牌坊做知識分子”的作秀。如社科院研究員施愛東則總結了兩條炮制韓寒的準則:“一是針砭時政的內容大幅增加;二是文章風格和價值觀念發生突變,用語變得文明,立場偏向底層,價值趨于普世。”
但不管是不是刻意設計,韓寒在文化、社會、政治表達上的趨于成熟,讓那些曾經各據話語體系,視韓寒如敵的50后60后70后們,對這個青年不再敵意濃厚,甚至態度逆轉。
在那個“公知”尚還不是貶義詞的年代里,洪晃稱“韓寒是中國唯一可以被稱為公知的人”,而梁文道則更是把韓寒捧為“當代魯迅”。
2010年,韓寒肖像赫然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照片中他手握鋼筆,表情冷峻,其號召力已然登頂。
此后數年,無論是跨行做雜志、開餐廳、拍電影、開影視公司,自稱“表達不一定要面向所有人”的韓寒,在新賽道里取得的豐厚流量和驕人成績,至少有一半的功勞來自那個時候。
當不少人在今天談及韓寒,目光還停留在20年前那個不羈少年身上時,其實他的身份早已換了一輪又一輪,在他身后,一座龐大的商業帝國正拔地而起——2015年,亭東影業成立,公司名字取自韓寒的家鄉亭林鎮亭東村。又四年后,亭東影業估值23億,韓寒已悄然攢出超10億身價。
當年韓寒準備退學時,他的伯樂、《萌芽》雜志主編趙長天對他說:“人是需要妥協的。你現在不妥協,將來也要妥協。”
韓寒沒聽進去。很多年后,他與蔣方舟在另一檔節目相逢,韓寒對她說了相似的話。
蔣方舟問:“我很久前在某個場合,說過‘韓寒做了一件很牛逼的事,他更新了社會的話語系統,但可惜的是他沒有文化,當然我知道用文化去衡量人太暴力了’,我到現在還覺得自己是對的,我想聽聽你的反駁。”
韓寒回道:“我為什么要和你反駁,你是個可愛的姑娘。終有一天,你會替我反駁你自己的。”
2018年,結束一場訪談后,韓寒發文感慨:“退學是一件很失敗的事情,說明我在一項挑戰里不能勝任,只能退出,這不值得學習。”
此話一出,眾人錯愕。韓寒駁倒了曾經的自己。
畢竟,“退學”曾是少年韓寒最為得意的“手筆”,他的成名路以及后來擁有的一切都發軔于此。
當年他掛科、留級、退學,寫下“七門功課紅燈,照亮我的前程”,身后是無數“效顰”的少年;17歲對著央視鏡頭驕傲地說出那句“美國總統四年一換,韓寒永遠不變”時,粉絲眼中的他,何等意氣風發……
但少年老去,理想也終于長出了啤酒肚。
曾經50萬版稅擺在韓寒面前他覺得也不過如此,但后來他也說:“提著一把大寶劍,要去改變這個世界,但大寶劍也是要錢的。”
他曾經夸張地對世界宣告“用漢語寫字的人里頭,錢鐘書是第一,我是第三”,但后來他放下了筆,甚至偷偷摘掉了“作家”的標簽。
有人引用王小波那句“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惋惜韓寒抖落一身鋒芒。但沒人注意,其實站在韓寒對面的已不是當年的對手了。
回溯韓寒的過去,這些變化我們很難去找出一個分明的節點。
也許是方舟子的代筆質疑,也許是女兒韓小野的出生,也許是涉足利益紛雜但必須維持“人情世故”的影視圈,也許都不是。
就像他首部電影《后會無期》制片人方勵說的那樣,以前他當作家、當車手,一個人可以擔下一切,而跨行當導演之后面對的是一群人,“……不能讓這個集體散掉,要把握這群人共同的情緒和愿望,任何一個年輕人,有過這種經驗之后,會有新的人生感悟。”
成長當然不是什么丟人的事情,“觀過世界之后才有世界觀”也不只是一句雞湯,用新的經驗去矯正少年時的狂妄,然后與自己和解,向世界道歉。
這樣的韓寒其實還是韓寒。
只是很多時候,神壇上的人,是不被允許做自己的。
韓寒最近一次公開出現,是在方勵導演的《里斯本丸沉沒》的上海路演現場。跟觀眾聊起了十年前二人是如何偶然在東極島探尋到這段往事時,他講的和媒體宣傳的有點出入,他說“當年寫‘當一艘船沉入海底’完全是為了押韻”,臺下大笑。
現場的他,打扮依然簡單,一身休閑,戴著細框眼鏡,面頰飽滿,談吐溫潤平和。久不露面,這個模樣很難讓人把他和心中的韓寒畫上等號。
最近兩年,他幾乎完全放棄了文字表達。新片上映沒有宣發,圍繞著他的幾場爭議也都沒有回復。韓寒在微博消失得徹徹底底。
他倒是開了抖音,3年里發了31條短視頻,積累粉絲36萬。這和當年韓寒入駐微博,僅僅發了一個“喂”字引發的轟動不可同日而語。
粉絲多少、傳播力如何早已不是韓寒在意的東西了。當年《后會無期》拍攝,路金波、方勵建議韓寒怎樣做時,韓寒對他倆說:“相信我,我懂年輕人想要什么。”
現在的他只會更懂。
但他偶爾也會想停下找找自己想要什么。他曾經寫,“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喜歡的一切在一起。”如今答案依然沒變。
少年時喜歡出風頭,迷戀“力量的延伸”,文字在他筆下是棍棒刀槍,俏皮張揚,他享受著被關注、被討論、被“標簽”;如今身價十億,已為人父,悟到的又是另一重心境。
過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年紀,被什么樣的東西吸引,就走什么樣的路,韓寒跳出“符號化韓寒”,又做回了自己。
工作不忙的時候,他也撥弄撥弄吉他,坐在上海夜晚的露臺里,手中響起盧冠廷作曲的《歲月輕狂》,他閉上眼睛,兀自唱著:從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響,放眼看歲月輕狂……不回想不回答,不回憶不回眸,回不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