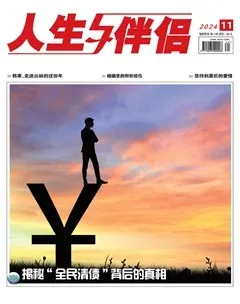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女作家去世:一生傳奇,享年99歲
2024年10月21日,著名華裔女作家、翻譯家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家中逝世,享年99歲。
她的次女王曉藍(lán)發(fā)布消息,稱母親“走得很安詳,沒有太多痛苦。”
聶華苓逝世時,距離她100周歲生日只差三個月。
在華語世界里,大家可能比較熟知張愛玲、嚴(yán)歌苓這樣的多產(chǎn)作家。而這位促進(jìn)世界文學(xué)交流的“昭君”,似乎很少人知道。
她被譽(yù)為“世界文學(xué)組織之母”,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來自中國的女作家。
在她家客廳,包括汪曾祺、陳映真、白先勇、王安憶、遲子健、畢飛宇等,全世界1400多名的詩人與作家,都曾在那里餐宴飲酒、肆意暢談文學(xué)。
打開聶華苓的自傳《三輩子》,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蕩蕩的歷史畫卷:國家戰(zhàn)亂、顛沛流離、永遠(yuǎn)的鄉(xiāng)愁。聶華苓漂泊了近一個世紀(jì),從漢口到北平,從大陸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
她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聶家祖上算是鐘鳴鼎食之家。
聶華苓的祖父是中過舉的前清文人,原本是要上任當(dāng)縣長的,沒想到赴任途中,武昌起義成功,他只好又坐著轎子回來了。父親聶洸(字怒夫)畢業(yè)于陸軍軍官學(xué)校,在桂系擔(dān)任要職,一度遭國民黨追捕。桂系被蔣介石擊垮之后,一家人在漢口的日本租界住下來。
兵荒馬亂中,聶洸被槍殺,聶家就此散了。
說起來,聶華苓這一生都在流浪。
13歲以前,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那時,她和弟弟為了吃上一根雪糕,需要走過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英租界的紅頭洋人,拿著木棒打得中國的人力車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饒;日本兵在日本人開的妓院里高聲歌唱,其間夾雜著高麗女人的媚笑。
半殖民地的凄惶畫面,在聶華苓幼小的心靈深處刻下了一道道永難磨滅的傷痕。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眼看武漢就要被日本人占領(lǐng),母親帶著五名幼子逃亡至鄉(xiāng)下避難。
母親孫國瑛是個開明人,在聶華苓的自傳《三輩子》里,她這樣描寫母親:一身黑緞旗袍,長長的白絲圍巾,圍著脖子閑搭在肩后。玳瑁黑邊眼鏡,襯出白皙的臉蛋。一腳在身后微微踮起,腳尖仍然點(diǎn)在地上,半轉(zhuǎn)身微笑著,要走又走不了的樣子。
聶母與聶父成婚后,方知他家中早已娶妻生子。聶母一度欲吞物尋死,多虧聶華苓揮著小手朝她笑,才讓她放棄了輕生的念頭。聶父死后,聶母帶著五個幼兒與聶家大家族內(nèi)部決裂,母子幾人數(shù)度遷家而居無定所
這樣的新式女性,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外頭烽火連天,她也執(zhí)意要送女兒到外地求學(xué):
“我母親說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讀書的……走的nkYO76awgOETe8Av40LTTw==時候看到我母親在岸上已經(jīng)相當(dāng)遠(yuǎn)了,就哭啊哭啊哭啊,我母親站在那里也哭。”
母親的氣度與倔強(qiáng),無疑對聶華苓后來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響。
彼時僅14歲的聶華苓,在母親毅然決然的目光和淚水中,就這樣流浪下去。求學(xué)的日子困頓至極,有時一天只啃一個硬饅頭,有時要跟狗搶食物。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寶飯”都成了人間美食,聶華苓甚至一度染上瘧疾。
只是,眼見大好河山慘遭日本人蹂躪,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體的苦,她的心中猶如倒入了黃連,痛苦至極。
為了不當(dāng)亡國奴,再苦也要一路奮戰(zhàn)。
聶華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動中:慰問抗戰(zhàn)的傷兵,為他們唱歌,代寫家書……
那一路上所見的名山勝水,更是讓她增加了愛國的砝碼:我年輕的日子,幾乎全是在江上度過的。武漢、宜昌、萬縣、長壽、重慶、南京……我在江上活過了四分之一世紀(jì)的戰(zhàn)亂。
從漢口到北平,從小學(xué)到大學(xué),從純真的孩子到挨凍受餓的流亡學(xué)生,總算迎來了抗戰(zhàn)勝利。
風(fēng)雨坎坷中,聶華苓與國立中央大學(xué)的同學(xué)王正路結(jié)婚了。
她以為找到了安心的歸宿,那個時期,她甚至以“遠(yuǎn)思”為筆名,發(fā)表了一篇諷刺性文章《變形蟲》,開啟了她的創(chuàng)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局勢也好,都無法讓聶華苓停下流浪的腳步。
王家的大家族,需要媳婦日日向長輩請安奉茶,繁文縟節(jié)壓制了聶華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嘆:“我在那個大家庭里,只是一個失落的異鄉(xiāng)人。”
而婚姻之外,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幼年失怙的情形仍歷歷在目,聶華苓內(nèi)心充滿了恐懼。
1949年,24歲的聶華苓拖著母親與弟妹,一家人到了中國臺灣。“流浪”變成了“流亡”。大陸成了她永恒的鄉(xiāng)愁地標(biāo)。然而,那座小島,并沒有給聶華苓帶來風(fēng)和日暖,而是一片肅殺之氣。
到了臺北后,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觸礁了。
出身大戶的丈夫根本經(jīng)不起風(fēng)雨,“結(jié)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實(shí)亡,家庭的重?fù)?dān)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個偶然的機(jī)會,聶華苓進(jìn)入胡適發(fā)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任文藝欄主編。當(dāng)時臺灣的文學(xué)環(huán)境政治色彩非常濃厚,不僅寫作者被監(jiān)視,文字也要被審查。而且,很多人為了賺取微薄的稿費(fèi),都可以寫出配合“反共”的文學(xué)作品。
但聶華苓不一樣,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爭,終致家庭離散,這使她對政治敬而遠(yuǎn)之。
為了避開政治,她將自己主編的《自由中國》文藝版,打造成純文學(xué)天地。這簡直就像是渾濁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異石頓時袒露在陽光之下。
現(xiàn)在成為經(jīng)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shí)秋的《雅舍小品》,還有柏楊的小說和余光中的詩,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場。
可以說,1950年代整個臺灣文學(xué)的火種能夠被點(diǎn)燃,都?xì)w功于聶華苓和林海音這兩位女性。
她們二人在威權(quán)時代開風(fēng)氣之先,提倡純文學(xué)創(chuàng)作,為整個中國的文學(xué)作出了卓越貢獻(xiàn)。

聶華苓在臺灣的倏忽15年,卻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評,也是聶華苓一生中編、寫、譯成果最豐碩的黃金時期。
她的《失去金鈴子》,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徐鐘珮的《余音》,并稱為三部帶有自傳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長小說。同時,《自由中國》在雷震的帶領(lǐng)下,除了發(fā)表針砭時弊的社論,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
可惜,當(dāng)時的臺灣文壇和政治環(huán)境過于險(xiǎn)惡,“白色恐怖”籠罩了全島。
因?yàn)槔渍鹂l(fā)了一篇夏道平寫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被誣陷“知匪不報(bào)”,以“煽動叛亂罪”坐牢十年。而創(chuàng)辦人胡適卻在盛贊雷震所作所為的同時,公開聲明辭去他發(fā)行人的角色。
對于胡適的態(tài)度,聶華苓認(rèn)為他明里是“抗議”當(dāng)局,實(shí)則是“擺脫”半月刊:“每個人都有很多面,多人以為胡適偉大,而我只是直說我在雷震案中所見到的胡適。”
聶華苓的無私與坦蕩,如男兒般的俠義與正氣,正是雷震以及殷海光——西南聯(lián)大金岳霖先生的弟子等人的風(fēng)骨與氣節(jié),教了她做一個中國人應(yīng)該有的樣子。
她在自傳里寫道:“他們做人的風(fēng)骨,獨(dú)立的風(fēng)格,幾十年來影響我的為人處世……雷震、殷海光是那樣的挺立。”
雷震出獄9年后便過世了,和殷海光最終長眠在“自由墓園”中—兩位鐵骨錚錚的理想踐行者,是擔(dān)得起“自由”二字的。
聶華苓跟隨著雷震等人,為自由而吶喊,然而,“自由中國”并沒有讓她看到自由。隨后《自由中國》被封,聶華苓身為編輯雖躲過牢獄之災(zāi),卻被孤立,終日受到監(jiān)視。彼時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自由中國》和前輩們蒙難;弟弟漢仲在一次例行飛行中失事;母親得了絕癥過世;婚姻和經(jīng)濟(jì)陷入死局。
聶華苓的第二個落腳處就此斷裂。《易經(jīng)》里說,剝極則復(fù)。剝到極點(diǎn)了,一切就會從頭開始。命運(yùn)大約十分憐憫這樣率直、不趨炎附勢,有著獨(dú)立人格的女子,在最艱難的時刻,一道生命曙光刺破了黑壓壓的烏云,照亮了她整個后半生。那道曙光,是聶華苓38歲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羅·安格爾。
安格爾對她一見鐘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臺北并不是個美麗的城市……但有華苓,看她就夠了。”
保羅·安格爾是一位美國詩人,這位馬夫的兒子出身貧寒,小學(xué)就開始打工。他為猶太人點(diǎn)過火、當(dāng)過送報(bào)員、在雜貨店兼過差,小小年紀(jì)就看盡人生百態(tài),卻對文學(xué)懷抱理想。
聶華苓對這段婚姻的評價,是“我們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美滿的婚姻。”他們婚后在愛荷華筑起愛巢,一起劃船、烤肉、談文學(xué),與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侶也不過如此。
此時,聶華苓學(xué)會用另一個視角看世界,她意識到,過去的生活雖然艱辛,但她對世界的認(rèn)識卻非常的片面:“在這兒,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峽兩岸的社會,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作家和作品,這使我的視野擴(kuò)大多了,感情冷靜多了,看法客觀多了!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來說明我的過去,大概是正確的。”
過往的痛苦與恩怨,終在時間的力量下漸漸消融。隨之涌上心頭的,是她那份歲月沉淀后的氣度與俠義。
彼時,安格爾聘請她到他的“寫作工作坊”教中文。
有一天,他們在河上泛舟,聶華苓突發(fā)奇想,建議安格爾將“寫作工坊”改成“國際寫作計(jì)劃”。安格爾聽了,忍不住大叫“瘋狂”,要是改成國際寫作,每個作家光是吃、住、路費(fèi)就要好幾千美元啊!
然而聶華苓卻鍥而不舍,他們先是得到愛荷華大學(xué)的贊同,接著到處寫信,拜訪,從私人到大企業(yè),終于募得300萬美元的基金。
接下來幾十年,我們看到地球上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愛荷華相遇了。
“寫作計(jì)劃”每年邀請各國作家赴美訪問,通過演講、討論、旅行等方式,讓作家們的文學(xué)觀念和表現(xiàn)技巧得到?jīng)_擊和對流。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當(dāng)時大部分作家都帶著狹窄的視野,但通過交流,發(fā)現(xiàn)世界上原來有那么多不同的人,回國后他們的世界觀都拓展了。
他們以文會友,消除彼此之間的隔閡與芥蒂。譬如,以色列作家和埃及作家從一見面就往對方臉上扔杯子,到四個月離別時,卻在機(jī)場抱頭痛哭;伊朗女詩人臺海瑞與羅馬尼亞小說家易法素克之間產(chǎn)生了愛戀。
丁玲回國后在《訪美散記》中寫下:她看到的美國,與過去聽到的“帝國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大不相同。
美國有超級市場,有分期付款的購房方式,“做的是今天的工作,花的是明天的錢,還的是昨天的債”,汽車多到停車難和修車難……
5年后,丁玲過世了,她寫下的這些,20年后在中國通通實(shí)現(xiàn)了。
而她所見識的一切,都是聶華苓為她提早打開了看世界的窗。
身為中國人,聶華苓最牽掛的還是那些用漢語寫作的作家。彼時,中國作家想出國,都會面臨語言和資金等方面的困難。為了讓中國作家參與國際寫作計(jì)劃,聶華苓自己每年都捐款。幾十年來,“寫作計(jì)劃”共邀請了世界各地作家1400多位,而漢語寫作的作家,就占了100多位。
在國際寫作交流上,聶華苓不遺余力;在個人作品上,除了翻譯作品,她堅(jiān)持用母語中文創(chuàng)作。《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三輩子》等,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歸心靈故鄉(xiāng)的途徑。
因?yàn)閷?chuàng)作語言的堅(jiān)持,聶華苓獲頒2009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xué)獎”
對故土與母語的眷戀,始終是聶華苓的難言之痛。1970年,她與安格爾共同翻譯了《毛澤東選集》。為了了解每首詩詞的背景,他們翻閱了很多中國革命的書籍,特別對二萬五千里長征作了較細(xì)的研究。
這使她明白了許多過去不明白的道理。她說,“他們什么艱險(xiǎn)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帶,是為了幾萬萬人民和后代,他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聶華苓的氣度與俠義,已超越了一個作家的范疇。

她有無私坦蕩的俠義,一心造福全世界文人,為近代中國作家打開了一扇走向世界舞臺的窗。
“愛得熱烈而純粹,恨得鮮明而徹底”,這位湖北的“昭君”,為華文文壇以及整個世界文學(xu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
既有來程,便有歸處。她用24年的韶光扎下了中國根,經(jīng)過歲月流轉(zhuǎn),長出蒼勁的軀干和繁盛的樹葉,又回饋給了中國文壇。
一個中國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用中文寫中國人、講中國故事,用綿薄之力促進(jìn)祖國統(tǒng)一。
作為一名世紀(jì)老人,聶華苓見證了祖國從動蕩走向穩(wěn)定,從衰敗走向繁榮,不論何時何地,她都驕傲而莊嚴(yán)地聲明:“我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