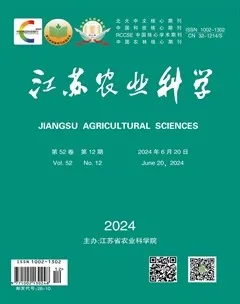基于轉錄組和代謝組分析八角黃酮類化合物合成途徑關鍵基因











摘要:為解析八角(Illicium verum Hook.f)黃酮類成分合成途徑的關鍵基因,以八角果實和葉片為試驗材料,進行轉錄組測序分析和UPLC-ESI-MS/MS代謝組分析,并將兩組學進行聯合分析。八角代謝組分析獲得12類共1 292種化合物,不同組織次生代謝產物的累積有明顯的差異,共有571個差異代謝物(DAMs),包括331個上調基因、240個下調基因,其中黃酮類化合物占比最大;測序共獲得41.04 Gb的clean data,各樣本Q30堿基占91.37%及以上。八角果和葉中檢測并篩選得到4 506個差異基因(DEGs),包括2 035個上調基因、2 471個下調基因,其中有132個與黃酮合成相關的差異基因;兩組學聯合分析篩選得到25個代謝物和33個基因,將其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C4H、CHS、CHI、F3H、F3′H、F3′5′H等基因的表達水平與黃酮代謝物的積累顯著相關,表明這些基因參與調控黃酮類化合物的生物合成。本研究首次闡釋了八角黃酮類成分的合成途徑和相關基因,為利用生物工程技術生產其黃酮類化合物提供了依據,對于擴大用藥資源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八角;轉錄組;代謝組;黃酮類;關鍵基因
中圖分類號:R282.71;R28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4)12-0060-09
藥用植物是許多化學藥物的重要原料,目前臨床用藥來源于植物代謝物的占1/3以上[1]。植物在發育和生長過程中,不同器官和組織的發育階段以及不同生長環境影響著其代謝產物和轉錄本的積累和表達模式,導致基因和代謝物存在一定的差異,基于這些差異進行植物功能基因、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徑的分子機制、藥用植物新資源開發、資源可持續利用及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等研究具有深遠意義[2-3]。
藥用植物中含有大量多樣的次生代謝產物,其積累與時間、空間、環境條件等密切相關[4]。次生代謝物的合成是一個復雜的調控網絡,其中包括相關基因的表達、轉錄后修飾、蛋白質翻譯和翻譯后再修飾等過程,而單一的組學技術難以充分揭示如此復雜的植物生物學過程[5-6]。通過多組學整合,建立起基因調控網絡,能夠在分子水平上對各分子間的調控以及因果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進而解析不同條件下植物的基因功能以及相互作用網絡[7]。代謝物的形成需要經過基因-轉錄-翻譯的過程,是基因與表型之間的橋梁,基于轉錄組測序得到的差異表達基因可以揭示在不同條件下相同基因的表達水平。通過聯合兩組學進行研究,能夠從“原因”與“結果”的角度探討藥用植物活性物質的生物合成途徑、代謝規律及關鍵調控位點,為闡明藥用成分的形成、提高藥用成分的積累、科學生產優質藥材提供理論依據,進而達到全面提升藥材品質的目的[6,8]。近年來,代謝組學和轉錄組學聯合分析已被廣泛應用于艾(A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9]、溫郁金(Curcuma wenyujin Y. H. Chen et C. Ling)[10]、銀杏(Ginkgo biloba L.)[11]等藥用植物的有效物質生物合成途徑分析。
黃酮類化合物在高等植物的葉、花、果實等組織中普遍存在,是植物經過長期自然選擇而形成的一類次生代謝產物[12]。黃酮類成分除了對植物的生長發育有重要影響,還具有抗氧化自由基、抗病毒、抗菌、抗腫瘤、抗炎鎮痛、抗癌、治療心腦血管疾病和骨質疏松、保肝、抗輻射和抗衰老等藥理活性[13],在美容、醫療、食品加工等領域有著廣泛應用[14]。
八角(Illicium verum Hook.f),別稱八角茴香,在我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應用歷史[15],具有溫陽散寒、理氣止痛的功效[16]。從八角果、葉中提取的八角茴香油是各種食品香精、香水、香皂、牙膏等產品的原料[17]。八角的主要化學成分為揮發油、有機酸類、黃酮類、萜類、苯丙素類等[18]。目前,關于八角的研究多集中于八角揮發油上,而關于八角黃酮類成分的研究較少,其生物合成途徑的相關基因仍不十分清楚,極大地制約了八角次生代謝調控和分子輔助育種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利用轉錄組學和代謝組學,基于基因和代謝物的差異表達,從基因表達和代謝物積累2個不同水平對八角葉和果實進行相關性分析,挖掘合成途徑上的關鍵基因,進而解析八角中黃酮類成分的合成途徑。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八角的葉片和果實于2022年4月采集于廣西南寧市高峰林場(海拔164 m,22°54′N,108°13′E),每樣3 份重復,純凈水沖洗干凈,以鋁箔紙包裹液氮速凍后,用干冰送至武漢邁維代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轉錄組與代謝組試驗。樣品經廣西中醫藥大學藥學院黃勇教授鑒定為木蘭科植物八角(Illicium verum Hook.f.)。
1.2 廣泛靶向代謝組樣品制備
使用凍干機(Scientz-100F)對供試樣品進行真空冷凍干燥,用研磨儀(Retsch,MM 400)將干燥樣品研磨(30 Hz,1.5 min)至粉末狀;稱取粉末 50 mg,加入70% 甲醇1.2 mL;渦旋 6 次,每次持續30 s,每30 min渦旋1次;之后離心(12 000 r/min,3 min),取上清液,用微孔濾膜(0.22 μm)濾至進樣瓶中,備用。取樣品提取物混合制備成的質控(QC)樣本,以檢驗在同一試驗條件方法下試驗樣本的重復性。在儀器操作的過程中,為監測試驗過程的重復性,每10個試驗樣本中需插入1個QC。
1.3 色譜質譜(UPLC-ESI-MS/MS)采集條件
超高效液相色譜(SHIMADZU Nexera X2)條件主要為:色譜柱為 Agilent SB-C18(2.1 mm×100 mm,1.8 μm);流動相為含0.1%的甲酸水(A相)和含0.1%甲酸的乙腈(B相);柱溫40°C;流速0.35 mL/min;進樣量2 μL;洗脫梯度14 min(0.00~9.00 min,5%~95%B;9.00~10.00 min,95%B;10.00~11.10 min,95%~5%B;11.10~14.00 min,5%B)。串聯質譜(Applied Biosystems 6500 QTRAP)條件主要包括:電噴霧離子源(ESI)溫度500 ℃;離子噴霧電壓(IS)5 500 V/-4 500 V (正離子模式/負離子模式);離子源氣體I(GSI)設置為50 psi,氣體II(GSII)為60 psi、氣簾氣(CUR)為25 psi,碰撞誘導電離參數設置為高。在QQQ和LIT模式下分別用10、100 μmol/L聚丙二醇溶液進行儀器調諧和質量校準。QQQ掃描使用MRM模式,并將碰撞氣體(氮氣)設置為中等。通過進一步的去簇電壓(DP)和碰撞能(CE)優化,完成各個MRM離子對的DP和CE。根據每個時期內洗脫的代謝物,在每個時期監測1組特定的MRM離子對。
1.4 數據分析
采用代謝物信息公共數據庫以及MVDB數據庫(武漢邁維代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物質定性依據二級譜信息進行,定量選用重四極質譜多反應監測模式(MRM)進行。得到不同樣本的代謝物質譜數據之后,對所有物質質譜峰進行峰面積積分,并對其中同一代謝物在不同樣本中的質譜出峰進行積分校正[19]。采用多元統計分析,對樣本分別進行主成分分析(PC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別分析(OPLS-DA),檢測各組樣本之間的代謝物差異,展示各分組之間的變異度[20],并對比較組中代謝物進行差異倍數(fold change,FC)值計算。根據 OPLS-DA" 結果,以FC結合多變量分析 OPLS-DA 模型的變量重要性投影(VIP)為篩選標準,選取 VIP≥1,FC≥2和FC≤0.5的代謝物為差異代謝物(DAMs),利用京都的基因和基因組百科全書(KEGG)數據庫,進行相關代謝通路分析。
1.5 總RNA 提取、文庫構建、測序及轉錄本組裝
使用RNAprep Pure Plant Plus Kit(TIANGEN,DP441)提取樣品總RNA,使用NanoPhotometer spectrophotometer、Qubit 和Aglient 2100分別檢測 RNA 樣品的純度、濃度,通過1%瓊脂糖凝膠電泳(80 V)檢測樣品 RNA 的完整性和污染性。構建測序文庫采用 Illumina 試劑盒(NEBNext UltraTM RNA Library Prep Kit);AMPure XP beads純化文庫片段,最終獲得文庫;文庫構建完成后,使用生物分析儀(Agilent 2100)和熒光計(Qubit 2.0)進行文庫檢測,Q-PCR對文庫有效濃度進行檢測,以確保文庫質量合格。將不同文庫按照有效濃度及目標下機數據量進行pooling,然后進行Illumina測序(由武漢邁維代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使用fastp軟件對原始數據進行過濾得到高質量序列(clean reads)。過濾標準如下:(1)剔除帶接頭(adapter)的reads;(2)當任一測序reads中N含量超過該reads堿基數的10%時,去除此paired reads;(3)當任一測序reads中含有的低質量(Q≤20)堿基數超過該條reads堿基數的50%時,去除此paired reads。獲得的clean reads使用Trinity軟件進行拼接,得到轉錄本序列,使用Corset對組裝得到的轉錄本進行聚類去冗余獲得Unigenes。并進一步使用HMMER軟件與功能數據庫比對,獲得Unigene的注釋信息。
1.6 差異基因分析
以每千個堿基的轉錄每百萬映射讀取的fragments(FPKM)作為衡量基因表達水平的指標,對基因長度與測序深度進行歸一化處理。采用DESeq軟件進行樣品組間的差異表達分析。使用Benjamini-Hochberg方法校正P值,得到錯誤發現率(FDR)。差異基因(DEGs)的篩選條件為 | log2FC |≥1,且FDR<0.05 [21]。獲得差異基因后進行KEGG注釋和富集分析。
1.7 轉錄組與代謝組聯合分析
根據差異基因以及差異代謝物的共同KEGG富集分析結果,找到兩組學富集到共同KEGG通路的基因和代謝物。利用R中的cor函數計算通路中差異基因和差異代謝物的皮爾遜相關性系數,相關性顯著條件為皮爾遜相關系數>0.80且P<0.05,利用Cytoscape做相關性網絡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代謝組分析
利用UPLC-ESI-MS/MS對葉片(mL)和果實(mF)的代謝組進行分析,檢測到1 292種化合物,聚類為12類。其中黃酮類化合物最豐富,占總量的20.36%,酚酸類含量第二,占17.88%。此外,脂類、氨基酸及其衍生物、有機酸類、生物堿類、核苷酸及其衍生物、木質素和香豆素、萜類的豐度分別為11.69%、8.98%、7.51%、7.28%、5.50%、5.26%、4.26%(圖1)。主成分分析( PCA)結果表明,葉片(mL)和果實(mF)代謝物數據在PC1維度上存在明顯差異(48.3%),在PC2維度上存在差異(18.59%)(圖2)。OPLS-DA模型分析中R2X=0.659、R2Y=1、Q2=0.943,表示模型穩定可靠,Q2=0.943>0.9表明模型為出色模型,認為兩組分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圖3)。PCA和OPLS-DA分析結果說明八角不同組織次生代謝產物的累積有明顯差異。
2.2 差異代謝物分析
比較組間的差異累積代謝物(DAMs)是根據VIP≥1和FC≥2或FC≤0.5的可變重要性來確定的。在葉片與果實的比較中,共積累了571個代謝物的差異積累(331個上調,240個下調)。在這些DAMs中,黃酮類、酚酸類、氨基酸及其衍生物和脂類占比很大(圖4)。KEGG富集分析發現DAMs富集于88條通路,其中富集最明顯的KEGG通路為硫代葡萄糖苷生物合成通路,亞油酸代謝通路,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謝通路,黃酮類生物合成通路,2-氧代羧酸代謝通路(圖5)。參與形成黃酮類化合物的通路主要為苯丙烷生物合成通路(ko00940)、黃酮類生物合成通路(ko00941)、黃酮和黃酮醇的生物合成通路(ko00944)和異黃酮生物合成通路(ko00943),分別富集到12、18、11、5個DAMs。
2.3 轉錄組分析
剔除低質量序列后,在八角葉片(tL)和果實(tF)中獲得了41.04 Gb的clean data。各樣本Q30堿基占91.37%及以上,GC平均含量為46.89%,說明轉錄組測序數據有較高的質量(表1)。對Clean reads進行組裝并聚類去冗余后得到Unigene,將Unigene 與KEGG、NR、SwissProt、GO、KOG、TrEMBL、Pfam數據庫比對,其中與NR數據庫顯著匹配的Unigene占總數的89.9%,比例最高,其次是GO(79.8%)。這表明本研究所得到的轉錄組測序數據是可信的,可用于接下來的數據分析。
2.4 差異表達基因分析
在葉片和果實比較中共檢測到4 506個DEGs,其中2 035個上調,2 471個下調。從聚類分析熱圖可以看出,DEGs聚為2組(圖6),表明八角葉片的基因表達譜與果實基因表達譜有明顯差異。KEGG分析結果顯示,DEGs主要分為細胞過程、環境信息處理、遺傳信息處理、新陳代謝和生物系統五大類,DEGs中富集最明顯的KEGG通路為光合作用通路、代謝通路、光合作用-天線蛋白通路、次生代謝物的生物合成通路、卟啉和葉綠素代謝通路(圖7)。參與形成黃酮類化合物的通路共富集到132個與黃酮合成相關的差異基因,其中苯丙烷、黃酮類、黃酮和黃酮醇和異黃酮生物合成通路分別富集到76、46、6、4個DEGs。
2.5 轉錄組與代謝組聯合分析
基于DAMs和DEGs共同的KEGG通路富集分析,共有39個DAMs和105個DEGs富集在與黃酮類成分生物合成相關的4條通路中。根據差異代謝物、差異基因、共同KEGG通路富集分析結果,篩選得到25個代謝物和33個基因,將這些代謝物和基因進行相關性分析,選擇皮爾遜相關系數>0.80且P<0.05作為相關性顯著條件,結果表明,有26個基因與25個代謝物顯著相關(圖8),說明這些基因參與調控黃酮類化合物的生物合成。
2.6 八角黃酮類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徑分析
目前,有關八角黃酮類生物合成相關基因未見報道,而其他物種如擬南芥、玉米和銀杏等植物的黃酮類生物合成途徑已經被闡述得較為清晰。根據轉錄組與代謝組聯合分析和植物的黃酮類化合物合成途徑研究,預測八角黃酮類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徑(圖9)。在八角黃酮類化合物成途徑中,苯丙氨酸在苯丙氨酸酶(PAL)、肉桂酸4-羥化酶(C4H)及4-香豆酰輔酶A連接酶(4CL)等的作用下形成黃酮類化合物的底物香豆酰輔酶A。香豆酰輔酶A進一步在查爾酮合酶(CHS)的作用下形成柚皮素、根皮素和異甘草素,然后分別由查爾酮異構酶(CHI)、柚皮素經黃烷酮3-羥化酶(F3H)、類黃酮3′-羥化酶(F3′H)和類黃酮3′,5′-羥化酶(F3′5′H)等酶作用生成黃酮類化合物。
柚皮素是一種重要的黃酮代謝中間產物,參與其他黃酮類成分的合成途徑[22],其含量在果中高于葉,為上調代謝物(表2),參與合成柚皮素的上游酶基因C4H、CHS和CHI均為上調基因,4CL的總體表達量趨于上調(表3)。柚皮素在上調酶基因F3′H和F3′5′H的催化下形成上調代謝物圣草酚;在上調酶基因F3H、F3′H和F3′5′H的催化下形成上調代謝物二氫槲皮素;而在黃酮合成酶(FNS)的催化下形成芹菜素和牡荊素等下調代謝物。八角黃酮類生物合成上的大部分差異酶基因均為上調基因,這些基因可能正向調控根皮素、圣草酚、喬松素、柚皮素和紫鉚素等化合物的代謝合成,反向調控芹菜素、牡荊素和三葉豆苷等化合物的代謝合成,因此認為CHS、CHI、F3H、F3′H和F3′5′H在八角黃酮類生物合成途徑中起著重要作用。
3 討論
開展藥用植物中藥用成分如黃酮類成分的生物合成調控研究,對于發掘植物功能基因和揭示其分子調控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黃酮類物質的積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3-24]。本研究聯合轉錄組與代謝組分析八角黃酮類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徑,首次闡釋了八角黃酮類成分的合成途徑和相關基因。
植物中黃酮類化合物的結構多樣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其合成途徑中各合成酶具有不同催化活性和特異性,盡管黃酮類化合物數量大、類型繁多,但其生物合成途徑和相關酶基因相對保守,并已經被闡述得較為清晰。作為黃酮類成分合成途徑上的第1個關鍵酶,CHS催化生成柚皮素查爾酮,并進一步生成各類黃酮類化合物,其表達水平與植物黃酮類化合物含量密切相關[25-26]。CHI是植物中柚皮素查爾酮分子內環化生成柚皮素必需的酶,是黃酮類成分生物合成途徑上的第2個關鍵酶[27-28],CHI過表達可增加擬南芥中黃酮醇的積累[29],并刺激黃芪中芹菜素的積累[30],而在本研究中芹菜素的含量下降,可能為負向調控的結果。F3H基因是黃酮類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徑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基因[31],是整個類黃酮代謝途徑的中樞,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分流節點調控著黃酮醇的形成和花青素苷的積累[32]。在八角黃酮合成途徑(圖9)中,F3H基因催化合成二氫山柰酚,然后在黃酮醇合成酶(FLS)的作用下形成黃酮醇類,如山柰酚、槲皮素,并經過無色花色素還原酶(LAR)等酶的聯合作用合成花色素。F3′H與F3′5′H歸類為細胞色素P450類,類黃酮B環的羥基化由F3′H和F3′5′H 催化完成,二者也屬于黃酮類成分生物合成途徑上的關鍵酶。由于對不同底物的催化活性和偏好性不同,F3′H 與F3′5′H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類黃酮代謝流的導向,是包括黃酮醇在內的植物類黃酮多樣性的重要原因[32-33]。
黃酮類化合物除了在CHS、CHI、F3H、F3′H和F3′5′H的調控下合成,還需要黃酮醇合成酶(FLS)、二氫黃酮醇4-還原酶(DFR)、花青素合成酶(ANS)、花青素還原酶(ANR)、udp-葡萄糖基轉移酶(UGT)以及其他修飾酶在內的一組復雜的多酶體系的幫助。八角黃酮類生物合成的關鍵基因在其生長過程中具有復雜的調控作用,其網絡調控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陳士林,孫永珍,徐 江,等." 本草基因組計劃研究策略[J]. 藥學學報,2010,45(7):807-812.
[2]王媛媛,楊美青. 藥用植物轉錄組的研究進展[J]. 安徽農學通報,2019,25(8):13-15,52.
[3]孟 媛,程 卓,林鋒科,等." 民族藥用植物代謝組學研究進展[J]. 植物資源與環境學報,202 1(2):73-81.
[4]李 慧,馬德志,姜 明,等." 傳統藥用植物轉錄組研究進展[J]. 中醫藥信息,2018,35(6):114-120.
[5]許秋健,李 麗,王松標,等." 代謝組和轉錄組聯合分析果樹生理機制的研究進展[J]. 果樹學報,2020,37(9):1413-1424.
[6]薛守宇,朱 濤,李冰冰,等." 轉錄組和代謝組聯合分析在植物中的應用研究[J]. 山西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42(3):1-13.
[7]Wang S S,Liu L,Mi X Z,et al. Multi-omics analysis to visualize the dynamic roles of defense genes in the response of tea plants to gray blight[J]. The Plant Journal,2021,106(3):862-875.
[8]宋發軍,黃 珍,羅 忠,等." 代謝組學及其在藥用植物研究中的應用[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35(2):36-41.
[9]Yi X Z,Wang X W,Wu L,et al. Integrated analysis of basic helix loop helix transcription factor family and targeted terpenoids reveals candidate AarbHLH genes involved in terpenoid biosynthesis in Artemisia argyi[J].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2022,12:811166.
[10]Chen R,Hu T Y,Wang M,et al.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key polyketide synthases by integrated metabolome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n curcuminoid biosynthesis in Curcuma wenyujin[J]. Synthetic and Systems Biotechnology,2022,7(3):849-861.
[11]劉志強,高 崎,李 航,等." 基于代謝組學和轉錄組學的不同生長年限下銀杏萜類生物合成關鍵基因表達分析[J]. 中草藥,2022,53(4):1138-1147.
[12]匡海學. 中藥化學[M]. 3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
[13]劉一杰,薛永常. 植物黃酮類化合物的研究進展[J]. 中國生物工程雜志,2016,36(9):81-86.
[14]黃河勝,馬傳庚,陳志武. 黃酮類化合物藥理作用研究進展[J]. 中國中藥雜志,2000,25(10):13-16.
[15]馬錦林,張日清,李開祥. 廣西八角良種研究綜述[J]. 經濟林研究,2006,24(3):59-61.
[16]國家藥典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M].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20.
[17]趙秀玲. 八角茴香天然活性成分最新研究進展[J]. 食品工業科技,201 3(19):370-376.
[18]侯振麗,胡愛林,石旭柳,等." 八角茴香的化學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進展[J]. 中藥材,2021,44(8):2008-2017.
[19]Fraga C G,Clowers B H,Moore R J,et al. Signature-discovery approach for sample matching of a nerve-agent precursor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XCMS,and chemometrics[J]. Analytical Chemistry,2010,82(10):4165-4173.
[20]Thévenot E A,Roux A,Xu Y,et al. Analysis of the human adult urinary metabolome variations with age,body mass index,and gender by i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workflow for univariate and OPLS statistical analyses[J].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2015,14(8):3322-3335.
[21]Audic S,Claverie J M. The significance of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J]. Genome Research,1997,7(10):986-995.
[22]張 剛,李軍營,黎旺姐,等." 煙草黃酮類化合物的代謝及其調控機制[J]. 基因組學與應用生物學,2017,36(4):1672-1681.
[23]卜紅宇,韓 峰,郝美玲,等." 藥用植物類黃酮生物合成調控的研究進展[J]. 北方藥學,2021,18(7):192-196.
[24]呂亮雨,段國珍,李發毅,等. 微生物菌劑對枸杞生長及土壤養分的影響[J]. 江蘇農業科學,2023,51(1):168-175.
[25]Koes R E,Quattrocchio F,Mol J N M. The flavonoid biosynthetic pathway in plants:function and evolution[J]. BioEssays,1994,16(2):123-132.
[26]Dick C A,Buenrostro J,Butler T,et al. Arctic mustard flower color polymorphism controlled by petal-specific downregulatio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anthocyanin biosynthetic pathway[J]. PLoS One,2011,6(4):e18230.
[27]Yonekura-Sakakibara K,Higashi Y,Nakabayashi R.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lant flavonoid metabolism[J].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2019,10:943.
[28]Nishihara M,Nakatsuka T,Yamamura S. Flavonoid components and flower color change in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by suppression of chalcone isomerase gene[J]. FEBS Letters,2005,579(27):6074-6078.
[29]Jiang W B,Yin Q G,Wu R R,et al. Role of a chalcone isomerase-like protein in flavonoid biosynthesi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2015,66(22):7165-7179.
[30]Elarabi N I,Abdelhadi A A,Sief-Eldein A G M,et al. Overexpression of chalcone isomerase A gene in Astragalus trigonus for stimulating apigenin[J]. Scientific Reports,2021,11:24176.
[31]Baek M H,Chung B Y,Kim J H,et al. Molecular cloning and characterisation of theflavanone-3-hydroxylase gene from Korean black raspberry[J]. The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2008,83(5):595-602.
[32]Holton T A,Cornish E C. Genetics and biochemistry of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J]. The Plant Cell,1995,7(7):1071-1083.
[33]邢夢云.楊梅FLSs和F3′5′H調控楊梅素生物合成的機制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學,2021.
收稿日期:2023-08-02
基金項目:廣西自然科學基金(編號:2020GXNSFAA238017、2023GXNSFDA026065、2019GXNSFAA245084);廣西壯瑤藥重點實驗室項目(編號:GXZYKF2022-20);廣西中醫藥大學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編號:YCSY2023006);廣西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項目(編號:桂學位〔2021〕6號);廣西高校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編號:S202210600060、S202210600063)。
作者簡介:王乙淋(1999—),女,廣西河池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藥(壯瑤藥)鑒定研究。E-mail:2460228324@qq.com。
通信作者:黃 勇,博士,教授,主要從事中藥資源和分子生藥研究。E-mail:huangyki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