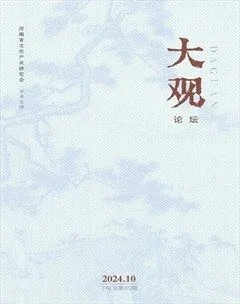北朝民歌《敕勒歌》的音樂特征及演唱技巧研究
摘 要:北朝民歌《敕勒歌》歷經千百余年流傳至今,是敕勒人民留給后世的寶貴文化遺產,同時也是敕勒族由戰亂到安定發展的有力證明。從音樂特征來看,《敕勒歌》的歌詞展現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豁達豪爽,其中所運用的蒙古長調委婉且具有節奏感,展現了北方民族的文化氣節與真摯情感。從演唱技巧來看,聲樂作品《敕勒歌》在氣息調節、咬字吐字、襯字潤腔方面靈活應用演唱技巧,更好地通過演唱技巧來實現情感表達,更好地傳遞出《敕勒歌》獨特的民族韻味和音樂感染力。
關鍵詞:北朝民歌;音樂特征;演唱技巧;《敕勒歌》
在千百余年的音樂發展歷程中,北朝民歌《敕勒歌》在當代音樂史上逐漸被傳承下來,其承載著敕勒族豐富的家園文化和歷史記憶,同時也是中華民族融合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早期,《敕勒歌》以鮮卑語傳唱,后被翻譯成漢語記錄于《樂府詩集》中,成為中國文學史上胡漢文化交流的典范。該詩歌憑借其生動描繪的草原風光和深刻的文化內涵,在宋代郭茂倩編纂的《樂府詩集》中占有一席之地[1]。進入現代,詩人薛保勤在保留原詩意境的基礎上,對《敕勒歌》進行了創新性填詞改編,音樂制作人劉洲也參與了作曲編排,使這一古老詩歌煥發新生。與傳統側重自然景觀描寫的《敕勒歌》不同,新版的《敕勒歌》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以一位少女的視角展開,并且在音樂故事中融入了細膩的愛情憧憬,構建起完整的人物故事與情感世界,實現了情景交融,既保留了原作的民族特色,又巧妙結合現代音樂元素,展現了深厚的文化傳承與藝術創新。
一、北朝民歌《敕勒歌》的音樂特征
(一)歌詞特征:北方游牧與南方清爽詩風相結合
《敕勒歌》作為一首北朝民歌,其歌詞在展現北方游牧民族粗獷豪放特質的同時,也融入了一絲南方詩歌的清新與雅致,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特別是歌詞通過少女的視角,分三個部分進行歌曲的闡述。音樂開篇,以“心隨天地走,意被牛羊牽”引入,勾勒出一幅黃昏牧歸圖。少女的情愫與草原的生靈緊密相連,牛羊的自在映射出草原兒女的灑脫。落日余暉與月升初現的浪漫交替,不僅描繪了草原的壯麗,還借由與月對話的浪漫主義筆觸,傳遞出少女內心的溫柔與憧憬。篝火映紅臉頰,套馬桿下人醉景醉,營造出一種溫馨而又略帶醉意的草原夜晚氛圍。音樂中段的情感進一步深化,少女“心隨天地走”,在追求達觀心境的同時,也暗含對愛情和家園的雙重向往。這段不僅強化了人物的情感層次,還將草原的自然美與人物的內心世界巧妙融合。在音樂的高潮與結尾,通過對原作的復誦,不僅強化了歌曲中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主題,還深刻體現了敕勒族人民的豪邁豁達與對家鄉的深厚感情。陰山腳下,敕勒川的遼闊與天空的壯美相互映襯,展現了“天蒼蒼,野茫茫”的無垠之美;風動草低,牛羊顯現,生動展現了草原的豐饒與生命力,動詞“吹”“低”“見”精練而有力,勾勒出一幅幅動態的草原生活畫卷。可以說,該歌曲的歌詞架構藝術感獨到,始于少女細膩的情感波瀾,拓展至對廣袤自然的崇高禮贊,進而是民族精神的巍然展現,最終以情感的回環往復收束,構建了一個閉合而深邃的主題循環[2]。這一精心布局不僅鞏固了敘述的流暢性與深度,更充分顯示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豁達豪爽,從而形成了一個北方游牧之歌與南方清爽詩風相結合的聲樂作品,彰顯了中華文明包容萬象、各民族文化異彩紛呈而又和諧統一的深厚文化底蘊。
(二)旋律特征:蒙古長調委婉且具有節奏感
《敕勒歌》在旋律上的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是北朝民歌的典型代表,更在于它如何巧妙地將蒙古長調這一傳統音樂元素融入其中,展現出一種跨越時空的文化交融與藝術創新。蒙古長調,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瑰寶,旋律線條悠長、情感表達深邃,集中體現著蒙古族人民對于自然的敬畏、生活的熱愛以及歷史的追憶。《敕勒歌》是一首帶有襯詞誦讀的二段體宮調式歌曲,其旋律雄壯激越,剛勁有力,表達了敕勒人民的民族情懷[3]。而“諾古拉”作為蒙古長調的靈魂,是一種高度技巧化的裝飾音與滑音處理方式,通過對單一音符的豐富變化,能夠在音樂作品中營造出一種音樂上的“微雕藝術”。這種技法要求演唱者具備極高的音樂感知力和控制力,能夠在保持旋律流暢的同時,通過細微的聲音波動和音色轉換,模擬草原上風的輕吟、馬的嘶鳴、河流的潺潺,以及牧民心緒的起伏,從而讓每一個音符都飽含深意,每一句歌詞都仿佛在訴說著古老而又生動的故事。特別是在《敕勒歌》的尾聲部分,蒙古長調的融入尤為顯著,它不僅增強了作品的地域色彩,更深化了歌曲所傳達的游牧文化精髓。演唱者在演唱《敕勒歌》的時候,可以通過真假聲的自如切換,以及對口腔、喉嚨各部位的精準控制,創造出既婉轉悠長又富含節奏感的旋律線條。這種獨特的音樂表達能夠更好地增強音樂作品的節奏感,讓聽者感受到游牧民族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
(三)情感特征:展現民族文化氣節與真摯情感
《敕勒歌》作為北朝時期一首極具代表性的民歌,不僅是音樂藝術的瑰寶,更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氣節與真摯情感的深刻映照。首先,這首歌曲以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綿延悠長的曲調,生動展現了敕勒地區廣袤草原上人民的生活畫卷,成為多樣性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其音樂特征不僅僅是調式的雄渾與氣息的深遠,更是北方游牧民族豪放性格與深沉情感的直接流露,是對大自然的崇敬、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未來的希冀的綜合體現。其次,作為多民族文化交匯融合的產物,《敕勒歌》承載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它不僅是民族音樂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認同與精神傳承的有力見證。歌曲中蘊含的真摯與壯美,激發了后人無數次的改編與再創作。這既是對其藝術價值的高度認可,又是對傳統文化血脈延續的實踐。每一次的重新演繹,都是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將這份古老的文化遺產融入現代語境,使之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促進不同音樂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鑒。可以說,《敕勒歌》的藝術魅力,不僅體現在它明朗豪邁的風格、開闊的境界以及雄壯的音調上,更在于其直抵人心的詩歌語言,不需要過多修飾便能觸動人心。自古以來,這首歌曲就得到了文人墨客及文學評論家們的高度評價,被視為民族音樂與文學結合的典范,其純真的情感表達與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跨越時空界限,引領聽者穿越至那片遼闊的草原,感受游牧民族的堅韌與浪漫,繼而將這份獨特的文化體驗帶向全世界,促進全球文化的多元共融與創新發展。
二、北朝民歌《敕勒歌》的演唱技巧
(一)氣息調節:正確呼吸保持穩定節奏
在聲樂藝術中,氣息的掌握被視為歌唱技巧的核心,聲樂教育家沈湘要求學生把聲音的力量放在橫膈膜上,輕聲地唱高音,這其實是半聲唱法。半聲唱法的訓練,必須結合哼鳴、氣息、混合聲等多個方面的技術,其中最重要的是學會控制氣息和嗓音的“比例”[4]。這也揭示了氣息運用在聲樂演唱中的基礎地位。要實現歌聲的流暢與自然,演唱者需要掌握恰當的呼吸技法,并能精準控制氣息。其中,維持氣息的均勻與穩定,是確保旋律連貫與維持聲音動力的基礎,特別是在演唱“心隨天地走”歌詞時,演唱者要細致拿捏氣息,使之柔和,保證樂句間的順暢,尤其在弱起的“心”字上,更應采用敘述式的溫柔表達,避免過分強調。在演唱歌曲的高潮段落,例如“敕勒川,陰山下”時,演唱者要在吸入充沛氣息的同時,通過腰部力量的參與來穩固發聲,確保聲音的飽滿與穩定。此過程中,演唱者需警惕氣息因音高的攀升而產生的不自覺上升趨勢,而且要學會在氣息運用上采取一種逆向思維,即在意識中尋找氣息下沉的“嘆息”感受。演唱者在演唱“天蒼蒼,野茫茫”中的“野”字時,要在吸氣后將氣息沉穩地置于下腹部,同時全面打開內口腔,為高質量的發聲做準備。至于全曲的高潮中的最高音“啊”的處理,除了確保深吸氣之外,還要留意整個發聲通道的暢通無阻,充分打開口腔、喉嚨乃至鼻腔,構建一個暢通的聲音傳輸路徑。只有精細掌握對呼吸與氣息的控制,演唱者才能在保留歌曲情感真諦的同時,實現聲音的自如駕馭與藝術表現的升華。
(二)咬字吐字:吐字響亮的同時快速收音
在歌唱藝術中,清晰而富有表現力的咬字吐字,是演唱者傳達歌曲意境與情感深度的關鍵。尤其是演繹富含文化底蘊的中國作品,如《敕勒歌》,更需深入探究漢語言的發音精髓,確保每一個音節都準確無誤、生動傳神。在我國,漢語發音的精妙在于字頭的啟動、字腹的展開及字尾的收束,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構建了字正腔圓的美學標準[5]。在演唱這首古風濃郁的歌曲時,演唱者需要反復吟誦,細致研習歌詞的發音規律,使每個字都能在唇齒間流轉自如,達到既響亮又細膩的效果。比如“牽”“圓”“桿”“天”“觀”“川”等字,演唱者要精確拿捏,特別是“圓”字的發音,演唱者要從小口型逐漸過渡到“ɑn”韻的大口型,避免扁平化發音,以免影響聲音的豐滿度。采用“ɑ”母音的口腔開闊感來輔助發音,可在吐字時賦予聲音更多的空間感與明亮度,而收音則需迅速而柔和地歸于應有的韻部,確保每個音節的清晰與流暢。因此,《敕勒歌》演唱前的首要步驟便是深入朗讀歌詞,通過不斷練習,體會并內化每個字的發音特點與韻律美感。只有這樣,演唱者才能在演唱時做到吐字既準確又充滿感情,使每個音符都飽含深意,真正實現語言與音樂的和諧統一。
(三)襯字潤腔:以聲傳情表達歌曲情感
在《敕勒歌》這樣的民族風格濃郁的曲目中,諸如“哎”“啊”“哈”之類的襯詞不僅豐富了音樂語言,更是情感流露的直接載體。尤其是尾聲部分的“啊”字,作為開口音,其易于展現飽滿與圓潤,雖無實義卻承載了樂曲的情感精髓。在演唱“啊”時,演唱者需要細膩捕捉音高變化的強弱對比,特別是當音樂從悠揚的中聲區開始,攀至激昂的高音區后再緩緩回歸,音域跨越八度。這一過程不僅增強了旋律的層次感,還深刻描繪出蒼茫大地與遼闊天空的壯麗景象。中低音區的沉穩與高音區的激昂形成強烈對比,映照出草原兒女內心的細膩情感與對故土深沉的愛戀。演唱者在演唱中,要確保“啊”字在不同音高與力度間過渡自然,通過細膩的強弱處理,展現草原人民內心細膩的柔情與豪邁的熱情,實現聲與情的完美交融,達到藝術表現的至高境界。此外,《敕勒歌》大部分旋律落于女高音的舒適區間,但引子后的部分則涉及中低聲區的靈活轉換,要求演唱者在不同區域保持音色的統一與流暢。在低音區,聲音需依托胸腔共鳴,運用真聲自然發聲,避免過度用力。如“心隨天地走,意被牛羊牽”的結尾部分,應憑借平穩的氣息支持,讓聲音輕松流出。轉至高音區時,要增加頭腔共鳴的運用,使聲音更為集中。這就要求演唱者提前準備,實現呼吸、發聲與共鳴三者間的協調一致,以此來確保高中低聲區的無縫對接與音色的和諧統一[6]。可以說,襯字的演唱,能夠更好地讓演唱者在歌唱的過程中以聲傳情、以情帶聲,準確表達歌曲的情感,以達到人歌合一的境界。
三、結語
北朝民歌《敕勒歌》作為中華民族音樂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不僅以獨特的音樂魅力穿越千年時空,見證了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廣闊與豪邁,而且在當代文化語境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從《敕勒歌》的歌詞、旋律、情感特征來看,該音樂作品營造出北方游牧與南方清爽詩風相結合的音樂風格,運用了委婉且具有節奏感的蒙古長調,展現出民族文化氣節與真摯情感。從《敕勒歌》的演唱技巧來看,演唱者要重視氣息調節、咬字吐字、襯字潤腔等方面的技巧應用,從而在歌曲演唱的過程中實現聲樂作品與情感的深度融合,展現歌曲深厚的藝術底蘊。可以說,演唱者對《敕勒歌》音樂特征與演唱技巧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在音樂演唱的過程中展現音樂魅力,傳承中華民族音樂文化。
參考文獻:
[1]原新萍.北朝民歌《敕勒歌》的演唱分析[J].黃河之聲,2023(20):146-149.
[2]張家榕.歌曲《敕勒歌》的藝術特征[J].藝術家,2023(10):51-53.
[3]特日格力.聲樂歌曲《敕勒歌》藝術特征及演唱技巧[J].藝術大觀,2023(15):35-37.
[4]馬麗娜.沈湘聲樂教學藝術對當代聲樂表演與教學的啟示:評《沈湘聲樂教學藝術》[J].中國教育學刊,2023(5):139.
[5]李佳峰.北朝民歌《敕勒歌》的藝術探究[J].藝術家,2023(3):75-77.
[6]李夏琳.古詩詞改編聲樂作品《敕勒歌》創作分析[J].戲劇之家,2023(19):74-76.
作者單位:
沈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