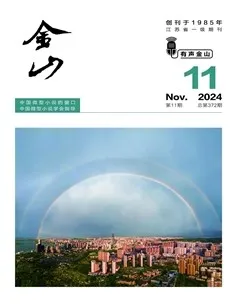耬癡
耬,農具名,又叫耬子、耬車、耩子。由耬腿、耬斗、機架組成,牲畜在前牽引,人在后邊扶持,開溝,播種。
早年,農村用耬耩地。把耬耩地是技術,是手藝,更是絕活。耩得好,苗齊苗壯,趕上一場透雨,噌噌往上躥。耩得賴,缺苗斷壟,像山羊啃過的墳頭草,賴在那里不長個。澤武耩地耩得好,背地里人們喊他“耬把式”,還得綽號“耬癡”。
澤武耩地向來不用別人家的耬,這些年下來,家里的耬有十幾架。農閑時,澤武拿塊抹布,擦拭這個,擦拭那個,不讓老伙計們沾一丁點土星。
木材市場,澤武尋得百年槐木,花大價錢買下,請當地有名的木匠,打制一架新耬。澤武花了錢,老伴心疼,肺疼,恨得牙根兒疼,氣得鼻子都歪了,蹾葫蘆摔馬勺,氣咻咻地說:“死了,你也舍不得買那么好的棺材板。”老伴沖著院里一口大缸努努嘴,說,“到時候把你裝到大缸里埋了。”澤武只一句:“耬好,地才耩得順溜。”別看澤武平時一分錢看得比磨盤大,三錐子攮不出一滴血,身上的褂子都飛起毛邊,露著白線頭,可花錢打造新耬,那可是連眼皮都不眨一下。
烏云壓頂,悶雷滾過,大雨傾盆而下。屋里漏成水簾洞,盆盆罐罐擺了一地。雨滴敲打出叮叮咚咚的交響樂。老伴找不到澤武,急得要上房,沖院里大喊:“澤武——澤武——你死到哪兒去了?”人家澤武也沒閑著,爬到柴棚子上苫蓋塑料布去了。那十幾架耬就放在里邊,那可是澤武的寶貝。澤武淋了雨,腦門燙手,打噴嚏,在被窩里縮成一團。老伴端水送藥,埋怨說:“澤武,以后你去柴棚子里摟著你的耬睡吧。”
后生請澤武去耩地,搬起耬往馬車上一蹾。這下,澤武可不干了,訓斥:“粗手重腳的,能不能穩當點啊?”接著,又給后生上起課來,“好幾斤糧食換一斤種子,把耬摔壞了咋弄?地耩不好,浪費種子不說,長出的苗像禿瘡疙疤一樣。秋后,人家收十成年,裝滿大車小輛,你收六七成年,幾個塑料袋背回家,豈不誤了年景?”后生臉紅得像開水煮過的蟹,武爺武爺的賠不是,澤武才消下氣來。心想:你不尊重耬就是不尊重我澤武。
常言說:“家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在身。”澤武靠耩地的手藝吃香喝辣,在街里走路,挺胸,抬頭,倒剪著手。村里人請澤武去耩地,掏出平時舍不得抽的煙,拿出平時舍不得喝的酒,送給他。村巷里彌漫的肉味,一準是從澤武家飄出來的。
澤武家的日子過成村民眼里的風景,眼饞的娘們兒背地里嚼舌:“你看人家澤武婆娘,吃得像個水桶,屁溝子流油。”
一晃幾十年。
澤武跟兒子進城,整天,手里沒抓沒撓的。聽說廣場那邊有個展覽館,跑了去。澤武往玻璃展柜里瞅,看著那微縮的農具模型,眼睛像添了油的燈,瞬間明亮起來,彎下去的腰也直了起來。把耬耩地的風光,仿佛一下子又回來了。看著看著,澤武背過臉,一個大老爺們哭得稀里嘩啦。
澤武搖耬耩地的癮犯了,像被蚊蟲叮咬過,癢癢的。他想回老家一趟,去看看他的老伙計們。夜里,睡得正香。突然,老伴大喊:“澤武,你干嘛呢!”這一嗓子把澤武吼醒了。澤武磕磕巴巴地說:“我……我……”卻原來,澤武半夜夢到耩地,迷迷糊糊地雙手拽住老伴的兩只胳膊,就像把住兩個耬把一樣,左搖右晃地耩起地來。
天蒙蒙亮,澤武朝河邊走去。瞅瞅,四下沒人,扭起秧歌。細瞅,總覺得那秧歌扭得怪怪的。再看,澤武微蹲,腰略彎,雙手放在腹前兩側,掌心向上攥拳,左右左右地搖晃,那秧歌分明扭出了把耬耩地的架勢。
好一個耬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