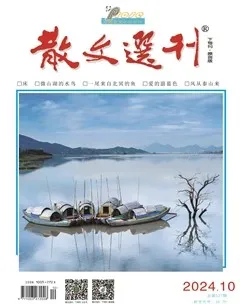憂郁的章弘

章弘來到巨野任知縣的第二年,即1701 年,便奉旨修金山。
金山是西施曾經養蠶浣紗織錦的地方,是大野澤和菏澤唯一的山,再賦以優美的傳說,在百姓眼里相當神圣!章弘按泰山格局來修,從西而入,有小紅門、中天門、小天街、南天門,北面還有泰山祠、王母閣,另外還有文昌閣、三圣殿、魁星樓、牛王廟、戲樓、玉兔洞、圣母泉等景觀,皆是依山布置,起伏有致。一俟修成,游客、商賈、官宦便慕名而來,朝拜的、祈愿的、觀光的絡繹不絕,把滿山的動物植物都攪熱了。只是那個秦王避暑洞,章弘研究了好久,依然不得其法。
1702 年,章弘瞄上了巨野縣城東南隅的文廟,這座始建于宋代,在明代洪武十五年由縣丞呂讓搬遷到現址的先師之居,在章弘手里,正殿金碧輝煌,廊柱石龍盤繞,殿堂樓閣齋亭廡坊近百間,諸祠皆備,這占地三十余畝的五進院落從此成為儒學所在。章弘興致勃勃地看著工匠在正殿的石柱上刻下幾個大字——“宣議郎巨野縣事宛平章弘重建”,已45 歲的他,站在文廟里,撫髯而笑,覺得自己未辜負圣賢書。
1703 年,章弘協助朝廷派來的官員在山東境內救災,大雪和洪澇導致山東顆粒無收,個別地方都有了人吃人的現象,章弘心有所慮,為此辛勞奔波,很快災情平息,迎來了豐稔人歡。
1707 年,章弘主持修纂《巨野縣志》,一年后,又增修。
章弘有一日來到了山西河南京城山東的交通要道田家橋邊,卻看到了大橋倒塌,看到了行人提衣過河的苦楚,一問,這橋竟然損壞于他出生的那一年,長嘆一聲,他捐出自己的俸祿,招募工匠,重修田家橋。十三拱的大橋落成后,舉人李嗣沆把此事刻在一座石碑上,贊嘆章公高尚的品德。
之后,章弘做了許多事情,直到離開這一天。他不知道的是,巨野人因為他的離開,刻下了一塊石碑紀念他,并把這塊石碑存放在文廟里。
康熙五十四年,朝中九子奪嫡事件愈演愈烈,康熙朝的儲位之爭暴露出皇權制度的種種弊端,但這并不會影響遙遠的山西兩位知州的換防。
章弘來到應州任知州,就喜歡上了這里。戰國時,應州是趙國的地盤。五代時,沙陀族在此筑金城,以此為基,后來發展出一個后唐王朝。遼代時,遼興宗皇后蕭撻里主持修建了佛宮寺釋迦塔(即應縣木塔)。桑干河流經北京后就成了永定河,章弘是知道的。遍地蜿蜒的河流,總是讓章弘想到大野澤,深厚的邊塞文化讓他沉迷,治理的宏愿升騰到眉間心上。于是,每條河流、每座山丘、每處建筑以及麥黍之間,都留下了他匆匆的腳步:應州署得修吧,不然在哪里辦公?書院得修,讀書人怎能沒個去處?察院行臺作用不大,改建為義學吧。廣盈倉得修得擴,不然沒有儲糧之地,災荒年怎么辦?文昌祠也得修,文運興盛,是一地的長遠打算。玄武廟也得修,民眾要有安放俗世愿望的地方……
最最關鍵的是木塔得修。章弘捐出自己俸祿便罷了,還曉諭民眾“凡登塔者,或提磚一塊,或持瓦一片,各給錢一文,一時白叟黃童接踵踴躍,搬運如飛,皆不受錢,而磚瓦堆積如山,應用不竭”。章弘說,自己已經65 歲了,本來是有腳疼的毛病的,誰知開修木塔之后就不再發病了,修塔之后,應州政和年豐,人民安泰,定是神靈護佑。
章弘把這些事寫成《修塔紀事》,并認認真真地鈐印,藏于木塔第五層內槽。這一年,是康熙六十一年。
這一年,康熙帝于十一月十三日駕崩,而章弘于這一年修好木塔后,執政應州七年多,迎來了自己的人生轉折。
大面積重修木塔以及在應州城里的大興土木,涉及一些必要的錢糧攤派,這就損傷了一些士紳和富戶的利益,鄉閭之間一時輿情四起,給章弘安上了各種名頭,一紙訴狀把章弘告到了朝廷。康熙剛死雍正即位,正是亂糟糟的時刻,朝廷把章弘調到綏遠歸化任職。章弘臨去時,66 歲的他,流連在應州的街頭,悲憤難抑,留下一首絕命詩:三山九出頭,二水繞城流。富貴無三輩,清官不到頭。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呀,應州人的行為傷透了一腔熱血的章弘,他在走出應州地界后,便自縊身亡了。從此,這樣一個為“文化遺產”做出重要貢獻的官員,永遠地消失于歷史之悠悠大野。
章弘死后,來繼任的是廣東順德貢生蕭綱。蕭綱也曾嚴查章弘的經濟問題,但無非是建設項目多、費用高、不合理等等,并無貪贓枉法。蕭綱刻《奉巡撫都察院諾大老爺批行禁革陋規碑》,禁止了一些陋規,不再攤派,但也把章弘留下的工程做完了。人們把木塔上懸掛的章弘刻下的牌匾“萬古觀瞻”的落款抹去了,應州舊志也消除了章弘的許多痕跡。
章弘死去三百多年后,專家破解了巨野的秦王避暑洞之謎,那本來是昌邑王劉賀的墓葬,只因改封海昏侯,這個半拉子工程就永久地留在了金山,隱匿在佛之崇拜背后,人們世世代代來供奉香火,沒人知道劉賀是誰了,也不知道章弘曾在這里仔細打量。
章弘死去三百多年后的朔州(應州后稱應縣,隸屬朔州),把章弘定位為一個貪官壞官,把他傳為“吊死鬼”,還說他是白身為官,與巨野對他的推崇形成兩種相反的現象。
而悠悠大野中,分明能看到章弘憂郁的雙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