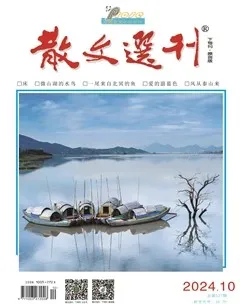河流的照耀
說是遠行,其實是父親帶著我,劃著小木船,到離家不足十公里的小集鎮去購買篾制的漁具。
父親劃著槳,我坐在與船頭相鄰的或左或右的船舷上,左邊右邊地看著水里的景致。魚兒游啊游的,水草飄啊飄的,云朵在行走中不停地變換著各種各樣的形態直至消散。那時的我一度以為,云朵是水里的事物。還有那些宛若精靈的漣漪,用不大不小的動靜,牽引著我充滿新鮮感的目光。我看到了河流兩岸的樹木,樹木里時隱時現的村落。
一年又一年,陰晴流轉中,父親走遠了,小木船也消失了。可河流還在。河流泛起的水光在記憶里似乎未曾衰老抑或凋零。
常常回憶起早年的夏夜,在河流之上的小橋之上,寡言寡語的我,凝視著靜月下的波光粼粼,半生不熟地拉二胡。拉的曲目多是與水有關,《二泉映月》《江河水》……那也算得上是一種忘我的境界,直到心中漾起波瀾。如今,那座小橋也被拆掉了。可河流還在。河流一直都在不舍晝夜地默默流淌著。
這條河流,叫城南河。
城南河,也許名不見經傳,但它一定是我最親最美最寬闊的河流。我一直認為,河流對于關乎生命的影響是潛在的,同時又是巨大的,哪怕被人們遺忘的時候。好在我那時也留下過一點點兒與城南河這條真正意義上的母親河有關的文字,否則我會罵自己是一個混蛋。我在一首題為《城南河》的詩中寫道:“城南河——我家鄉的河,綻開一朵朵童稚的笑靨。你從我記憶的峽谷里流出,又在我沉思的曲徑上漫過……”這首詩,反反復復,被我改得面目全非,可最終還是沒能定稿。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放棄了對這首詩的繼續修改,或許是因為我的閱歷淺,沒有河水那么深。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有意識地去探究城南河的源頭到底在哪里。隨著我生活幅面的逐步擴大,在一片水光的映照下,我的目光有了更多需要依靠以及追尋的渴望。就像我逐漸了解到的那樣,長江的源頭在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側的沱沱河,漢江的源頭在陜西省漢中市寧強縣,是長江的最大支流。這是不是可以說,城南河就是長江支流的分叉呢?
我開始注意到漢江,并迅速地將其司空見慣,因為它就在我的身邊,同時對我身處的江漢平原有了更深層面的認識。
江漢平原是由河間洼地組成的洪泛平原。長江、漢江形成主干河間洼地,其支流又分割主干河間洼地形成次級河間洼地。這些洼地就成為湖泊或沼澤,故江漢平原湖泊多數屬于河間洼地湖。河流至湖泊的微地貌依次是天然堤、決口淵塘、決口供積扇、廢棄河道、堤內低漫灘、河間沼澤地、河間洼地湖等。我生活的周圍或者地域,湖多,口多,灘多,也就是說水多。更多的時候,我會選擇某一種方式去由衷地贊美它。我在歌曲《春天的故鄉》里寫道:“荊風爽,楚水長,江漢平原有個好地方。捧一把泥土香如酒,插一把筷子它也滋滋地長。若是你到這里來,你就像到了水鄉天堂……”
我是懷著一顆敬畏之心走近江漢的。其實,它讓我有了放大的故鄉這樣一個概念。什么叫流域?這是一個多么深厚、多么寬廣的詞語啊!從城南河流域,再到漢江流域,再到長江流域,其實是一脈相承,同源共生。所以我每次跨越長江,都有一種穩穩當當的親近感。其實,漢江早已設置或者安排好了作為它的子民的我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氛圍。只要走出去,風光處處在。漢江有數不清的小溪小河,澆灌著漢江兩岸的良田。每年夏秋季節,常有洪水暴漲,此時的漢江,江面有數里寬,浩浩蕩蕩,蔚為壯觀。而一到冬春季,江水一下子小了幾十倍,不但兩岸裸露出了寬闊的沙灘,就連江心也露出大塊大塊的江心島。兩岸村民把它們不叫島而叫灘。于是,漢江灘成了江漢平原一個特殊的標記。這些灘只高出水面一兩尺,最高的也不過三尺。灘面積大小不等,小的只有幾分幾畝,大的竟有上百畝。灘的位置隨著江水的沖刷淤積而一年一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飄移不定。由于這些灘是由腐殖質和熟土堆積而成的,所以非常肥沃。肥沃的土地適于播種。那高一些的灘地,開春之后可以播一茬兒花生。漢江灘上的花生殼薄仁大,堪稱一絕。除了花生,還有黃豆、小麥、芝麻……漢江灘,顯然是一幅綠色的畫廊。
最終,我還是回到長江上。長江,長江的支流以及支流的支流,水光中的記憶,承載著我所有的疼痛與歡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