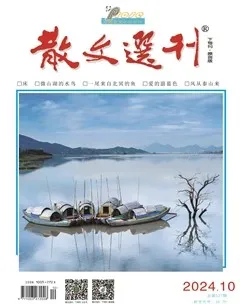讀年
那年冬天,放寒假了。
經(jīng)常聽到父母偷偷盤算事兒:“快年根了,老大的褲子不能再穿了,老二的棉襖得換棉花了,老三個子長了、褲腿短,得買新的了。還得買幾斤魚、肉吧……”聽著這樣的絮叨,感覺家里用錢的地方多著呢。可,莊戶人家哪有什么積蓄?最后,父母商定把埋在南墻根下雪地里的香菜拉到城里賣了,來置辦年貨。
臘月二十六晚上,父親趕集回來,接著裝滿一平板車香菜去濟(jì)南賣。由于路途近百里遠(yuǎn),擔(dān)心父親一人拉車太累,我又是長子,就上蹦下跳著、毛遂自薦與父親同去。
父親上下打量了下我這個半大小子,也沒有說什么話。母親給我爺倆下了一鍋熱騰騰的面條,嘮叨著進(jìn)城里賣菜嘴要甜、架子要活泛,別虧了肚子。爺倆兒每人三碗面條下肚后,整裝出發(fā)。結(jié)伴同行的還有胡同里的我大舅、小舅,他兄弟倆也拉著一車菜盼望能賣個好價錢。在那個年代,雖說是拉車徒步進(jìn)城,但也并沒覺得多苦,總感覺大年三十前進(jìn)濟(jì)南是一種生活儀式、是繞不過去的;也頗有帶著希冀去戰(zhàn)斗的意味——殊不知,這是一場因音訊不通而輸不起的“賭”。
晚上七點(diǎn)多,兩輛地排車像拉著一座小山,一前一后地出了村頭。這是我有生以來首次進(jìn)濟(jì)南府,心里還想著終于可以看看“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了。百里之行,之于我雖說是一場毅力與體力的磨煉,但倍感欣悅,腳步邁得也特輕盈。“我有勁兒吧?!”一路上我駕轅當(dāng)主力,與父親說笑著,不覺間到了龍山大橋。刺骨的寒風(fēng),無法阻擋我們周身洋溢的熱情,汗水在棉襖、棉褲與肌膚大面積的親密粘貼,一會兒就變得冰涼起來,渾身不自在。
歇息了一袋煙的工夫,父親磕掉了煙袋鍋里還帶點(diǎn)兒小火星的余灰,“還有一半的路就到濟(jì)南了,你在一邊拉繩,我在中間駕轅!”“為啥要換位?!”“這一路上我?guī)缀鯖]使勁兒,是你拉著車跑,后來就感覺你的勁不如剛開始的時候大了!”想想已浸汗被風(fēng)吹涼、緊貼在身上的棉衣,我就到邊上拉車。為了能使上勁兒,證明體力還行,我就把拉繩纏在自己穿著棉襖的左前胳膊上,繞過肩膀把繩拉得直直的,車輪“吱吱”歡笑著吻過腳下每一寸黑亮亮的路面,慢慢向前翻滾著。
漆黑的夜空里,除了星星從四面八方擠著眼注視我們外,蒼茫間,只剩下四人步調(diào)不一的“噗噗”腳步聲。間或有小吉普車顛晃著大燈,“嘀”的一聲,從身邊駛過,眼前的光亮在閃暖小臉面的同時,瞬間灑向身后,留下眼前片刻的黝黑;也有從身后趕超過來的車輛,遠(yuǎn)遠(yuǎn)地就把我們收攏在漸亮的光束中,儼然戲中的主角。
第二天早上約九點(diǎn),太陽升到頭頂時,我們來到了王舍人大集。經(jīng)歷了一夜奔波,人困馬乏。父親看看我,拿出綠面的兩角錢讓我去買點(diǎn)兒吃的。我這才感覺肚子在“咕咕”不停地唱歌。
可當(dāng)我抬腿邁步的時候,突然感覺抬起的腳不敢落地了,好像沒有了知覺——不,是腳底板暴露出來,不敢觸地了!是怵了吧?我再試另一只腳,一個樣,也不能邁步走路了,一走就疼,是從腳底沿脊柱瞬間傳到頭頂?shù)哪欠N疼。
這些,被父親看進(jìn)眼里。“他小舅,孩子腳不能走了,你先馱他回家吧,菜,我和他大舅賣!”小舅騎回程備用的自行車,用了不到4 個小時就把我馱回家;而我們拉車用腳丈量這百十里地卻用了近14 個小時,時間的反差詮釋著負(fù)重前行的艱辛。
這都是為著心中的那個年啊!
一天后,我的腳慢慢能動了。我們姊妹仨就常去村西頭看父親回來沒,又過了兩天,終于在大年初一下午,一夜未眠、眼睛有些紅腫的母親帶我們再次來到村頭時,正好看到由遠(yuǎn)及近拉著車、拖著疲憊身子緩緩走來的父親和大舅。他倆一臉灰土、面無表情。父親低著頭自言自語:“年三十中午就開始返程了……”我向車上看看,用草苫和破棉被蓋著、還未賣出的香菜足有半車多……
父親這年根兒的一賭,直讓我心頭憋悶,莫名的淚在眼眶里打轉(zhuǎn)轉(zhuǎn);也是這一賭,讓我猛然讀出了那段時光中之于我、之于我家的過年的滋味,更讀出了父親在那個年代對我的愛……
那年還有七天,我就滿14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