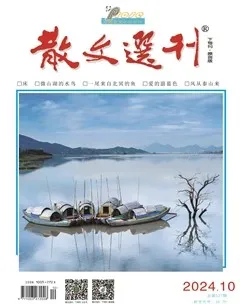九元錢
1962 年,我的老師給我介紹了一個村辦小學去教書,23 歲的我成了山區的一名民辦教師。
那個村莊離我家步行要兩個多小時。于是,我住在村民的家里,村民也是非常善良淳樸的,沒有收我的租金。每個星期天下午,我就帶上一小袋米和一小袋的番薯絲曬的干兒,再加上一個牙杯的咸菜。第二天一直到星期六去給十幾個孩子上課。這個村里當時有十來個孩子需要讀書,但是年齡有大有小,我就按年齡把他們分成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和五年級。所有的孩子就我一個老師,那我就教他們語文、數學。教室也只有一個,就是村里的祠堂。我教一年級的孩子兩個字,讓他們坐在邊上抄寫,然后再安排二年級的孩子做算術題,安排好了之后讓他們做一會兒題目,接著又去給三年級的小朋友講課,講完了之后布置一個作業,然后又去給四、五年級的小朋友安排學習的任務,如此安排,學生也很聽話,沒有搗亂的。因為學生人數很少。一個年級也就三到五個孩子。
我的媽媽幫我帶小孩兒,老三出生了以后,有一次我們鄉村的民辦教師要去區里開會。我就用裹巾(一種古時候農村婦女用來背孩子的長長的布條)背上七個月大的老三,褲兜里塞一些舊被單剪成的尿布,步行走到區里去開會。那個時候開會是有米飯吃的,一個很大的木桶里面裝著白米飯。有一個男老師臉上長滿了絡腮胡,剛剛剃過,那個胡須茬兒又硬又粗,我在打飯的時候,那個男老師擠了進來,動作很快。我還沒來得及退讓,手臂就被他的絡腮胡茬兒給刮傷了一片,紅紅的,生疼生疼。你可以想象為了去打飯,我們有多么擁擠。你甚至無法想象那時候我們對一頓白米飯是多么的渴望。
我住在一戶村民家里的一樓牛欄隔壁的一個房間里,倒是也習慣了農村牛欄豬欄的氣味,因為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有養牛或者養豬。但可怕的是那個年代還有野獸,經常會在夜里出來偷襲家養的豬或者牛。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什么野獸來偷襲村民家的牛,把一只大公牛嚇得跳了起來,因為牛欄的上面蓋著一些稻草,整個牛欄的屋頂都被頂翻。幸好村民聽到動靜就起來把野獸趕走了,可是我從此就嚇得不敢再在牛欄旁邊睡覺了。這一家村民家里人口也比較多,樓上已經沒有空的房間,后來實在沒辦法,主人家就讓我跟她和她的小孩兒一起睡。我就和女主人以及她的孩子睡一張床,當時她家的小孩兒每天晚上都尿床,那時候冬天冷,我就穿著襪子睡覺,早上起來襪子都是濕的,因為被小孩兒給尿濕了。
我一個月只有九塊錢的工資,也不是說上好一個月的課就能拿到工資的,往往要等到年底,然后去學生的家里挨家挨戶地收學費。大部分的學生家長還是很爽快的,但是偶爾也會碰到一兩個家長說三道四,不肯拿錢出來。討來的學生學費,去除書本費之后就是給自己的工資,還要上交一部分給政府。雖然是一名民辦的教師,但也是政府委派的,所以拿多少工資也都是經過政府部門計算的,我不能隨意,不是想要多少工資就去拿多少的。
所幸的是,我從九塊錢一個月,領著領著,工資加到了二十幾塊錢一個月,那時家中有六個小孩兒。工資拿過來不敢去買好的米吃,買最便宜的生了蟲子的米來吃。再過幾年工資漲到了一百多,退休的時候就幾千塊錢了,真是今非昔比呀!
如果我跟現在的年輕人說,那個時候我們一個月教書的工資是九元錢,年輕人會相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