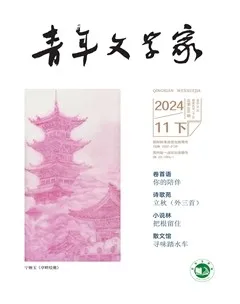童年趣事
對我來說,回憶童年是一種幸福。盡管年代久遠,但是童年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卻怎么也揮之不去,就像在腦海扎下了根,發(fā)出了芽,又開出了花一樣,時刻在我的面前晃動。這些美好而甜蜜的回憶注定要跟隨我的一生,即使到了人生的終點,我也不會忘記,我會把它們帶進另一個世界,這樣在那個陌生的空間里也不會孤單。我想從我的童年回憶里擷取幾朵小花,與大家共享芬芳。
回憶童年是一種幸福
記得看過一本雜志上登的文章,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將軍戎馬一生,聲名顯赫,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對著自己的孩子們說的最后一句話卻是:“我真想回到小時候,再喝一碗恁奶奶做的疙瘩湯,蒸的咸窩窩呀。”
童年的回憶是一種財富。
回憶是一筆我們永遠也花不完用不完的精神財富,包括那些逝去的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久已無法恢復原貌的田園村莊,還有那些無法保鮮的空氣、藍天、童顏、嬉戲—都是多少金錢無法購買和兌現(xiàn)的。在我們孤單的時候,它會給我們以慰藉;在我們得意忘形的時候,它會給我們以警醒;在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它會慰藉我們受傷的心。
童年和回憶總是連在一起。
人的一生不只包括童年,但是回憶的內容卻總是童年的居多。人生好比一張白紙,我們最初的描畫總會留給余生難以磨滅的印記。最初的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所以童年總是和回憶連在一起。一個人的童年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我們的一生,快樂或是悲傷,幸福或是不幸,這段經歷或多或少會影響日后性格的形成和人生觀的確定。我們經歷過童年,已無法改變發(fā)生的一切,但是我們能做到的是給孩子們以怎樣的童年。希望我們的孩子大了的時候,回憶童年感受到的也是一種幸福和快樂。
我跟奶奶撿破爛兒
1977年,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到了當時濟寧的城鄉(xiāng)結合部,也就是現(xiàn)在益民小區(qū)附近。那時候那里還是大片大片的菜地。家里有一畝多菜地,媽媽在地里干活兒,爸爸在附近的濟寧地質勘探隊開車,收入不高,全家的日子并不富裕。當時,我們家屋后不遠就是一個大垃圾場,附近的幾個國營工廠經常往那里運送垃圾。別看是垃圾,對我們這些沒有經濟來源的小家伙們來說,那可是寶貝,那真是“賣水的看見河—都是錢呀”。于是,垃圾場成了我們的聚寶盆。運垃圾的車來的時候,就會有幾十口子人虎視眈眈地把車圍住,車一卸完,呼啦一聲……我們團團圍住,鉤子、鏟子、釘耙,還有手一起上,廢銅爛鐵、紙盒子、廢電線、布條子、碎玻璃……都是寶貝呀!
有時候還會撿到吃的東西。我不敢吃,但奶奶敢吃。有一次,我跟著奶奶去扒破爛兒,她在前頭扒,我在后頭拾。扒著扒著,她就停下了。我一看,她拾起來一塊糖,那糖包著糖紙,糖紙有些臟。她剝開糖紙,是一塊水果糖。“吃!”她遞給我。我不敢吃,直搖頭。“熊孩子……”她一邊說一邊擱進嘴里,還嘟囔著,“不干不凈,吃了沒病。”
最高興的就是賣破爛兒的時候,我們帶著自己的勞動成果,到附近的一個廢品收購站去賣。那時候的廢品收購站還是國營的,一進去,一股子廢銅爛鐵味。收破爛兒的有一個獨臂老人,別看就一只手,可靈便了。賣了破爛兒掙錢了,我們覺得很富有,就買糖吃,那時候覺得最好吃的就是糖,再就是去人民公園爬山看猴子和老虎。
現(xiàn)在,我仍然還有一些破爛兒情結……會過日子,舍不得丟棄破舊物件,這是跟那時候的經歷有關系的吧。
好吃的香油馃子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我最難忘的是童年,因為童年充滿了太多的回憶,太多的歡樂。在我的印象里最深刻的記憶是童年時故鄉(xiāng)的一抹藍天,天是那樣的藍,透明的藍,一眼都望不到底,使人充滿了星際的遐想……現(xiàn)在很難看到這種藍的天了。故鄉(xiāng)還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春天時,如大海波濤翻滾一樣的層層麥浪,在飛舞的春風里此起彼伏,如千軍萬馬,浩浩蕩蕩,蔚為壯觀……童年的故事也很多,先說一個饞嘴的事吧。
小時候可能是家里窮的緣故,好東西吃得少,嘴很饞。20世紀70年代初,人與人之間串門走親戚的時候,都會買十幾根油條送禮。我們這兒的油條又叫“香油馃子”,是當時很好的禮物。有一次我去走親戚,在人家家里吃香油馃子吃多了,撐得直打飽嗝兒……那家人拍著我的小肩膀說:“別看這小家伙人不大,還怪能吃哩!”那人不知道,我一年沒吃上這個東西了。
還有一次,我一個人在路上好好地走著,突然一下被什么東西絆倒了。我爬起來一看,地上突起一塊黑東西。這個黑家伙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地上。我離近一看,原來是塊大黑鐵!我狂喜不已,蹲下一點一點把它給摳了出來。我把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大黑鐵,賣到附近的廢品回收站,賣了一毛多錢。那時的一毛多錢對我這樣一個窮孩子來說已經很多了。我拿著錢到供銷社買了好幾塊糖,真甜……家里人不知道,我睡覺的時候嘴里還含一塊糖呢,做夢都是甜的。
魔幻童年
身處喧鬧的街市,斑駁迷離的街景好似一劑迷魂藥,令自己迷失在人海與光影之中,擯棄了外面的喧囂,穿越了歲月時空,忘卻了陌生的現(xiàn)在,思緒又把我?guī)У搅四莻€有著蛙鳴、蟋蟀歡唱的童年。
童年是人之初,一旦形成的印象、經歷、感受都會在整個的人生畫卷上難以拭去,這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
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充滿神奇的童年,注定了熱愛自由、不愿束縛、向往自然的個性,那是個童話的童年、神話的童年、魔幻的童年。
每當太陽落山,夜幕降臨,整個平原上的村莊一片沉寂。春天的晚風里,布谷鳥在遙遠的夜空中咕咕吟唱;夏天村邊地頭的水塘里,蛙鳴此起彼伏,猶如優(yōu)美的合唱;秋夜里,蟋蟀吱吱作響,無意間增加了絲絲的寒意;難忘的冬夜,屋頂傳來北風凜冽的呼號……奶奶點亮煤油燈,在昏黃的燈光下,人物好似油畫里凹凸分明的背景。如豆的光亮,令人覺得是那樣的溫暖,暫時忘卻屋外的寒冷。蜷縮在暖和的粗布的被窩兒里,看著正在燈下為我縫補的奶奶的背影,聽著她講述的古老傳說,聞著好聞的煤油的味……很快便進入神話一般的夢境。
奶奶講的故事有很多種,什么親身經歷,鬼怪志異,以及各式各樣的神話傳說,聽得我縮在被窩兒里,看著映在墻上的影子,感覺這些神靈無處不在。
冬日的早晨,奶奶先從房外的麥秸垛里抽出一把鮮麥秸,在屋里點著火,拿著我的開襠棉褲在火上烤。烤得棉褲發(fā)燙了,我才在煙霧繚繞中將它穿起來。這時,空氣中都是燒麥秸的味道。
后來,村上有了有線廣播,也通到了每家每戶。像紙一樣薄的喇叭,播起音來竟哇哇響。我覺得很是神奇,問奶奶:“里邊怎么有人說話呢?”奶奶說:“誰知道呢,許是人鉆在電線里邊說話吧。”我信以為真,天真地想哪天鉸開電線自己鉆進去講。
我最愛吃奶奶煎的“結了龜”(蟬蛹)。我家南墻外就是一片大楊樹林,一到夏天,吹得滿院子的清清的樹葉子味。那楊樹干又白又直,樹葉子清涼墨綠,在有風的時候,嘩啦啦地響徹耳邊。那是我兒時的天堂。記憶最深的是夏天雨后逮“結了龜”,它們這時躍躍欲試,等待著爬上大樹,而我則圍著樹根的位置找小洞,找尋它們的棲身之所。有的小孔如針眼大小,找起來很是吃力。找到后只要把小棒放下去,它們就會隨著小棒爬上來,然后束手就擒成為甕中之鱉。我把它們帶回家,把腿掐掉,放進鹽罐里。等上一天后,奶奶就在地上支上鏊子,點上柴火,把腌好的知了放在上邊,滴上點油,然后用鏟子一壓,一股特別的肉香飛進鼻孔,香極了……這比現(xiàn)在的燒烤香多了。至今,我仍忘不了充滿陽光,充滿知了香味的時光。秋天,樹林里飄了一地的紅葉,走上去軟綿綿的,我會拿一根鐵條穿上長長的線,把一枚枚樹葉穿起來帶回奶奶家當柴火用。
剛來了一場急雨,使初春的夜晚更加清新和濕潤,月亮更明亮,但是覺得還是童年故鄉(xiāng)的月亮更圓、更亮。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20世紀80年代初,我家從鄉(xiāng)下搬來濟寧市區(qū),戶口落在城郊三官廟村。那時城郊都是菜地,一出城到處綠油油的。特別是夏天,地里長著鮮紅的西紅柿、翠綠的黃瓜、長長的豆角、黑紫的茄子……我家一畝多地,媽媽是種菜的好手,按照一年四季二十四節(jié)氣,把菜園收拾得郁郁蔥蔥,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家里的菜地里也是生機盎然。家種的大棚韭菜,春節(jié)前上市,十分好賣,一斤能賣到一塊多。為了防止韭菜被盜割,我和大舅夜里要到韭菜地里的地窖去住。黑燈瞎火的地窖里點著一盞小煤油燈,如豆的煤油燈熏得小地窖里一股煤油味。窖外寒風刺骨,萬籟俱寂,滿天繁星格外明亮……
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或者學校放寒暑假,我就到菜地里干活兒,摘豆角、澆地、上化肥、翻地,再跟著媽媽到菜市場賣菜。當時,街上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賣菜,幫著家里大人干活兒,別看人沒有自行車高,可是騎上去比誰都騎得快,騎得穩(wěn)當。車座后邊往往綁著個大筐,里面裝滿了菜。我都是到現(xiàn)在的十三中附近、市委一宿舍、半截閣賣菜,一邊走一邊喊。弟弟當時也就四五歲,跟在我的后邊,累了,就坐到小車上;餓了,我就用賣菜的錢給他買吃的。有一回,我賣的是小白菜,不值錢,幾分錢一斤,一下午才賣了兩毛多錢。弟弟喊著餓,我就給他買了個一毛多錢的大面包,回家后沒法兒交差了,只能被批一頓。
幸福就是一塊糖
什么是幸福?人們的回答會各不相同。我童年時理解的幸福就是吃上一塊糖。
20世紀70年代,我們家不富裕,唯一奢望的美食就是一塊水果糖而已。因為沒見過香蕉、橘子,也不知道他們的味道。唯有糖果,吃在嘴里,化在舌間,那絲絲甜意使人暫時忘記貧乏的生活。
我總是期待著來家拜訪的客人帶來一些糖果,那是我的最愛。沒有糖吃的時候,我就自力更生,到附近的垃圾場撿破爛兒賣錢。有時候收獲很大,幾塊廢鐵、碎玻璃、破布就能賣上幾毛錢。除了能買到糖吃,還有多余的錢到濟寧公園遛一圈,那時候濟寧公園的票價是兩毛錢。沒有票的時候就從公園南邊假山附近的墻上偷偷地爬過去。
奶奶每次來我家都帶著糖來,我假期里到奶奶家住的時候,奶奶也經常給我買糖吃。那時候,牙齒保健知識幾乎為零,家里也沒有嚴格要求,就經常吃著糖睡覺,后來長大了,有一些牙齒也壞掉了。
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孩子們,小時候能吃上一塊水果糖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現(xiàn)在,吃的東西越來越豐富,再好的糖果也不喜歡吃了,已經找不到童年那種感覺了。
童年的游戲
20世紀70年代的孩子都還記得當時的游戲,那時候沒有電視、電腦,但是一樣有著幸福的童年。小時候玩過的游戲很多,比如玩泥巴、摔瓦屋、藏毛猴、打子彈仗、推鐵環(huán)、摔煙盒、彈玻璃球、玩娃娃模—單從這些游戲的名字上,現(xiàn)在的孩子們已經不知道了。
我玩泥巴很在行,一攤爛泥,在我手里一會兒變成了坦克、小人、餅干、桌子、板凳之類的物件,玩得煩了,統(tǒng)統(tǒng)一摔,又成了一堆泥巴。用膠泥捏手槍效果最好。從干涸的泥坑深處挖出黝黑錚亮的黑膠泥,這種泥很黏、很硬,最適合做手槍模型。我先把泥巴摔成一個長方形,然后畫出手槍的大體模型,隨后用刀子把輪廓外的泥巴剔走,最后按照想象中的模樣,把這塊泥巴修理成一把盒子槍。我見過人家做得像的,簡直可以以假亂真,要是半夜里拿出去,一定以為是便衣警察出來了。
有一種泥巴游戲很好玩,就是娃娃模(mu)。小時候,一些在農村走街串巷的貨郎,木轱轆獨輪車上會有一些很稀罕的貨,我情有獨鐘的就是娃娃模。娃娃模是一種類似復制玩偶模型的陶片,上面有凸出的圖案紋理,做得很精細、很形象;內容也五花八門,有古代戲劇人物、神話人物、虎狗兔貓等,十分神奇。我用泥巴糊在娃娃模上,取下來之后,上面的圖案就復制在泥巴上。為了讓復制后的泥巴更能長久,要放在火里燒,我都是等到家里燒鍋做飯的時候,將它扔到鍋下的火堆里燒,燒得不紅不黑的時候再取出來,那種成就感、幸福感溢于言表。
還有一種游戲叫摔瓦屋。先把泥巴捏成個碗形,底兒用唾沫蘸濕弄得薄薄的,接著高高舉起往地上一摔,砰的一聲,只見瓦屋被摔爛在地上,摔出個大洞。誰摔得響,摔出的洞大,誰就獲勝,其實就是熊孩子搗蛋的玩法。
童年的游戲盡管最原始,但也最深刻。那種在涼爽的樹蔭下、明亮的月光中、無垠的雪地里與玩伴的天真爛漫,在一起藏毛猴的神秘刺激,遠比現(xiàn)在的摩天輪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