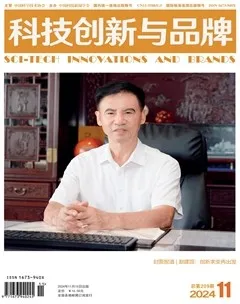朱正圻:經世致用,為國獻策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領域科學化程度最高的學科之一,以向自然科學看齊為旨趣;同時,經濟學也被認為是經世致用之學,被賦予推動和指導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期待。
在中華民族奔涌前進的歷史中,朱正圻將自己比喻為“一滴水珠”。這位出生于1929年,科研實績豐碩的經濟學者流露出的謙虛品德,如水利萬物而不爭。而他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貢獻,如同大海中的一股澎湃力量,推動著時代的進步。
他在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筆耕不輟,如今年逾95歲仍活躍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保持著日王盛的學術熱情和創作活力。作為首批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經濟學家,朱正圻在學界所獲得的獎勵和榮譽令人矚目。然而,支撐他繼續伏案工作的,并非外在的榮譽,而是源于一生對于國家與經濟學的熱愛。
為發展獻智
朱正圻出生于上海的“國貿世家”,家族四代從事國際貿易業務,對經濟學的熱愛和對社會發展的關注根植于朱正圻的血脈之中。新中國成立前,朱正圻考入復旦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在逐步精深專業知識的同時并投身愛國行動,于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朱正圻將經濟學家的天職使命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聯結在一起,面向國家需求而做研究。
20世紀50年代中期.朱正圻撰寫的有關世界經濟專題報告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研究生后,朱正圻先后轉入上海經濟研究所和市外事部門,研究世界經濟、地區和國別經濟、對外經濟關系,兼及貿易、市場、工農業和外交等方面,在《文匯報》學術版發表《西歐共同市場的出現、影響及趨勢》后,引起廣泛關注,被譽為“北有前輩易夢虹,南有后輩朱正圻”。
朱正圻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任歐洲研究室主任后當選為上海歐洲學會首任會長,并被德中友好協會委任為中國上海地區首席代表。適逢改革開放帶來國際交流的機遇,朱正圻積極參加國際學術交流,通過對美國、英國、德國等國進行實地考察,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和報告,如《中外經濟體制異同比較及研究價值》《西歐經濟運行機制》等。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使中國身處劇烈的社會轉型期,亟須大量經濟學者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為國家治理建言獻策。朱正圻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也需要市場機制。在西方國家中,德國的社會市場對中國有較大的借鑒意義。基于此,他建議邀請德國經濟學家共同研討,推動了中國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一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服務跨國外包迅速發展,既帶來了歷史機遇,也催化著一場新的競爭。朱正圻關注到起步較早的接包方國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我國也正加快發展跨國服務外包產業。他主持撰寫的《現代服務跨國外包》榮獲“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優秀創新成果”獎,并被編入《踐行科學發展觀》理論卷。
嚴謹、務實、創新是朱正圻的學術風格,堅定的愛國信念是朱正圻的學術底色。他的愛國精神和學術成就,不僅影響了當代經濟學的發展,也為后人樹立了榜樣。
與時代共進
親身經歷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的歷程,使朱正圻擁有廣闊的經濟學歷史視野。而把目光放在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最前沿,對于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研究,是這位經濟學家的思考線索,具有鮮明的當代特點。
“科技金融”與“金融科技”本質不同。科技金融屬于產業金融的范疇,落腳點在金融,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典型代表。而金融科技落腳點在科技,與其并列的概念是軍事科技、生物科技,意指利用科技為金融服務賦能。
朱正圻認為,現代科技與金融是現代經濟生活中最核心的兩種資源,對其他資源和要素起著強大的吸引和凝聚作用。
2016年,他主持完成了《科技金融現代版——內涵與運轉》,闡述了科技與金融的關系,強調科技的發展需要金融相助,但不能過度強調金融的重要性,突出了科技應有的地位。
相比發達國家,我國在金融科技領域起步較晚。面對國內金融對科技的迫切需求,朱正圻將金融科技列為新的科研項目,開展走訪調研,廣泛收集資料,潛心撰寫。2021年,九十三歲的朱正圻出版了近30萬字新著《金融科技——涵義、運轉及賦能》。
在本書中,已進入鮐背之年的朱正圻與時俱進、博學多通。他關注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先進技術賦能金融服務發展,認為“對于銀行,金融科技推動了銀行改革創新,拓展業務,提升質量,降低成本;對于企業,金融科技是企業生存、發展、開拓提升、改革創新的動力、依據和基礎。企業急切需要科技賦能,用好新一代信息技術,加大創新力度,使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務于企業。”
朱正圻關注到,在科技驅動和支持下,金融服務的受眾數量、層次和效果極大提高,普通人和小微企業也能享受到金融科技帶來的便捷。對于金融科技的未來,他充滿希望,“隨著金融科技不斷發揮實效,我們能夠更好地控制風險,更快地創造發展機會。科技的發展將開啟共享繁榮的新時代”。
在朱正圻身上,凝聚著奮進的力量與創新的榮光。這位光榮在黨七十年的經濟學家,始終保持著赤子之心和進取精神,以一以貫之的經世濟民思想,為國家貢獻著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