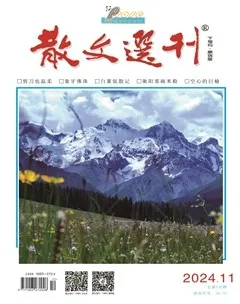標準答案
“ 鄧老師,鄧老師,我的答案是對的——”一個翻轉身,我發覺自己在夢中呼喊。
記憶中,鄧老師的個頭兒恐怕只有一米六的樣子,在那個普遍營養不良的年代,他卻敦敦實實的,肚腹碩大,夏天,架在身上的兩條短短的胳膊前后擺動,像極了從湖里采出的兩支粗壯的蓮藕,他微微笑著,活似鄉下的土地菩薩,走起路來,蹬得泥地教室一陣陣打顫。就是這么一個正值盛年的鄉村教師,整整當了我三年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老實說,一般同學是不喜歡語文的,尤其是一上作文課就頭疼。在同學們的眼里,喜歡語文往往是極其浪漫而非女生莫屬的,而我這樣半晌打不出一個悶屁的男生,竟然對作文感興趣,大家都覺著奇怪。
自從鄧老師當了我的語文老師,我就對上語文課對作文有了興致。起因是,有一次,鄧老師的大兒子(那時應該還不到二十歲),冬修水利的時候,寄居在我家里,對我堂屋里毛主席像兩側的一副由我書寫的對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嘖嘖稱贊。某天一大早,鄧老師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說,你以后不但要認真習字,更要好好練習寫作文,字是人的一張臉,作文可是你的魂兒,記得啦?這突如其來的好運,讓我有點兒茫然不知所措。
鄧老師教我們作文,有一宗事很讓同學們反感,不論寫什么文體,一律得事先擬寫作文提綱并謄寫在作文本上。我卻十分討厭寫提綱,我習慣于打腹稿,腹稿長啥模樣是說不清的,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每次鄧老師念同學的范文,幾乎都沒落下我的。時間一長,鄧老師對我是否寫提綱,也就不作要求了。以至于發展到畢業的那一年,同學們統一寫命題作文,我可以不受此限,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惹得同學們個個切齒痛恨,巴不得將我剁了燉湯。
針對我的特殊化,鄧老師給出的理由是,誰能像劉博的作文上《小溪流》雜志,就可以不用寫提綱,自擬作文題目,這下可把同學們怔住了,而我成了落單的孤雁,客觀上也助長了我驕傲自大的壞毛病。
我最得意的時候,莫過于盼望發作文本下來,每次鄧老師寫在我作文上紅杠杠的眉批,都不盡相同:標題新穎,主題突出,段落層次分明,描寫強弱得當云云,批得我心花怒放。每當我的作文被當作范文在全班宣讀甚至在高年級傳閱的時候,一股股成功的暖流,如同潮汐般一次次朝我涌來。
獨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鄧老師抱著一摞子作文本,還有段考測試卷走上講臺。我似乎有一種預感,心突突不安起來。45 分鐘過去了,到了要宣讀范文的時候了,平日里從來沒有被表揚的同學,做夢也想不到作文被當作范文宣讀的同學被一一表揚過后,我著急了:鄧老師竟然沒有點我的名字,我的測試卷98 分,因為我把對“嶄新”中的“嶄”字解釋成了“十分”,老師給出的標準答案是“非常”“很”,我失分了。我以為一向語文成績在班上領跑的我,這次讓鄧老師大失所望了。末了,鄧老師叫我下課后去了他的辦公室。
我越想越不對勁兒,越想越覺得屈辱。一聲戰栗的“報告——”后,鄧老師對我說,這次沒有表揚你,你覺得委屈了不是?我帶你們幾年了,有的同學一次都沒有表揚過呢,你一次不表揚,就成這樣了。你不覺得你有些自私嗎?四十幾號人,一個集體呀,我最最要做的是,希望你們個個都升到重點中學去!
其實,你的“十分”與“很”“非常”有什么分別呢,扣你的分,是想叫醒你戒驕戒躁,別把尾巴翹上了天!
我點點頭,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待我轉到外鄉上學時,打聽到鄧老師去老家探親后就再也沒有返校來。后來,再打探老師的下落時,他早調回城里了。
幾十年了,至今,經鄧老師推薦第一次發表在《小溪流》雜志上的習作《鄉間小路》,仍存留在我精心制作的作文剪貼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