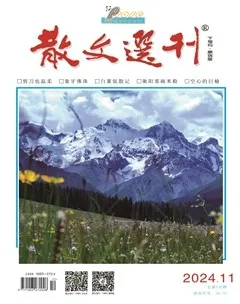打米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農民自產的稻谷,必須挑到很遠的打米廠去加工。
新打米廠設在桃林港電排后面,距家將近二里路。星期天或寒暑假,碰上打米,我和哥就換上縫了補丁的破爛衣服,一人一擔谷,大清早出發,往打米廠小跑。天還沒有大亮,經常能看到幾顆星星,有時還能看到月亮。我和哥踏著星月,挑著擔子小跑。小跑了沒多久,左肩膀就疼了起來,于是就把擔子挪到右肩膀上。不久,右肩膀也疼了起來,我就把擔子再挪到左肩膀上。一路上,兩個肩膀輪著挑擔子。一擔谷只挑到半途,全身就開始發熱。緊接著就大汗淋漓,腰酸背痛,只好放下擔子小坐一會兒。掀開衣領一看,兩個肩膀上都長出了紅桃子。不等汗息干,肩膀不那么疼痛了,我們兄弟倆又挑起擔子,邁開大步繼續朝前走。
到了打米廠,已有許多人排起了長隊。輪到我們打米時,兄弟倆就雷急火急地將谷倒在泥巴地中間一小塊水泥地上,學著前面大人們麻利的樣子,一簸箕一簸箕地往機器斗里喂谷子。眨眼間,白花花的大米,就從機子下方吐出來。谷殼呢,就變成黃黃的糠,從另一個出口出來了。打完米,我和哥還要用風車把米里的糠吹干凈。吹米時,糠灰米塵彌漫,把一身衣服弄得灰撲撲的。頭發、眉毛、胡子由于都沾滿了粉塵而變得灰白,年紀輕輕的我,儼然是白發白眉白須的老頭。回家后,母親用米篩子篩一兩遍,把細碎的砂石清除了,才把米放入米缸,以備一日三餐舀取做飯。
春節前,要打過年米。正月客人多,打的米就多一些。況且,還要打一些糯米拍水酒,做糍粑,做坨子粑粑,等等,用來招待客人。這時,我們就向境況稍微好一點的鄰舍借一輛板車,拖三擔谷,上面再加幾個麻布袋。哥在前面抓住板車把,掌握方向;我在后面推。有一次打完米回來,我為了顯示能耐,就和哥換個位置,我在前面拖板車把,哥則在后面推。年底陰雨連綿,高低不平的爛泥路面溜滑不堪。板車像喝醉了酒,一搖一晃、一上一下地踉蹌著。我緊緊地抓住板車把,身體極力往前傾,腳拼命向后蹬。我喘著粗氣,汗,從額頭到腳后跟,像洗澡一樣……突然,肩膀和手狠狠地朝上一抖,板車滑進了一個坑洼,翻了,米與糠倒在了爛泥里!哥瞪了我一眼。我們倆趕緊蹲下身,把漂浮在爛泥上面的糠和米一捧一捧地捧進籮筐里。被爛泥完全淹沒的,就只能忍痛放棄了。重新上路時,我的屁股被哥哥用扁擔狠狠地拍了一下,板車把也被哥搶去。我心虛,乖乖地放棄了“司機”的崗位,重新到后面推車去了。
整個村只有一臺打米機,打米廠里總是籮筐扁擔擠得滿滿的,一天到晚,挑擔子的人進進出出。打米師傅忙個不停,生意相當紅火,隨來隨打。幾年過去,打米師傅的腰包鼓了起來,服務態度卻大不如以前,一天比一天冷淡。后來,打米師傅把工作時間定在每天清晨和傍晚,再后來,改為傍晚打米……
四十年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我的鄉親們已經完全用不著再自己去打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