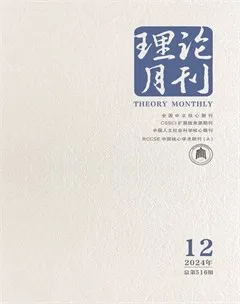中國網絡文學商業化轉型動因再認識:基于網絡文學實踐的微觀視角


[摘 要] 一直以來,外部環境誘導被視為中國網絡文學商業化轉型的主要原因,對客觀因素的片面歸咎遮蔽了網絡文學商業化發展的內在必然性。只有回到網絡文學的具體實踐中,對網絡文學的讀、寫、傳播進行微觀考察,才能真正揭示網絡文學商業化轉型的內在邏輯:超文本理論家空談理論,無視超文本理想讀者與現實傳統讀者、數字原住民、電子游戲用戶之間的巨大錯位,導致研究者們對網絡文學先鋒性發展的錯誤預判;文學網站作為寫作元程序的一種,推動網絡寫作沖破精英圈層開始了大眾化的蓬勃發展,但這種將用戶行為局限在使用者層面的寫作模式,擠壓了超文本寫作的生存空間,也將網絡文學的發展與文學網站的發展深度綁定;網絡媒介使傳統文學制度統御下文學青年們的發表焦慮得以釋放,但新的關注焦慮又催生了以虛擬聲望大量累積為標志的網絡作者資格認證裝置和以此為占位資本的網絡文學場。
[關鍵詞] 網絡文學;理想讀者;元程序;關注焦慮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12.016
[中圖分類號] I206.7"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12-0138-10
當下,中國網絡文學已成為與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并列的“世界第四大文化奇觀”。這與中國網絡文學已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具有典范性、引領性商業化運作體系息息相關。商業化使網絡文學呈現出消遣性網絡類型化小說盛行、經濟邏輯綁架網絡自由書寫、讀者中心主義大行其道等諸多文學、文化景觀,顛覆了華語網絡文學發軔之初人們對其先鋒、自由、民主的發展期待。中國網絡文學這一意料外的發展,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討論。技術商業化、媒介融合的必然性和消費社會的資本誘因、特殊時期文化轉型的順勢而為等被普遍看作中國網絡文學商業化轉型的主要原因1。
但對客觀環境因素的片面歸咎遮蔽了網絡文學商業化發展的內在必然性。深入網絡文學的具體實踐,對網絡文學的讀、寫、傳播過程進行微觀考察,就會發現超文本理想讀者與實際讀者的錯位,寫作元程序——文學網站帶來了文學大眾化亦使網絡寫作與其深度綁定,關注焦慮與網絡作者資格認證裝置的產生為先鋒性超文本的衰微、網絡文學發展道路的重新選擇提供了契機與內在動因。中國網絡文學正是在內外合力的作用下走上了商業化發展的必然道路。
一、讀:超文本理想讀者與實際讀者的錯位
長久以來,在對網絡文學定義已形成的層次化共識中,以超文本文學為代表的狹義的網絡文學被視為最具代表性、典型性、充分性的網絡文學,是網絡文學的“究極體”和必然發展方向,歐陽友權稱其為“真正的網絡文學”1。
超文本是一種全局性的信息結構和文本模式,以非線性、動態性、交互性區別于封閉、靜態、單向傳播的線性印刷文本。它使巴特的“理想文本”在虛擬世界中實現了可視化呈現,打造出網絡交錯、相互作用的無中心、無主次、無邊緣的開放空間。“文本”有別于“作品”,顛覆了傳統形而上學的秩序,使闡釋失去效用,具有“‘不可閱讀性’,使人們不能對它‘消費’,人們要獲得‘文本’,就要把它們重新恢復為一種演奏、一種任務、一種時間”2。由此文本閱讀也區別于作品閱讀,后者以目的為導向,讀者通過解析作品內容尋找深層含義來喚醒自己的情感反應,而前者則是在尋找文本意義已不再作為核心導向的前提下,讀者的一種純粹的文本體驗。國內外的超文本理論家們熱衷于使用巴特的文本理論對超文本進行認識與闡釋。然而,有別于巴特等解構主義學者與形而上學的闡釋學的決然決裂3,超文本理論家們對文本意義的態度總是曖昧的、含糊的、優柔寡斷的。
這種曖昧態度集中體現在超文本理論家們對超文本敘事的關注。喬伊斯強調重讀對超文本文學的重要性,他將超文本讀者分為篩選者(screeners)和采集者(gatherers),前者通過對鏈接的選擇來產生一種符合其敘事期待的文本,而后者則試圖在一次次的重讀中對超文本進行整體性把握,但他也意識到客觀意義上的重讀在超文本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將超文本比作一臺講故事的機器,“每一次閱讀……都會生成一個新的文本”4。這無疑使超文本閱讀倒向了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超文本敘事研究學者瑪麗-勞爾·瑞安揚棄了這種觀點,不再追求讀者的期待文本或是對文本進行整體把握,認為超文本閱讀不能以目標為導向進行刻意的信息檢索,必要時懸置敘事是合理的5,但她仍無法徹底放棄敘事,認為意義是閱讀過程中的偶然生成,并提出了超文本存在的互動悖論:如何將用戶的自由同形成精致的、能帶來審美滿足的故事的需求調和起來6。在超文本理論家看來,超文本賦予了文本千變萬化的可能,使一部普通的作品也能在不斷地變形改造中形成無邊無際的文本宇宙,而讀者是航行其中的舵手,是超文本價值實現的中介和關鍵。
正是由于超文本讀者的這種重要性,傳統作為沉默、溫馴、被動的接受者的讀者已不能滿足需求,讀者需要成為解釋者、共同敘事者甚至寫作者。國內代表性超文本研究學者黃鳴奮強調閱讀(讀者參與)過程本身的重要性,認為超文本閱讀無所謂結果或內容,因為在“文本自身不再向讀者提供結構清晰、條分縷析的閱讀順序”的情況下,“‘秩序’和‘層次’只能由讀者本身來賦予”7。但這里所說“秩序”“層次”絕非單純地通過鏈接選擇對超文本拓撲結構的探索,這一點在他對“超讀者”的論述中可窺一斑:“這種超讀者至少應該在三方面表現出自己的造詣來:其一,具有更為強烈的批判意識和溝通愿望。他們不是滿足于閱讀‘本本’,更不會執著于其中的只言片語,而是善于充分利用電子超文本所提供的便利,將閱讀變成一種切磋琢磨的過程。其二,具有更為高超的自持能力和鑒別能力。在缺乏上下文提示的電子超文本環境中,他們能夠把握‘航行’方向;紛至沓來的大量信息不僅不會使他們感到混淆、茫然或無所適從,反而會激勵他們在主動地比較、甄別過程中進行創新。其三,具有更高的思維靈活性和積極性。他們是超越了傳統讀者角色規范的新型角色,具有高度的參與精神,絕非電視文化所熏陶出來的‘沙發土豆’。”1數字文學研究學者單小曦進一步提出“精英讀者”范疇:他們具有一定技藝創造能力和合作性新主體精神,能充分利用數字交互媒介,積極探索數字美學潛能2。不管是超讀者還是精英讀者,都代表了超文本理論家們對超文本文學理想讀者的期待:超文本理想讀者是讀者與作者界限模糊的合作者,這種超位性的角色必須具備極強的閱讀素質,如屏幕閱讀技能、超文本閱讀理解能力、豐富的紙質文本閱讀經驗、元認知能力等3,才能在超文本建構的宇宙中自由穿梭、游牧,對意義進行隨意采擷與編織,才能在不同的文本間建構起關聯性,才能避免在文本宇宙中迷失方向,使閱讀不至于淪為一種單純的體驗或是能指漂浮的文字游戲。
理想讀者的提出總使人聯想到伊瑟爾“暗隱的讀者”或是姚斯所說由作品與讀者“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相碰撞而產生的讀者形象。與之不同的是,相較于姚斯和伊瑟爾將理想讀者視為一種內在于文本的構成,超文本理想讀者首先強調讀者應該具備必要的能力和素質,強調讀者要能在閱讀開放性和意義無限性中尋找到“解釋者的權利”與“文本語境權利”之間的平衡點。但與一貫的讀者理論相同,超文本理想讀者也代表著對實際、經驗的讀者的懸置,正如伊瑟爾所言,“暗隱的讀者的概念是一種超越的范式,它使我們能夠描述文學文本的結構效應。它標示出:讀者的角色只有用本文的結構與有結構的活動才能予以解釋”4。理想讀者作為一種策略被提出,旨在凸顯讀者在超文本閱讀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假設,對現實的閱讀實踐缺乏有說服力的指導,與現實中的讀者之間存在巨大的錯位。
這種錯位一方面表現在超文本理想讀者與傳統讀者的閱讀習慣存在巨大差距。這里所說的傳統讀者,指經由傳統線性文本培訓出的普通讀者。2001年一項超文本閱讀效果研究發現,超過55%的超文本讀者選擇鏈接是為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因此當對故事發展感到困惑時,這些讀者會本能地認為自己錯過了某些關鍵鏈接,更有75%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總是感到困惑和不解——超文本理論家們預期的閱讀效果在具體實踐中很難實現5。實際上,大多數讀者都更愿意被邀請進一個故事,而不是從頭開始創造故事6,因為多數讀者都沒有足夠的元認知能力去處理無窮的鏈接、交錯、跳轉帶來的混亂,在閱讀過程中會因為找不到情節主干而陷入一種漫無目標的游蕩,被困在敘事的可能性過剩的迷宮,超越期待視野達成視域融合很難實現。迷路(Disorientation)是超文本閱讀的必然宿命,但迷路同時也意味著讀者堅信存在一條或多條正確的道路。超文本理論家們總是忽視這一危機:不管超文本為文學帶來多少空前的新變,它所面對的多數還是經由傳統線性文本培訓出的讀者,這些讀者在進行超文本閱讀時很難擺脫印刷時代殘留的思考模式和閱讀慣習:期待視野、線性思維、文本尊重情節……他們無法將閱讀視為單純的文本體驗,卻總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迷失方向。
另一方面表現在超文本理想讀者與數字原住民在認知方式上存在巨大鴻溝。布斯認為不同的修辭策略總是與特定的讀者群體密不可分,他所謂的“修辭”取自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意味著作品如何與讀者交流、引起讀者興趣,進而影響讀者。從這個角度看,不同的文本、媒介自然會孕育出各自獨特的讀者群體。互聯網非線性共時結構、互文的文本形態、交互性的主體參與方式漸漸培養出一批具備新媒介素養的讀者——以“超級注意力”(hyper attention)為認知方式的數字原住民。所謂“數字原住民”即出生伊始就濡染于數字化環境的讀者群體,他們受電子閱讀文化的深刻影響,形成了與以注意力長時間集中、穩定、聚焦單一目標為特征的深度注意力(deep attention)相對的另一種認知方式,即超級注意力。超級注意力使讀者的注意焦點在不同信息之間持續跳轉,這些讀者偏好多重流動的資訊,厭惡單調乏味的內容和形式。超級注意力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個體在超文本環境中面對鏈接、節點必須進行大量決策工作,認知資源在重復的決策中不斷被浪費,進而加重了讀者的認知負荷,導致他們對信息進行處理、記憶、比較、總結的效率不可避免地下降1。表現在具體的閱讀活動中,則是以略讀、掃讀的瀏覽閱讀模式取代了精讀的沉浸閱讀模式,以驚顫的審美體驗取代了沉思的審美心境,閱讀活動不再是對意義的探索與追求,而是如解構主義論者所說:“當批評家面臨的是一個無從闡明的對象,一個具有被無窮發隱索微潛能的未知世界的時候,批評是否更像對作品的一種體驗:與其處心積慮給作品套上一個意義框架,不如來欣賞它撲朔迷離的構成圖像呢?”2這一認知方式的出現標志著閱讀的淺層化、快餐化、娛樂化時代的到來,也代表著數字原住民與超文本理論家們所期待的理想讀者漸行漸遠。
超文本理論的不斷發展,使網絡文學這一新文學形式迅速通過其先鋒性表達方式、實驗性敘事模式、典范性超媒介存在形式證實了其品格的獨立性,在確證網絡文學研究的學科價值、開拓新的學術視野方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超文本理論家們空談理論、忽視實踐的做法也一直為人所詬病。“研究者們依靠先入為主的一些觀念或常識來進行討論,而不去面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現實”3,崔載溶認為這種抽象性與觀念性傾向嚴重影響了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事實上,超文本理論與實踐的巨大錯位,也使學者們對網絡文學的發展方向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錯判,認為網絡文學理應沿著先鋒性、實驗性、典范性的超文本道路繼續前進。但作家為讀者寫作,文本為閱讀存在,網絡編輯勞拉-米勒在超文本理論最炙手可熱時就曾悲觀地說:“我還沒有遇到過閱讀超文本小說的人……(閱讀超文本小說)是一項讓人無精打采的任務,是一個不停地在備選方案中作出選擇的問題,我確信,每一個備選方案都不會比其他方案重要。蘭道認為,這個過程讓我‘成為一個真正積極的讀者’,但這種體驗卻讓人感覺毫無意義、枯燥乏味。”4無人臥游的文本宇宙注定不會產生關于審美的呼喚與應答,沒有讀者的超文本也只是一堆冰冷死寂的虛擬字符,網絡文學要繼續發展,注定其不能直接沿著實驗性、先鋒性、典范性的超文本道路繼續前進。但米勒在當時顯然也未曾注意到超文本正以文字冒險游戲和MUD(Multiple User Domain)游戲的形式迅速捕獲一群特殊的讀者。電子游戲在日后迅速發展甚至被冠以“電子海洛因”的標簽,并伴隨著技術迭代與媒介融合成為人們進行多元交互、實現虛擬生存、超越涌現敘事的文本空間1——但這種以娛樂、解壓、打發時間為目的電子游戲用戶顯然也并非超文本理想讀者 。
實驗性、先鋒性、典范性超文本文學的衰微是網絡文學發展的必然。小說家保羅·拉法奇認為超文本文學之所以處境艱難,是因為它誕生于一個尚未準備好的世界,超文本文學受制于這個世界中“糟糕的(寫作)技術”和“不利于用戶的界面設計”,但更重要的是,“在專業閱讀圈子之外,它的名聲并不好”2。超文本文學召喚的理想讀者始終沒有出現。
二、寫:“元程序”寫作的利與弊
與印刷文學將文字書寫在具有穩定物理形態的書頁上不同,網絡文學以比特形式存在于虛擬程序、網頁中,比特是網絡文學的第一語言。但網絡文學作者無法直接使用比特進行寫作,須在特殊操作環境中,通過對比特經過編碼、譯碼、轉碼形成的符號、程序展開創作,如超文本創作軟件、超文本網絡等。它們為作者提供的用以創作的“元程序”(metaprograms)是一種現成、穩定的操作環境和規范,能夠避免從頭開始為某一文本進行編程的痛苦,但它的不足也恰恰在于預設了作者的所有操作范圍和規范,局限了作者的行為。為了說明“元程序”與使用者之間的復雜關系,賽博文本研究學者亞瑟斯引入“用戶”這一概念以取代傳統讀者、作者的劃分。用戶包含更廣泛的行為和角色,更不容易被預設;同時,用戶也暗示了“元程序”使用者復雜的政治內涵——它代表了積極參與,同時也意味著依賴,意味著它必然受到某種系統的影響。
用戶這一身份表現出的雙重屬性對我們理解“元程序”寫作的利與弊無疑具有啟發意義。亞瑟斯以“元程序”Hypercard為例,將用戶的參與屬性與依賴屬性具體化為兩種角色系統:開發者系統(Developer)和使用者系統(User),如圖1所示。在該系統中,從最終開發者(D2)到最終使用者(U4)之間至少存在四個不同的位置層,而在傳統印刷文本中通常只有兩個位置層。事實上,包括網絡在內的所有超文本系統都存在縱向的分層。用戶的分層直接影響了文本的分層。這里的文本分層并非指現象學、新批評、讀者接受理論從文本淺層意義向深層意蘊世界轉變過程中對文本內部結構進行的劃分,而是指“元程序”中文本的具體存在方式。假設一個“元程序”提供了最基本的系統S,S可以發展出一個表達潛力有所減弱的子系統S′,而子系統S′又可以發展出一個更加減弱的S″,由此類推。在這個過程中,文本不是存在于某一層,而是存在于系統中的一個縱向結構:它在最基本的S層中表達,但同樣依賴于不同層次子系統提供的元素。文本對后者的依賴并不是絕對的,因為就算子系統被取代、刪減、改變,但最基本的S層始終保持不變。換句話說,計算機程序文本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系統(S)轉換成文本(T)的結果1。在結構性存在的“元程序”中,不同層次文本對應擁有不同權限、能力的用戶,代表著不同層次用戶的表達潛力和寫作自由度也不同。鑒于此,博爾特認為:“電子寫作定義了一種新的創造力層次——介于浪漫主義藝術家的明顯原創性和傳統讀者的明顯被動性之間的無數層次。”2亞瑟斯贊同這種對作者—讀者之間的層次劃分,認為數字系統的這種縱向結構提供了多個可以對文本進行創造性干預的層次,語言課程層(language lesson)的用戶會受到更深層次用戶行為的制約與影響,不同權限之間的用戶必然是不平等的3。瑞安也意識到這種文本層次和用戶層次的存在,她將數字文本比喻成可以一層層剝開的洋蔥,并從用戶參與的影響深度上對用戶的交互行為進行了分類,提出了最高層次的“元互動”(Meta-Interactivity)。“元互動”用戶不再僅僅消費文本,而是為其他用戶預設新的文本,如引入新的角色、將現有對象與新的行為聯系起來,以及在總體上擴展故事世界所提供的行動可能性。她認為,要構成真正的“元互動”,就必須通過編寫代碼和修補源代碼來實現,而不是使用游戲內部工具4。顯然,這一層的用戶相當于亞瑟斯所說的“最終開發者”。這是最難征服的交互性,因為與可以被普遍讀寫的文字相比,編寫、修改代碼始終是困難的。
在從最終開發者到最終使用者這個坐標系統中,先鋒性超文本文學寫作更側重強調用戶的開發者身份。第一部發表于萬維網上的超文本小說《陽光69》(Sunshine69),是一個使用JavaScript編程語言、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并結合層疊樣式表(CSS)等多種技術創作的故事系統,以鏈接、圖片、聲音、文字組成的復合符號文本形式呈現在讀者(最終使用者)面前,讀者需要不斷地翻閱日歷、展開地圖、打開不同角色的手提箱,以期把握這個發生于1969年舊金山灣區、圍繞當時美國流行文化陰暗面展開的歷史故事。這個過程中作者鮑比·拉比德的多重開發者身份不斷凸顯:他是萬維網的開發者、陽光69故事網頁的開發者、《陽光69》故事的開發者……超文本寫作對用戶這種開發者身份的強調意味著作者不僅要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人文情懷,還要懂得甚至精通數字技術并能夠較充分地使用計算機網絡工具,“他們身上體現出了文學精英與技術精英相綜合的特點” 5,是亞瑟斯所說的“聰明的用戶”。這使超文本寫作更接近浪漫主義藝術家的創作,代表了“元程序”深層用戶的權限和能力:寫作過程中更少受到程序和其他用戶的制約和干擾,作者的表達潛力、創造力被不斷激發、釋放,是賽博空間中精英寫作的代表。這種由技術門檻導致的精英化寫作阻礙了超文本文學的流行,拉法奇認為超文本寫作式微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創作難度很大……(超文本寫作)需要創建一個用戶界面,也許還需要一個內容管理系統,甚至創造一個應用程序。突然間,你的抗抑郁藥也不足以讓你起床了”6。
文學網站作為寫作“元程序”的一種形式,為網絡寫作開辟出一條通向大眾化的捷徑(見圖2)。與先鋒性超文本寫作不同,文學網站更側重強調用戶的使用者身份。“榕樹下”最初只是朱威廉搭建的個人寫作“元程序”,因一次突發奇想,他將一個投稿鏈接放在了網頁上,用戶點擊這個鏈接,即可通過電子郵件向“榕樹下”投稿。這個鏈接打開了網絡寫作的潘多拉魔盒,在國內只有不到30萬臺計算機接入國際互聯網的當時,“榕樹下”的獨立IP訪問量迅速突破了10萬。以文學網站、社區為代表的網絡寫作“元程序”為廣大懷有作家夢的草根提供了一條官方出版和網絡精英化寫作之外的路徑。在這里,文學網站的開發者將用戶的文學活動局限于“元程序”的淺表層,用戶必須無條件地接受文學網站創建者給予的代碼和腳本,否則就會被排除在文學網站之外1:受限于技術和運營成本等因素,文學網站、論壇大多以單一文字符號文本作為內容載體,單一文字符號文本因而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流形式;用戶必須遵守網站開發者制定的所有規則,包括對登錄網站、瀏覽網站、發表觀點、進行交流等一系列操作的限制,以及對用戶發表內容隱蔽、持久的影響和左右……網絡文學網站在有形無形中使用戶放棄了部分表達潛力和自由,令超文本寫作失去其立足和進一步發展的土壤,也為網絡自由書寫蒙上一層陰影。但同時用戶也不用再費心去編譯代碼、搭建網站、設置規則,只要能夠敲打鍵盤、操縱鼠標,就能即刻發表文章、加入討論。這種技術上的便宜性、快捷性極大地降低了網絡文學書寫、閱讀、傳播的門檻,助推著新型文學公共空間的建立,使網絡寫作沖破精英圈層,朝著大眾化、平民化、草根化一路狂奔。
這種“元程序”寫作在推動網絡文學大眾化發展的同時,也將網絡文學與文學網站的發展深度綁定。“元程序”寫作產生的文本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單個人作品。不管是超文本寫作還是文學網站寫作,用戶總是在他人提供的明確框架內利用他人規定的明確要素進行創作,文本由不同層次用戶、“元程序”開發者和使用者共同創造,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進行個人生產的“天才”式作者,一個作品從寫成到被讀者閱讀,其中不僅凝結了故事作者的創造性勞動,也包含“元程序”中不同層次用戶的智力成果。在網絡文學人口急劇膨脹的過程中,網絡文學文本成為由作者、網站組織者、網站代碼編寫者等多層主體綜合活動而產生的復雜文本,網絡文學網站、論壇、博客成為網絡文學活動的第一現場和組織中心。
網絡文學發軔之初,網絡文學和網絡文學網站是一體兩面,網絡文學的發展必然伴隨文學網站的發展。但早期建立在免費服務器上由小團體進行日常維護的文學網站總是面臨著組織能力嚴重不足和資金短缺的問題,很難滿足大規模用戶的使用需求。文學網站“龍的天空”創始人樓蘭雪認為“龍的天空”的衰落主要是因為網站存在技術缺陷且缺少財力支持。前者表現為網站在組織能力、技術編寫上的不足,后者則直接體現在面對服務器高昂的購買、租賃、托管費用時個人或小團體運營者的捉襟見肘,這使“龍的天空”時常出現網站卡頓、擁堵甚至崩潰,直接導致“龍的天空”在發展起來之后反而人氣下滑,用戶大規模流失。文學網站帶來的大眾化寫作,使網站的運營、技術與資金間的矛盾更為尖銳,文學青年們出于興趣愛好建立的非營利性文學網站用戶越多,網站越是掙扎于這樣的生存困境中。為此,眾多文學網站從20世紀末開始不斷探索網站盈利模式,但都效果不佳,直到2003年“起點”確立VIP付費閱讀制度。VIP制度為文學網站帶來了可預測、穩定的收入,使其可以穩定地活下去。而對大多數文青、草根用戶來說,一個能夠穩定地活下去的文學網站,是他們在賽博宇宙得以棲身的家園,是實現他們寫作夢、自由夢最觸手可及的路徑。在文學網站發展的探索期,網站每每陷入低谷、面臨生存危機,總會有用戶或自發或響應號召地為網站捐款,大眾的慷慨解囊源自對守護虛擬家園、延續自身文學夢想的迫切渴望,文學網站最初的商業化探索亦源自此。
三 傳播:從“發表焦慮”到“關注焦慮”
在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統御下,發表或出版作品是一個業余作者成為作家的唯一“資格認證裝置”1。2021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作家協會章程》中規定:“凡贊成本會章程,發表和出版過具有一定水平文學作品、理論批評、翻譯作品,或從事文學編輯、教學、組織工作有顯著成績的中國公民,可申請入會。”2百度百科將“作家”定義為以文化創作為業,以寫作為主的文學創作工作者,也指文學領域有功名成就的人。因此,一般能被稱為“作家”者,其作品大都能夠獲得出版發行,歷史悠久。
網絡媒介出現前,一部文學作品想要公開發表,實現公共傳播,尋求印刷出版是唯一的途徑。這一方面是因為印刷出版機構作為文學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與生俱來的“制度賦權”,另一方面是在國家實施嚴格的行業準入制度的前提下,出版機構對正版書號、發行渠道的壟斷實現了出版社的自我賦權。但要出版或者發表一部作品并不容易。一個從事創作的人想要進入文學生產傳播的鏈條之中,“他要先從業余作者開始,不斷地向文學期刊投稿,一旦有幸得到某個文學編輯的賞識,他的作品就更容易發表。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有機會加入相關級別的作家協會。加入作協就意味著成為一個‘合法’的作家,可以把創作作為自己的職業了”3。事實上,大多數作家的發表之路都道阻且長,更多業余作者根本無法進入到這個生產傳播的程序中。這種對發表的執著當然不僅僅是因為現行文學制度下對作家身份的確認,還源自詮釋學和接受美學對讀者閱讀的功能性強調,他們為寫作者們打上了這樣的思想鋼印:作者通過作品誕生于世間,但只有讀者才能為作品注入生的活力。對于印刷媒介時代的文學作品來說,尋求印刷出版是作者誕生、作品價值實現的唯一途徑。故此,對印刷文化體系中的作者來說,發表焦慮是貫穿其寫作全過程的潛在壓力4。這種焦慮在互聯網時代得到了技術性釋放。
盡管現在仍有不少網絡作家將自己的網絡原創小說紙質化出版當成自我價值實現的標準,但這一標準已經不再必要或迫切,失去了印刷媒介時代作為作家“資格認證裝置”的權威地位。究其原因,是因為互聯網打破了印刷出版機構對文學傳播渠道的壟斷。互聯網的交互性、便捷性、隱蔽性、離散性使得網絡構建的文學公共空間與非網絡的公共空間相比,具備出入自由、信息共享、交流民主等技術生成特征,極大地便利了大眾的信息傳播和自主接觸。一切可以上網的人都可以在網上發表自己的作品、評論、觀點,作品可以是游戲之作,評論可以僅是一個表情符號,觀點更無所謂對錯。以往被排除在文學場之外的草根、被埋沒的寫作者獲得了登上舞臺展示自己的機會。作家寧肯的代表作《蒙面之城》曾以自然來稿的方式寄送過《收獲》《花城》《鐘山》《大家》《十月》等文學期刊,皆無回應后無奈發表在網上,引起轟動后才由《當代》雜志選錄發表。互聯網的出現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生產機制培養出的文學青年群體提供了發表的窗口和交流的渠道。至此,困擾人們多年的發表焦慮煙消云散,展現在文學青年、廣大網民眼前的是一片豁然開朗的文學開闊地。
但網絡在消解發表焦慮的同時,又催生了新的關注焦慮。世紀之交,“榕樹下”“六藝藏經閣”“清韻書院”“西祀胡同”“紅袖添香”等一批由文學青年創建的文學網站、論壇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隨之而來的是網絡文學人口和作品數量的激增。1999年僅“榕樹下”一個網站每天都會收到幾百篇投稿。同期網民數亦呈指數級增長,從1997年的62萬人增加至2000年的1690萬人1。與網絡空間眾聲喧嘩相伴而來的是網絡文學作品的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盡管現在看來,早期文學網站的編輯制度作為傳統出版機構編輯制度在網絡空間的延伸,無法完全體現網絡的自由、民主、共享性,但同期一些網絡文學從業者卻立場鮮明地表達過對編輯制度的支持。李尋歡認為網絡文學要有專業的人來作判斷,到底是真好還是假好,同時也需要一個中介幫助用戶降低溝通成本,就像人們在購入電腦時會以品牌為依據判斷電腦性能一樣,編輯的作用也是幫助用戶預判作品的優劣和傾向。陳村說得更直接:“……編輯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在那么多文章里,有誰來看你的?有編輯在的話,他們給你推一下,你就有可能被看見。”2當懷揣文學夢的人們一窩蜂地涌進這個公共廣場,當網絡文學數量爆炸式地增長,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出現了:那么多文章,有誰來看你的文章?
這種關注焦慮源自作為文化公共空間的網絡向人們無限敞開后讀者注意力的匱乏。閱讀活動是一種有目的的定向探索活動,讀者閱讀過程中通過消耗注意力而實現對作品意義的把握、捕捉和認識。但人腦的串行信息處理系統決定了注意力是一種在能量、空間、活力限度上具有有限性的心理資源。對個體來說,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在以消耗注意力為前提的信息獲取、處理過程中,過多的無關信息會成為干擾人感知和思維的噪音,造成注意力的浪費。而注意力作為一種一次性資源,被浪費是無法彌補的3。網絡世界中信息的高效率傳輸和內容的高頻率更新與個體閱讀時間和個人精力的有限性形成了尖銳矛盾,在持續的信息轟炸下,讀者逐漸被消磨掉閱讀的興趣和對深層意義的期待,從而陷入了一種心力交瘁、不忍卒讀的尷尬處境,大多數符號和信息因此難逃被讀者忽略、錯過、誤解的命運。網絡無遠弗屆,窮山距海,以聯通一切為己任,卻也加劇了注意力的浪費和匱乏。王朔曾說過:“網上雖寫得痛快,但讓人也有種寫了白寫的感覺,因為有百兒八十個人看了這個帖子就很不錯了!”一篇發表在網絡上的文章,如果瀏覽量為0,如果無人評論,在接受美學理論家看來,它作為作品的意義和功能依然是缺失的,印刷文學體制下造成的發表焦慮此時已逐漸被關注焦慮所取代。如何被讀者看到,如何能吸引讀者點擊,成為每個上網的文學青年必須面對的問題。
關注焦慮催生了新的網絡作者資格認證裝置,因為作者的身份取決于對作者身份的認可,這是一個社會范疇,而非技術范疇。早期文學論壇奉行一種更為自由的發表態度,形成了以“頂帖”為代表的作品篩選制度。所謂“頂帖”制度,即文筆出色、情節豐富或是內容奇葩、存在爭議的文章,每每引起群體性“拍磚”、評論就會通過讀者和作者不斷頂帖、跟帖、回復,長時間地停留在論壇首頁,進而獲得被更多人看到的機會。與之相對的,大多數文章則成為“頂帖”制度的受害者,在極短時間內就從首頁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創作者如同春蠶吐絲般的創作渴望并不能通過網絡寫作和發表得以紓解,無人關注的網絡寫作是一種網絡潛在寫作,沒有讀者的網絡文學也僅是一種網絡“抽屜文學”。由此,一種基于作品的可見度和討論度的“網絡作者資格認證裝置”逐漸產生。對創作者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章在論壇、社區、聊天室中被頻繁討論、廣泛復制和傳播,積累大量的點擊和評論,進而為自己帶來一定網絡虛擬聲望時,才能在網絡空間中獲得寫作欲望的滿足,獲得對其作者身份的確認。
資格認證并非短暫性制度的體現,而是對具體實踐有著深刻、本質的影響。網絡空間中讀者注意力的相對匱乏和作者關注焦慮之間的矛盾,推動了一個以虛擬聲望為占位資本的網絡文學場的產生。在這個場域內,占有虛擬聲望的讀者群體取代了傳統的編輯、批評家、知名作家,擁有了發現藝術家并封其為“著名藝術家”或“公認藝術家”的話語權,擁有了把某種文學合法化甚至經典化的資格。行動者為實現對虛擬聲望的大量占有,進而在這個游戲空間中獲得對其作家身份的認可,就必須有意無意地向讀者獻媚、示好,盡可能地通俗化和引起轟動亦成為網絡文學寫作的首要原則。加之網絡匿名寫作對主體責任、義務的卸載,使網絡寫作不再推崇天才原創,不再追求文辭精美,轉向了對讀者注意力資源的爭奪。早期網絡監管尚未成熟時,網文拳頭加枕頭題材的泛濫,消遣性類型化小說的蓬勃興起,網絡抄襲糾紛的層出不窮……諸多現象背后始終貫穿著創作者們的關注焦慮,以讀者中心主義為坐標的網絡文學社會學得以確立。正如布迪厄所說,場域內一切形式的資本在特定條件下最終都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并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客觀化1。網絡文學通過線下出版、付費閱讀、影視改編等商業模式,完成了外部權力場對網絡文學場內群選經典、讀者造神(大神作家)這種新“文化合法性”的肯定,是對場域內行動者位置間關系結構的客觀確認,一種關于網絡文學的集體幻象由此獲得多重確立,并為新入場者設立了一個進場參與游戲的準入門檻。這就使得網絡文學從早期代表文學青年、都市白領叛逆精神與小資生活的私人化寫作,轉向了服務于讀者趣味的流量化、類型化寫作,技術預設下網絡空間中作者與讀者之間自由、平等的主體間性關系被改變了。
四、結語
從讀、寫、傳播的微觀視角重審中國網絡文學商業化道路選擇,不難發現,早期論者對超文本“先鋒性”的預設是建立在無視文學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理論與現實的巨大錯位帶來“先鋒性”超文本文學的必然衰微。而單純從網絡文學發展外部環境去考察其商業化轉型,亦無視了網絡文學參與者的主體性,將大眾視為被動的、受文化工業裹挾、逆來順受的烏合之眾,必然陷入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評的困境。新媒介技術最大限度地賦予網絡草根和文學青年們文學自主權、審美自主權,帶來了網絡文學的野蠻生長,并自律地形成制度化的作品創作、篩選、傳播模式,商業化即是在這個過程中萌芽、生發,并與網絡文學交互共生、相伴發展。從這個視角看,很難斷言是商業化選擇了中國網絡文學,還是代表著大眾、草根文學的中國網絡文學選擇了商業化道路。
當前,中國網絡文學的影響已經溢出華語文化圈開始輻射全球,從Wuxiaworld建站到起點國際版上線,標志著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完成了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跨越,實現了從作品出海到文化擴散的歷史性轉變。隨著中國網絡文學生產機制在海外落地生根,中國范式的網絡文學國際化寫作開始蓬勃發展,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某種世界性網絡文學”或許正在醞釀2。在中國網絡文學的影響力不斷擴張的當下,以后視的眼光回看其發展歷程,會發現中國網絡文學的命運在商業化轉型前就已經寫在其基因里。
責任編輯" "余夢瑤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藝審美共同體研究”(18ZDA227)。
作者簡介:周銘悅(1990—),女,西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研究生。
1參見靳瑞霞:《網絡小說產業化芻議》,《東南傳播》2010年第7期;周志雄:《論網絡文學商業化問題》,《中州學刊》2014年第5期。
1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本體論綱》,《文學評論》2004年第6期。
2王治河主編:《后現代主義辭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612—613頁。
3參見韓模永:《從闡釋到反對闡釋——兼論超文本文學的閱讀模式》,《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
4Joyce, Michael,Of Two Minds: Hypertext, Pedagogy, and Poe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p. 193.
5參見Marie-Laure Ryan, “The Interactive Onion: Layers of User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Narrative Texts,” in Ruth Page and Bronwen Thomas,eds., New Narratives: Stories and Storytelling in the Digital Ag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p. 42.
6參見張新軍:《數字時代的敘事學——瑪麗-勞爾·瑞安敘事理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4頁。
7黃鳴奮:《超文本詩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3頁。
1黃鳴奮:《超文本詩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4頁。
2參見單小曦:《“作家中心”·“讀者中心”·“數字交互”——新媒介時代文學寫作方式的媒介文藝學分析》,《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8期。
3參見王祺:《試論網絡超文本文學的閱讀理解》,《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4沃爾夫岡·伊瑟爾:《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周元浦、周寧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47頁。
5參見Miall D S,Dobson T, “Reading Hypertext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Themes Usa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2001, vol.2, no.1, pp.78-91.
6參見Marie-Laure Ryan, “The Interactive Onion: Layers of User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Narrative Texts,” in Ruth Page and Bronwen Thomas,eds., New Narratives: Stories and Storytelling in the Digital Age,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p.52.
1參見謝繼紅、劉華山、吳鵬:《超文本與線性文本中元理解判斷的比較》,《心理學探新》2018年第1期。
2陸揚:《德里達:解構之維》,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92頁。
3崔載溶:《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11年,第24頁。
4Laura Miller:《Booked》,1998年3月15日,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98/03/15/bookend/bookend.html?mcubz=0,2024年3月12日。
1亨利·詹金斯將游戲敘事分為預設敘事(又譯嵌入敘事)和生成敘事(又譯涌現敘事),前者是不可變動的敘事序列,所有看似隨機的事件實際上都是預先設置好的;后者不依賴預設劇情,而是基于角色和世界的持續互動而涌現生成的故事。
2Paul Lafarge:《Why the books future never happened》,2011年10月4日,https://www.salon.com/2011/10/04/return_of_hypertext/ 2011.10.4,2024年3月12日。
1參見Espen J.Aarseth,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3-175.
2Bolter J. David,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Hillsdale,N.J.:Erlbaum, 1991, pp. 158-159.
3參見Espen J.Aarseth,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6.
4參見Marie-Laure Ryan, “The Interactive Onion: Layers of User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Narrative Texts,” in Ruth Page and Bronwen Thomas,eds., New Narratives: Stories and Storytelling in the Digital Ag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p. 59.
5單小曦:《“作家中心”·“讀者中心”·“數字交互”——新媒介時代文學寫作方式的媒介文藝學分析》,《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8期。
6Paul Lafarge: 《Why the books future never happened》,2011年10月4日, https://www.salon.com/2011/10/04/return_of_hypertext/ 2011.10.4,2024年3月12日。
1參見Douglas J Y, The End of Books-or Books without End? Reading Interactive Narrativ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133.
1威廉斯認為“職業”統領著永久性和短暫兩種排列形式(permutations)的制度(institution):一方面,職業制度為想要從事某一行業的人設定了一種資格認證裝置,人們如果跨越了各種各樣的制度障礙(資格考試、學位論文等)獲得資格認證,就可獲得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權。另一方面,獲得資格認證的人們依然要受自己身處的職業制度的管制。在威廉斯看來,獲得某一領域的資格認證,盡管只是一種短暫性制度的體現,但不能將其視為短暫性的外來干擾,而要承認它對主體的工作具有本質性影響。
2《中國作家協會章程》,《文匯報》2021年12月24日,第2版。
3鄭崇選:《網絡時代文學生產機制的生機與困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5期。
4許苗苗:《網絡文學與微時代文學的新質》,《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1期。
1參見《第一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1997年12月1日,https://www.cnnic.net.cn/n4/2022/0401/c88-802.html,2024年3月4日;《第六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2000年7月1日,https://www.cnnic.net.cn/n4/2022/0401/c88-786.html,2024年3月4日。
2邵燕君、肖映萱編:《創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始人訪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6頁。
3參見李志昌:《信息資源和注意力資源的關系——信息社會中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
1參見皮埃爾·布迪厄:《帕斯卡爾式的沉思》,劉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157頁。
2吉云飛:《中國網絡文學國際傳播“枝葉長青”》,《人民日報》2022年1月1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