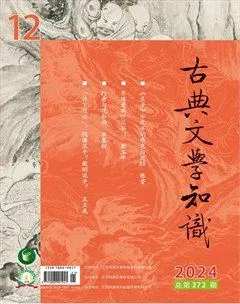“林下巨公”,錢謙益乎?戴明說乎?
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闌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仆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余月耳。”唐詩曰:“與兄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為之咋舌。論者謂潘生狂士,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終身。然不能謂其無理也。
上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姑妄聽之”中的一則內容,表面看似記述文苑士林之逸聞,彰顯潘班的狂放不羈,實則有力烘托了忠貞道義于世間長存的可貴性,正如紀昀所言,“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廢乎?”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林下巨公”的名氏,可能是源于對前輩賢達身份的尊重和聲譽的顧忌,紀昀并未直接道白。今人敘及“林下巨公”時往往將之指向錢謙益,考諸史冊知始作俑者當為晚清陳康祺。陳康祺在著作《郎潛紀聞·三筆》中整段照搬紀曉嵐所述,并在最后落筆接續云:“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字,蓋即明降臣禮部尚書常熟錢謙益也。”同時,陳氏為此掌故還擬了標題“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但若爬羅剔抉,深究細繹,知事實并非如此。
首先來了解一下潘班的生平概況。潘班,字淵度,號盤實,一號芥孫,歲貢生,黃葉道人乃其別號。潘班原籍溧陽,幼時因父北來經商而相隨至滄州。是時清人雖已定鼎中原,鞭勒江南,但寰宇初定,時局未靖,天南地北千里顛簸,往返極為不便;加之當時長蘆都轉鹽運司衙署尚未移至天津,處于運河之岸的滄州盡管也曾受戰火波及,但幸未傷及根本,“鹺商靡集于此,文繡膏粱紛華奢麗,商業繁榮非他處所及”;潘班之父又常年為生計奔波,于是幾乎無暇返鄉,遂落戶安家于滄州。潘班賦性歧嶷,自幼師事劉患骨(按,劉佚,字無逸,號遜志,晚年名夢,號患骨,滄州人,明末諸生,隱居不仕),就學期間,敏而好學,刻苦自勵,學問精進。成年后,潘班體姿修頎,儀度堂堂,雄心矞皇,飄飄有凌云氣,才藝又奇崛峭拔,一時名師宿儒無不以遠大之器期許,奈何青云路偃蹇困頓,屢上屢躓,僅獲貢生,“士林惜焉”。中年的潘班在青紫難獲后痛定思痛,遂掩隱了仕途利祿心性,開始以佯狂之貌表襮于世。從此潘班釋放天性,不再壓抑自我,于放浪形骸里,寄情山水,沉醉酒茗,性情變得愈發疏狂狷介,不拘小節起來。黃葉道人對“林下巨公”之異端即屬此列。然而潘班輕世傲物,放蕩不羈,睥睨一切,于世人前一幅不近人情、和時宜睽違的狷介疏狂面孔,說實話,也許是潘班自我情感的一種放逐,是志不得其舒、才不能其用后的玩世不恭。好友龍震在《玉紅草堂后集散錄》之《題潘淵度卷中樹石》中已有明示:“潘子讀萬卷書而終羈賤,揮千黃金而成清貧。其抑塞磊落之奇不可拔,故披白發、翻白眼、佯狂自放以絕天下之凡民。”由此可見,塵世里所謂的文人清高,多不過是命運坎坷之士面對現實暗淡的棘刺,出于內心抗爭之不屈表達而裝扮上的一層厚厚偽裝而已。潘班傲岸儀態蓋難脫此畛畦。
盡管功名不顯,僅為清初一名中下階層文人士子,但由于潘班學問淵博,才華橫溢,一度“文酒動江城”(語出潘班詩《溪上》。江城者,滄州也),因此作為當時的滄州名士,《滄州志》《天津府志》等史志均有小傳載及。乾隆《滄州志》潘班小傳載:“(潘班)博學工文,尤長詩畫,于書法靡不精究,篆隸行草咸得古人筆妙,詩多溫李體,詞復纖媚有致,畫以水墨寫意,枯木竹石堪與東坡翁頡頏。”晚清金石大家王國均《蘭根草舍詩鈔》之《辛鶴千博雅好古,構舫齋為書畫室,題以二絕》詩,有“潘石當軒妙入神”之句,自注云:“君近得潘班畫一卷,甚佳;潘以畫石得名。”可見州志言及的潘班文墨丹青精湛之能絕非虛譽。
關于潘班生卒年,乾隆《滄州志》記其壽齡:“卒年七十歲”,但無有詳載生辰和作古日期。盡管如此,在和“林下巨公”相戲時,潘班曾言“仆以順治二年九月生”之語,知其生辰年份,即乙酉年(1645),由此可知其作古之年應為康熙五十三年(1714),歲在甲午。
知悉了潘班的行狀后,結合錢謙益的人生事跡進行對比,便可發現二人“連坐”,并發生潘班“屢呼”錢謙益“為兄”的戲謔之事卻大有問題。錢謙益生于明神宗萬歷十年(1582)九月二十六日,歲在壬午。通過紀氏一文知,面對潘班挑戰人格式的咄咄之狀,“林下巨公”十分慍怒,并還擊道:“老夫今七十余矣!”盡管沒有明確具體年齡,但據此可圈定大致發生的時間階段為1652年至1660年間。若此,潘班是時的年齡階段被限定在八歲到十六歲,其間恰是童齔至舞勺之年的青春成長之際,潘班正在親炙于劉患骨門下,居留滄州。據《錢牧齋年譜》(按,清代葛萬里編,一笏齋綠絲欄鈔本)知,是時錢謙益主要活動蹤跡在江南,無過黃河北岸。當然,尚不能排除年少的潘班借隨父南返探親的情況下趁機與錢氏相會的可能(實際此種行為可能性極低),畢竟二人存在著同鄉“溧陽”的最大關聯。假設有此一聚,作為翩翩少年的潘班正處于積聚才學,向前輩大家求學問道的韶華階段,張狂的性格尚未養成,面對錢謙益這樣的鴻儒碩學定不會舍棄虛心求教的大好時機,而刻意捉弄前輩,嘩眾取寵。即使退一萬步,存在譏絀錢謙益之為,但從潘班當時的年齡和社會影響力來看,只能被當作孟浪無知之舉,是小兒豎子的無理取鬧,當不得名士間的逸聞趣事而去傳誦。如若前述尚不能信服,則潘班對“林下巨公”降清的時間“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的提及則是明證。眾所周知,盡管逝后的錢謙益位列乾隆朝編纂的《貳臣傳》之上,亦在《重麟玉冊》(清乾隆初年浙江山陰人沈冰壺撰)中被貶斥為“江浙五不肖”之一,并有“蒙面灌漿人”之詬詈,但錢謙益降清是在順治二年的五月,而非順治元年五月。《牧齋遺事》(《虞陽說苑》本)云:“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齋有難色。”兵臨城下,錢謙益終棄高節于不顧在白下降服。《郎潛紀聞》作者陳康祺只是注意到投降的月份相同,而對具體的年份卻棄之不顧,實是管中窺豹之訛誤。后來者亦不明其中內里,廣泛引用陳氏之說而流播,導致錢牧齋代他人而受無端指摘。
“林下巨公”身份撲朔迷離,可是并非無跡可尋,翻閱康熙《滄州新志》、乾隆《滄州志》等留存文獻史料,按圖索驥,知能夠屈尊紆貴和潘班有文酒之會,同時在天崩地坼之際命運又曲折離奇的懷黃佩紫之“林下巨公”最為吻合者當系戴明說。戴明說,滄州人,字道默,號巖犖,道號定園,天啟七年丁卯科舉人,崇禎七年甲戌科進士,于明季累官至兵科都給事中,入清后于順治年間官至戶部尚書,誥授資政大夫。甲申(1644)之變時,李自成陷京師,崇禎于三月十九日自縊于煤山,一干群臣在國破家亡之際的人生艱難抉擇充分驗證著“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的可貴性。官至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吳橋范景文聽聞龍御歸天,誓不作二姓之臣,投水歿,以身殉明。同為朱明舊臣,定園卻進退失正,靦腆事敵。不久闖王又旋敗,時局愈加動蕩不堪,戴明說只得攜家眷遁歸滄州原籍以避亂。作于康熙庚申五月長至日的陳遇堯《前戶部尚書定園戴公傳》(下文簡稱《戴公傳》)亦有記載,不過為顯者諱而進行了粉飾,“都城之變,公兩繯一溺,皆以太夫人救而奪厥志。公乃護太夫人旋里”。順治元年五月二日,多爾袞率清軍抵達京師,并欲一統天下,于是打著為崇禎復仇的大義之名招攬前明舊臣希圖安定人心,為己所用,戴明說即于此情形下接受招降變身清臣的。《戴公傳》載:“甲申夏,清朝定鼎,驅剿群氛,遣錦衣慰留南下諸臣并疏畿紳以聞。復補兵都,公首疏恭謝復仇大義,即控陳青齊、河北、秦豫善后事。宜悉嘉納。”身在滄州的“畿紳”戴明說于五月歸順新朝,六月正式接受清廷起用,官復“兵科都給事中”原職,贊畫戎機,《閱微草堂筆記》中潘班所言“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之語蓋此而來。
關于戴明說的生卒年,據《滄州戴氏族譜》記載:生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己酉九月二十三日,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丙寅七月十二日,享壽七十八歲。戴明說辭官致仕林田則是在順治十七年(1660),時年五十有二,即“林下巨公”退居生活之伊始。再據“老夫今七十余矣!”一句推斷此活動時間大致應在1679年至1686年間,由此潘班年齡可圈定在35歲至42歲之間,正是潘班人性逐漸恣肆放任的中年階段。當然,潘班對戴明說的僭妄之舉或許為酒興正酣時朋輩間的一時噱頭,但事件本身的發生一方面反映了潘班性情的狂蕩不羈,另一方面也映襯出戴明說因一身事兩朝的行徑違背了儒家所提倡的忠君思想,在有生之年即廣遭物議,只是罕有猶如潘班這般直面戴氏的揭短者而已。
不可否認,同為失節之臣的錢謙益和戴明說二人之間確有相似之處。二人都是一方文化巨擘,或以詩歌文辭見重當世,或以詩文書畫著稱文林。錢謙益自不贅言。戴明說工書畫,善繪山水、墨竹,亦工詩文,有《定圃集》等。《戴公傳》載:“公博學能悟,公余苦心風雅,為詩與王覺斯(鐸)、吳駿公(偉業)、范箕生(士楫)齊名,兼善書畫。”順治十二年(1655)仲冬,戴明說奉旨制詩作畫,深受順治帝隆恩加賞:“蒙賜御畫者七,上載公名者四;及貂冠蟒裘。復賜銀圖章,勒‘米芾畫禪,煙巒如覿,明說克傳,圖章用錫’十六字。”足可側面識見戴氏文藝成就之非凡。再者二人在鼎革之時皆因惜命而變節,進而身后被目之“背君無行之貳臣”,飽受爭議,當事人自身亦介懷于心,存有愧赧之情;另外二人歸隱林泉后皆經歷曲折,一言難盡,然終以高壽而終,亦算“兩截人”中之幸運者了。
星霜荏苒,居諸不息。在歷史滄桑變幻的煙云中,明清兩朝早已湮沒于時代滾滾前行激起的揚沙塵埃中,錢謙益、戴明說抑或潘班等無數的風流人物也皆已作古不在,如“林下巨公為兄”諸般的故事亦成為后世茶余飯后的談資,但由此背后所折射出來的千百年來傳承不息的士人獨立人格和傲岸風骨還是值得共鳴和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