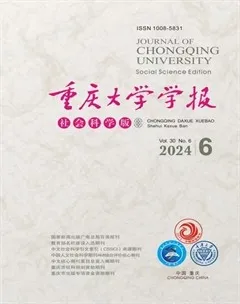論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取證范圍限定
Doi:10.11835/j.issn.1008-5831.fx.2022.09.001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吳桐.論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取證范圍限定[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6):250-262.Doi:10.11835/j.issn.1008-5831.fx.2022.09.001.
Citation Format: WU Tong. Analysis of restrictions on electronic data search and seizure[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6):250-262.Doi:10.11835/j.issn.1008-5831.fx.2022.09.001.
摘要:
電子數據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搜查、扣押的適用邏輯,先搜查后扣押的行為順序已經無法有效應對電子數據的取證活動。為了保障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當前我國相關電子數據取證規范均規定“能夠扣押電子數據原始儲存介質的,原則上應對其進行扣押”。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往往將其理解為“能夠扣押儲存介質的,原則上應扣押電子數據的儲存介質”。這就導致原本是針對電子數據完整性和真實性的規范要求反成為了授權偵查人員實施“概括性扣押”的依據。先概括性扣押再全面搜查成為電子數據取證的實踐常態。雖然概括性取證能夠有效應對電子數據對偵查實踐提出的諸多挑戰,但不受任意搜查、扣押是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享有的基本權利。概括性取證的出現難免會引發電子數據取證方式與搜查、扣押對象特定性要求之間的矛盾沖突。在比較法上,日本和美國刑事訴訟根據其對搜查、扣押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限制概括性扣押和限制概括性搜查這兩種改革方案。前者堅持物理標準對電子數據取證的限制作用,主張應限制偵查人員在物理空間內的扣押行為。這樣既可以保障數據持有人的財產權,也維持了搜查、扣押應是公開偵查措施的基本定位。后者重視事前令狀審查對偵查措施的授權和規制功能。只要偵查行為符合搜查、扣押的標準,就可以通過中立法官簽發搜查、扣押令狀來賦予其正當性,與其行為針對的是有體物還是無體物并無直接關系。限制概括性搜查既能夠保障數據持有人的隱私權不受過度侵犯,也可以通過排除非法證據的制裁后果來威懾違法偵查行為。如何限定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范圍是我國偵查程序法治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在規范層面上,目前電子數據取證的程序規則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對此,我國當前需明確電子數據搜查、扣押與傳統搜查、扣押的關系,構建以限制概括性扣押為重點的電子數據取證程序。具體應區分載體相關性和電子數據相關性,明確電子數據調取中偵查對象的協助義務,重點保障數據持有人的在場權或事后知情權。
關鍵詞:電子數據;概括性扣押;搜查;個人信息保護;知情同意
中圖分類號:D915.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6-0250-13
一、問題緣起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信息已經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交流的必要載體和社會生活的表現形式。數據技術的發展在賦予人們更多自由的同時,權力與權利的非對稱關系也容易導致“數字鴻溝”和“數字弱勢群體”的出現。面對現代科學技術,公民所享利益不均衡是一種常態[1]。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以“數據”換“安全”的慣性思維背后潛藏著公安司法機關過度干預公民基本權利的現實風險。可以說,數據服務的便利性和技術侵權的風險性是科技發展的一體兩面,電子數據取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實現偵查程序法治化的方式雖然存在些許差異,但將科學技術與偵查工作相結合的發展趨勢并無實質不同。隨著信息技術與刑事司法的深度融合,我國偵查活動逐漸有從物理空間向數據空間發展的趨勢。實踐也表明,實體偵查與數字化偵查相輔相成的新格局是當代偵查演變的必由之路[2]。對搜查、扣押而言,電子數據的出現改變了過往的偵查邏輯。電子數據存儲介質通常具有實物形態,并未突破傳統搜查扣押制度,而將數據直接作為搜查對象則是對傳統搜查制度的重大突破[3]。在傳統偵查活動中,搜查和扣押雖是兩個獨立的偵查措施,但通常遵循 “一步式取證”,即偵查機關通過搜查,然后扣押需要收集之物[3]。在電子數據取證中,搜查和扣押則呈現出“兩步式取證”的實踐邏輯。前一階段的搜查、扣押是以發現或占有電子數據儲存介質為目的,后一階段是在儲存介質內發現與案件有關的電子數據。電子數據具有難以直接感知性、海量性、形態易變性等特點,偵查機關實施搜查應當對與犯罪有關的哪些事項進行證明? 應當證明到何種程度? 法律和司法解釋都沒有作出規定[4]。因此,在我國偵查實踐中,除極少數情況外,偵查機關對第一階段搜查發現的儲存介質一般以概括性扣押為原則,第二階段的搜查通常采取的是概括性搜查。然而,任何隨意的、不合理的搜查與扣押,均屬于憲法禁止的行為[5]。偵查權本身的擴張性質可能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和個人信息安全[6]。由此引發了電子數據的概括性取證方式與搜查、扣押對象特定性要求之間的矛盾沖突。
之所以會產生上述問題,一方面是由于電子數據的特殊性使依托于物理空間和因果關系建立起的相關性判斷存在技術困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刑事訴訟及相關法律規定和理論研究對數據權利保障問題的重視程度不足。當前,刑訴學界針對電子數據取證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主題進行:第一是電子數據的真實性。雖然電子數據真實性要求立法機關制定完備的電子數據取證規則,但真實性的關注重點是單一電子數據的客觀性,與之配套的鑒真規則是技術操作規范而不是權利保障規范[7]。因此,電子數據的真實性不僅無法起到限制偵查取證范圍的作用,反而會促使偵查人員進一步強化概括性扣押的實踐運用。為了保障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基本上形成了“以扣押原始儲存介質為原則,以提取電子數據為例外,以打印、拍照、錄像等方式固定為補充”的規則[8]。第二是電子數據的關聯性。有學者認為,相較于真實性而言,電子證據運用于法庭攻防和司法裁判中的特色,其實質在于關聯性[9]。然而,電子數據的證據關聯性更多關注的是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采納與采信,主要發揮著輔助判斷電子數據真實性,提煉法庭證據爭點的功能,并不能直接界定偵查階段電子數據的取證范圍。第三是電子數據取證的程序規則。該主題研究主要探討對電子數據實施搜查、扣押應當遵循哪些原則和制度[4]。問題在于,電子數據取證分為兩個階段,即在物理空間內針對儲存介質的搜查、扣押和在數據空間內針對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究竟應當在第一階段就限制對儲存介質的概括性扣押還是在第二階段限制對電子數據的概括性搜查,或者是兩階段均進行嚴格控制,既有研究并沒有將兩者進行明確區分。
那么,相較于傳統偵查而言,針對電子數據的概括性搜查、扣押是否具有實踐必要性以及存在何種現實風險?域外國家的刑事司法采取何種方式來合理限制電子數據的取證范圍?概括性扣押與概括性搜查中的相關性要件指向的對象及程度是否存在本質區別?我國應當如何構建合理限制電子數據取證范圍的程序適用體系?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考察分析。
二、電子數據取證中概括性搜查、扣押的必要性及風險
在電子數據取證中,概括性取證的優勢在于能夠更為全面地收集證據,提高偵查效率從而發揮打擊犯罪的積極作用。隨之而來的風險是,此種無明確對象的取證方式不免會有過度強化偵查效率,降低搜查、扣押適用門檻的可能性。探討概括性搜查、扣押在電子數據取證中的必要性及風險,可以明確電子數據作為新型證據種類對搜查、扣押范圍提出的特殊要求。
(一)電子數據特征對偵查對象特定性要求的挑戰
相較于傳統的物證、書證而言,電子數據在信息承載量、表現形式以及形成方式上均具有獨特性,這些個體特征以及由個體特征組成的整體特征是促使概括性取證成為偵查實踐常態的重要原因。
首先,電子數據蘊含的信息分為內容信息和系統信息,兩者均具有難以直接感知性和海量性。電子數據是以虛擬數字空間為信息依附,以物理存儲介質為現實設備支撐而存在的[10]。在偵查取證過程中,電子數據的難以直接感知性使偵查人員在物理空間的搜查僅能發現可能與案件事實相關的儲存介質,無法直接判斷其中儲存的電子數據是否也與案件有關,而電子數據儲存內容的海量性又使偵查人員難以在犯罪現場逐一搜查儲存介質。不僅如此,電子數據又具有易變性和變動的可察覺性。電子證據成為一個含有內容、屬性、痕跡的綜合體[11]。偵查人員通過分析電子數據的系統信息可以知悉該電子數據的操作日程,甚至可以恢復已經被篡改或刪除的電子數據。因此,在電子數據取證中,偵查人員對儲存介質的概括性扣押和概括性搜查確有現實的必要。
其次,電子數據對取證主體提出了合法性和技術性的雙重要求,概括性取證成為彌補偵查人員取證需求和技術能力之間落差的應對方式。相較于其他證據而言,電子數據更容易被篡改[12],電子數據取證具有技術性門檻,偵查人員若缺乏相應專業知識支撐,很可能無法有效收集電子數據,甚至會損壞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在具體操作中,任何接觸原始電子數據的行為都有可能造成數據變動,甚至可能導致電子數據被篡改或徹底毀壞。因此,在無法全面提升偵查人員專業能力的現實難題下,允許偵查人員對電子數據進行概括性扣押能夠有效應對電子數據取證的合法性和合技術性的雙重要求。
最后,無論是儲存內容的海量性、難以直接感知性、可變動性還是技術性都并非專屬于某一特定種類的電子數據,而是電子數據的常規特征,概括性取證在電子數據取證中具有普遍性。僅就單一特征而言,即使是實物證據也可能存在儲存內容海量性、難以直接感知性、技術性。如在針對海量文件進行搜查、扣押時,同樣會面臨難以直接感知的問題。在Warden v.Hayden案的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廢除了單純證據規則(Mere Evidence Rule),將扣押范圍從違禁品、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發展至單純證據{Warden v.Hayden,387 U.S.294(1967)}。該判例的潛在影響在于,警察在搜查可以作為證據的文件時,為了能夠找到歸罪性的文字材料,常常需要翻檢與犯罪無關但包含有隱私內容的文件,但只要其已經試圖將對隱私的不必要侵犯降低到最低程度,法院仍會認可其行為[13]。在現場勘查過程中,偵查人員針對指紋、足跡以及DNA數據的提取同樣需要具有專業性,并且偵查人員的不當操作極易導致證據被徹底毀壞且無法復原,相較于電子數據取證而言更具風險性。但電子數據的特殊性在于,上述特征均屬于電子數據的常規特性,任何一個電子數據均存在上述取證風險。甚至當前刑事司法實踐中圍繞著區塊鏈技術還出現了基于區塊鏈基礎生成的原生型數據,基于區塊鏈技術儲存的網絡數據以及基于區塊鏈技術核驗的網絡數據三種新型電子數據[14],進一步提升了偵查人員的取證難度。并且,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意味著在任何類型的案件中都有可能出現電子數據的身影。因此,在電子數據取證中,概括性取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電子數據搜查、扣押中概括性取證的風險
雖然概括性取證能夠有效應對電子數據對偵查實踐提出的挑戰,但也可能對數據持有人的權利造成更為嚴重的干預風險。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概括性搜查降低甚至架空了搜查的適用門檻限制,可能會對數據持有人的隱私權造成不當干預。無論是強制偵查法定主義還是令狀主義均對搜查設定了基礎的適用門檻限制,這是公民不受任意搜查權利的核心要求。在針對實物證據的搜查中,物證的形態可以起到從客觀上限定搜查范圍的作用。然而,這種物理界限卻很難在電子數據取證中發揮作用。從外在形態來看,手機、硬盤以及電腦雖然在物理表現形式上存在差異,但均具備存儲海量電子數據的能力,包含的個人隱私數量遠遠超過傳統的一般物品[15]。因此,概括性取證的實踐必要性并不能消減其可能嚴重干預隱私權的客觀事實。如果一概肯定概括性取證的合理性會使本就缺乏必要限制的偵查裁量權在電子數據取證中再度擴張,不僅有違比例原則,亦無法彰顯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限權法的本質屬性。
第二,概括性扣押忽視了儲存介質和電子數據之間的差異,可能會過度干預數據持有人的財產權。在傳統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圍繞著“嫌疑”對與直接事實或間接事實相關的證據進行收集,不同證據之間呈現出鏈狀的因果關系。但在電子數據取證中,扣押儲存介質的數量直接決定了后續搜查行為的對象范圍。可以說,概括性扣押反映出在數據化時代偵查人員取證邏輯由強因果性到弱相關性的轉變。這種轉變在擴大偵查取證范圍的同時,也使偵查人員需要處理的數據信息呈幾何倍數遞增。并且,概括性扣押針對的并非電子數據本身,而是將儲存介質作為附屬品一并扣押。雖然扣押原始儲存介質能夠有效建立起電子數據的證據保管鏈,從而保障電子數據的真實性。但在實物證據的收集中,物證的證明功效與存在形態具有一體性,電子數據與其依附的儲存介質是可以分離的,并且儲存介質指向的是數據持有人的財產權,電子數據對應的則是隱私權,兩者承載的利益并不相同。作為數據載體的存儲介質而言,其財產性價值遠高于紙張等傳統書證載體[16]。因此,在電子數據取證中,不區分儲存介質與電子數據的概括性扣押可能有混淆不同權利保障邏輯的風險。
總的來說,在傳統偵查活動中,搜查、扣押應當受“場所物品”和“相關性”的雙重限制,偵查人員應當重視搜查目的與場所(包括人身或容器)或物品在物理上的對應關系,在搜查后應當確認該物品是否屬于“令狀上所記載的與案件有關應予以扣押的物品”。在電子數據的搜查、扣押中,雖然場所和物品等物理意義的標準和相關性的事實判斷標準均面臨著諸多難題,但鑒于概括性搜查、扣押是以過度限制公民基本權利作為解決電子數據取證難題的代價,應當謹慎審視該做法的合理限度。因此,如何判斷和限制電子數據取證范圍就成為推進電子數據取證程序法治化的關鍵問題。
三、比較法視野下相關性要件的實踐運用邏輯
在偵查實踐中,電子數據取證存在兩種操作方式:一是偵查人員搜查發現儲存介質后,當場搜查儲存介質內的電子數據并扣押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或儲存介質。二是偵查人員發現儲存介質后,先進行概括性扣押,事后再對內部的電子數據進行搜查。美國和日本兩國根據其對搜查、扣押客體屬性和相關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從限制概括性扣押和限制概括性搜查兩個思路來規范偵查取證范圍的應對方式。日本刑事訴訟主張應以限制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為電子數據取證的規制重點,美國刑事訴訟則主張應通過限制對電子數據本身的概括性搜查來限定偵查取證范圍。在上述兩種方案中,電子數據和儲存介質的相關性內涵、判斷標準均存在差異。
(一)以概括性扣押為限制對象的偵查相關性
日本傳統觀點認為,搜查和扣押應當是以有體物為對象的公開偵查措施,令狀的特定性要求也具有鮮明的物理屬性。如搜查令狀的特定性表現為“管理權單一”,即對屬于同一管理權管轄下的場所或物品應簽發同一搜查令狀[17]。扣押令狀的特定性表現為偵查人員根據令狀記載可以識別、選擇的物品。但相較于以“范圍”為實施對象的搜查而言,偵查人員很難在案件偵辦的初期就事先明確應扣押物品的具體特征。因此,在具體審批過程中,允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簽發概括性記載的扣押令狀[18]。此時,扣押令狀需滿足以下條件方可簽發:偵查對象具有犯罪嫌疑、可能存在與犯罪嫌疑事實相關的證據物以及扣押的必要性[19]。隨著電子數據的出現與發展,以“有體物”為基礎建立的搜查、扣押規則如何應對屬于無體物的電子數據成為困擾日本司法實踐的棘手問題。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奧姆真理教越谷案件的判決中首次肯定了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的正當性,其認為,當根據令狀記載應搜查、扣押的電腦、軟盤中可能存在與案件具有相關性的電子數據,且現場確認數據內容有可能發生損毀等危險時,應當允許偵查人員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20]。該判例的適用重點在于如何解讀“相關性”。對此,日本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在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時,應當將“相關性”理解為偵查相關性,而非證據相關性。
具體而言,第一,相關性具體區分為證據相關性和偵查相關性。證據相關性是審判階段的相關性,其作用在于防止無關證據混淆爭點和造成陪審員的偏見與誤解。偵查相關性則具有限定偵查階段證據收集范圍的功能,其指向的不僅是與犯罪事實相關的積極證據,還包括不成立犯罪的消極證據[21]。第二,在概括性扣押中,相關性的判斷需要權衡偵查的效率性和公民權利保障兩項非認識性要素,而非單純的邏輯關系判斷。只有在復雜案件且存在大量證據或者證據數量較少但在搜查、扣押現場無法逐一判斷時方可進行概括性扣押。偵查相關性的判斷是以客觀事實為基礎的綜合性判斷,其中儲存介質內可能存在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是判斷基礎,現場逐一確認具體內容存在客觀困難或外在影響屬于實施概括性扣押的必要條件[20]。因此,在電子數據取證中,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屬于例外,原則上偵查人員應當在現場確認儲存介質內的具體內容后方可進行扣押。
2011年日本《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電子數據進行了專門規定,進一步豐富了電子數據的取證手段,偵查相關性的判斷也形成了不同主體的區分。本次修法從以下角度對電子數據扣押制度進行了完善。第一,豐富扣押措施的行為方式。《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2款第1項和第2項規定,偵查人員對應予以搜查、扣押的電子數據,可以自行或要求被扣押人員通過復制、印刷、轉存的方式轉移到其他儲存介質并進行扣押。在區分電子數據與儲存介質的同時,規定了偵查對象的協助義務。第二,針對海量儲存介質或儲存介質去向不明的情況創設了“附帶記錄命令的扣押”,該措施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強制性,而是偵查機關基于對偵查對象的信賴要求其主動提供。因此,在行為方式和權利侵害程度上較為柔和。第三,針對云端數據規定了偵查人員可以在搜查現場內實施的遠程扣押型偵查措施。該類電子數據的相關性被限定為“應扣押電子計算機制作、修改的電子數據”。
至此,日本電子數據取證方式,從行為強制程度和取證范圍大小來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層次:第一,偵查人員要求數據持有人提供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該行為的取證范圍最為明確,強制程度最低。第二,偵查人員根據事前簽發的令狀自行復制、提取電子數據,該行為的取證范圍有所擴大,強制程度也隨之提升,但整體上仍受事前令狀的范圍限制。第三,偵查人員在現場發現儲存介質后,搜查并扣押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與附記錄命令的扣押相比,搜查電子儲存介質的做法提高了偵查行為的強制程度。第四,偵查人員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以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該行為的取證范圍最為寬泛且強制程度也達到了最高水平。
日本之所以選擇以“概括性扣押”為對象來限定電子數據的取證范圍,其原因在于:第一,日本刑事訴訟立法者和學者并不想改變搜查、扣押應針對有體物的傳統立場,仍堅持物理場域對電子數據取證的限制作用。這樣既可以保障數據持有人的財產權,也將扣押前的搜查行為置于數據持有人的監督之下,維持了搜查、扣押應是公開偵查措施的行為屬性。第二,在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過程中,扣押儲存介質的范圍往往決定了后續搜查行為的取證范圍,限制電子儲存介質的概括性扣押行為可以有效兼顧財產權和隱私權的保障問題。第三,為了避免電子數據取證中概括性搜查對數據持有人隱私權的侵害,日本《刑事訴訟法》針對數據持有人設定了附記錄命令的扣押以合理限制電子數據的取證范圍,這種做法與郵件扣押的處理方式具有一致性。對此,田口守一教授認為這種新型偵查程序構建了市民參與的協助機制,為今后的刑事司法提供了素材[22]149。事實上,近年日本刑事訴訟學界和司法判例對于新型偵查措施都持“強制偵查法定主義”的解釋論立場,強制偵查法定主義的回歸是日本刑事司法界對多年來吸收借鑒美國刑事訴訟理論的有效性和適當性進行深刻反思后作出的嘗試[23]。但缺點在于,該做法有意避開電子數據搜查可能存在的風險,無論是概括性扣押后的搜查行為還是在實施扣押前的搜查行為均屬于概括性搜查,不對其進行規范似乎有違令狀主義的特定性要求。
(二)以概括性搜查為審查對象的證據相關性
與日本刑事訴訟堅持將搜查、扣押限定在“有體物”的傳統立場不同,美國刑事訴訟很早就放棄了“有體物”或“物理場域”對搜查、扣押的限制作用。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搜查本身就屬于抽象概念,其行為分別指向人身權、財產權以及隱私權三種憲法性權利。因此,電子數據的出現正好契合了以“隱私合理期待”為核心建立起的搜查概念體系,兩者并不存在矛盾沖突。如美國聯邦第九巡回法院認為,針對電子儲存介質進行的電腦鑒識行為屬于實質意義的搜查,應接受與傳統搜查類似的限制{United States v.Cotterman,637 F.3d 1068(9th Cir.2011)}。
在電子數據搜查、扣押中,美國選擇以概括性搜查為規制對象并以證據相關性作為證據排除法則的適用標準。具體而言,偵查人員針對扣押的儲存介質進行搜查必須申請單獨的搜查令狀并且令狀的特定性需要達到明示具體電子數據內容的程度。在如何判斷是否達到明確性的問題上,美國司法實踐存在多種觀點。有觀點認為電子數據的載體是一個封閉容器,根據封閉容器理論,公民對封閉容器內的信息享有隱私合理期待權。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儲存介質內的文件是否應被視為一個單獨的封閉容器?對此,美國聯邦第五巡回法庭曾認為一個存有多個文件的計算機屬于單獨的封閉容器{United States v.Runyan,275 F.3d 449,464-65(5th Cir.2001)}。第十巡回法庭則拒絕偵查機關在缺乏令狀的情況下對計算機進行全面搜查,并警告該行為存在對個體隱私權造成巨大侵害的可能性{United States v.Walser,275 F.3d 981,986(10th Cir.2001)}。上述分歧直接決定了在電子數據搜查、扣押過程中,偵查人員能否基于“一覽無余原則”進行另案扣押。對此,美國多數法院認為,必須將電子數據限定為與特定犯罪有關的文件和信息,一覽無余原則不能為偵查人員明顯超越搜查令狀許可范圍之外的行為提供正當性基礎。但對于電子數據取證中第一階段的扣押儲存介質行為,美國法律職業人員法律教育行政辦公室在其發布的《犯罪偵查中對計算機搜查扣押與電子數據的獲取》指導性文件中建議,一般的搜查方案是追求最迅速地、最少侵入性地、與搜查令中所描述的證據保全相一致、最直接的搜查方案。該搜查方案將允許執法人員在一些案件中對計算機進行現場搜查,同時也允許執法人員在扣押搜查目標計算機后進行非現場審查,關鍵在于靈活性[24]。甚至有偵查學者建議,為了保護數據,應扣押所有計算機硬件、軟件和光盤以及計算機旁所有的手冊和紙張[25]。因此,美國刑事訴訟法并不禁止偵查人員對儲存介質進行概括性扣押,但禁止對儲存介質進行概括性搜查,令狀的特定性要求偵查人員獲取的應當是與特定犯罪事實具有證據相關性的電子數據。
美國選擇以“概括性搜查”為規制對象的原因在于:第一,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搜查對應的權利大多表現為“隱私合理期待權”。在電子數據取證中,當儲存介質本身不屬于違禁品時,其僅是承載電子數據的“容器”,而非證據。因此,可能侵犯隱私權的概括性搜查更契合第四修正案的保護對象。第二,在電子數據取證之前,美國刑事訴訟就曾肯定了針對大規模文件進行概括性扣押的合理性。如針對組織或業務具有欺詐性質的案件,法官對令狀的特定性要求應大幅度降低。這被稱為形成“充滿欺詐性法理”(permeated with fraud)[26]。美國聯邦第四巡回法庭在Moore案的判決中認為,被告人逃稅的行為具有明顯的欺詐性質,應肯定法官簽發的概括性扣押令狀{United States v.Moore,498 Fed.Appx.195(4th Cir.2012)}。因此,電子數據取證的規制重點也不應是針對儲存介質的概括性扣押。第三,限制概括性搜查能夠訴諸證據相關性并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剛性的程序性制裁后果。在司法實踐中,電子數據搜查令狀的授權內容與電子數據搜查實際對象的不匹配是法官否定電子數據可采性的常見原因。因此,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后,限定電子數據搜查的取證范圍既是美國司法人員和技術專家都可以接受的“最佳方案”,也被認為是“兩步式”電子數據取證方式優越性的體現。但缺點在于,一律肯定概括性扣押儲存介質的做法不僅存在嚴重干預數據持有人財產權的可能性,并且,偵查人員在搜查儲存介質內電子數據時,其行為也缺乏公開性,數據持有人只能通過事后非法證據排除申請來質疑該行為的正當性,權利救濟存在滯后性問題。
四、電子數據取證中相關性要件的運用方式和適用程序
偵查人員是否能夠成功發現和收集電子數據已經成為當前偵查取證的關鍵問題。如何限定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范圍則是偵查程序法治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我國目前電子數據取證的程序規制體系尚未在規范層面上得到應有的重視,由電子數據真實性的審查判斷規則走向真實性與合法性并重的取證程序規則是電子數據取證程序法治化的改革目標。在如何限定電子數據取證范圍的問題上,雖然域外國家積累了成功經驗,但也需要注意不同改革方案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和偵查實踐現狀的適應性。具體應在承認和接受普適性法律原則作為電子數據取證程序改革基礎的同時,結合我國國情和法律傳統,采取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從逐步的技術性改良走向制度變革,即相對合理主義[27]。
(一)電子數據取證中相關性要件的規范對象和運用方式
雖然電子數據給世界各國刑事訴訟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具有一致性,但各國在面對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概括性取證風險時采取的應對方式卻并不相同。本文考察的日本與美國就存在限制概括性扣押和限制概括性搜查的區分,其背后反映的是兩種規制邏輯。
日本刑事訴訟重視強制偵查的法律授權依據,即強制偵查法定主義。因此,電子數據的搜查、扣押必須回歸到刑事訴訟條文之中來尋求規范上的正當性。由于電子數據與儲存介質具有一定的依附關系,扣押電子數據被解釋為扣押電子數據的儲存介質并無障礙,但僅針對“電子數據”實施的搜查則很難被納入傳統的搜查概念之中。為了合理限制電子數據取證范圍,日本刑事訴訟法主要是通過規范偵查人員對儲存介質的概括性扣押行為來限制概括性取證。美國刑事訴訟程序重視事前令狀審查對偵查措施的授權和規制功能。只要偵查行為符合搜查、扣押的基本判斷標準,就可以通過中立法官簽發搜查、扣押令狀來賦予其正當性,與其行為針對的是有體物還是無體物并無直接關系。因此,以概括性搜查為規范對象既能夠保障數據持有人的隱私權不受過度侵犯,也可以通過排除非法證據的制裁后果來威懾違法偵查行為。
我國應選擇何種方式來限定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范圍,既需要考慮到我國偵查實踐的客觀情況,也需要評估不同改革方案的成本效益。日本刑事訴訟對電子數據取證的程序規制并沒有脫離傳統偵查的規范框架,基本上是將傳統偵查規則略作調整以適應電子數據取證的特殊性。美國刑事訴訟則通過判例,創制出了一套專門針對電子數據取證的規則體系。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搜查的目的是“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范圍是“身體、物品和其他有關的地方”。扣押的目的是“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對象是財物與文件。從規范表述來看,搜查、扣押的唯一限制就是“物理空間”和“實體物”。至于搜查、扣押對象具體應是什么?是否應設定更為具體的范圍?法律和司法解釋都沒有進行明確規定。因此,在偵查實踐中,由行政機關內部審批授權的搜查和扣押并不存在明確的特定性要求,概括性扣押、概括性搜查均屬常態。可以看出,在電子數據取證的法律規制上,我國當前法律規定存在規制方式滯后和規范體系不協調等問題。那么,在未來的改革方向上,日本刑事訴訟針對概括性扣押的改革方案和美國刑事訴訟針對概括性搜查的改革方案究竟何者更具有現實性則需要評估何者更契合我國現行法律框架和法律傳統。
本文認為,雖然美國當前對電子數據取證的規制更側重于保障數據持有人權利,也對電子數據取證范圍進行了更為嚴格的規制。但對我國而言,該方案的改革成本過高并不適宜作為當前我國限定電子搜查、扣押取證范圍的現實選擇。理由如下:第一,我國的搜查概念與美國搜查概念存在本質區別,美國刑事訴訟中的搜查概念對應著我國的搜查、勘驗、技術偵查、網絡遠程勘驗以及在線提取數據等偵查措施。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應對哪種措施進行修改才能借鑒吸收美國的經驗。這反映出我國遵循的強制偵查法定主義與美國判例造法之間存在的理念差異。第二,當前我國缺乏實質意義上的令狀制度,即使是針對實物證據的搜查、扣押仍存在概括性取證的問題。若參考美國刑事訴訟的做法,應先確立由中立法官簽發令狀的制度,進而在令狀記載上明確電子數據搜查的具體范圍后才能合理限制電子數據取證范圍。我國目前雖然規定搜查、扣押應依據搜查證、扣押證實施,但其僅具有令狀主義中的“書面特征”而已。因此,該做法的權利保障理念雖然先進,但與目前我國的制度現狀落差較大。第三,美國刑事訴訟是以“證據相關性”作為審查是否屬于概括性搜查的標準,進而通過“證據排除法則”來達成制裁威懾效果。這種對搜查、扣押的救濟需要依附于個案審判,并結合剛性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才有實質意義。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違法偵查的約束作用與美國存在明顯差異,借由證據相關性審查的間接規范方式是否有效有待商榷。并且,即使排除規則相當嚴格,該方案仍有以下兩點不足:第一,違法搜查必須有所斬獲,才會成為審查對象,若是撲空的違法搜查,既未取得證據,亦無“排除違法搜查所得證據”的問題;第二,若案件未進入審判程序,則無審查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我國刑事訴訟的基礎概念和制度架構沒有進行變動之前,美國通過證據相關性限制概括性搜查的做法不宜作為當前我國限制電子數據取證范圍的改革方案。日本刑事訴訟的相關改革方案則與我國偵查實踐和制度架構更加契合。
(二)電子數據取證中相關性要件的適用程序與權利保障
針對如何限定電子數據搜查、扣押范圍的問題,日本刑事訴訟的改革經驗對我國的借鑒意義與優勢在于:第一,日本刑事訴訟法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搜查、扣押的定義具有一致性。我國若效仿其做法,以刑事訴訟法已有的搜查、扣押規定為依據限定電子數據的取證范圍,進而以搜查、扣押為基礎整合目前較為混亂的電子數據取證體系,制度改革成本較小,具有效益性。第二,在物理空間的搜查過程中,判明電子數據與案件的相關性可以避免扣押與案件無關的儲存介質和電子數據,從而保障數據持有人的隱私權和財產權,同時在一定條件下賦予概括性扣押正當性也兼顧了偵查效率。第三,雖然日本也要求搜查、扣押應遵循令狀主義,但在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問題上,電子數據搜查被視為扣押的必要處分,并且扣押令狀的記載也并不要求細化到具體文件夾或文件名,而是交由偵查人員裁量判斷。我國目前僅規定了電子數據的扣押,尚未明確電子數據搜查的規范地位。因此,通過相關性判斷電子數據扣押的合法性更契合我國電子數據取證規范體系。若參考日本刑事訴訟的改革方案,我國對電子數據搜查、扣押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規定。
1.明確區分載體相關性和電子數據相關性
當前我國關于電子數據取證的規范存在將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和概括性扣押混淆的傾向。如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刑事電子數據規定》)第5條規定,扣押、封存電子數據原始儲存介質,僅是保護電子數據完整性的方式之一,但第8條則將其上升為電子數據的取證原則。《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以下簡稱《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第16條對無法扣押原始儲存介質的情形進一步予以細化,其中“需通過現場提取電子數據排查可疑儲存介質的”屬于情形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存在兩種適用情形:第一,是現場搜查電子數據后,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屬于電子數據完整性的要求;第二是在不確認電子數據內容的前提下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屬于典型的概括性扣押。在我國,第二種情形屬于電子數據取證的原則,第一種則是例外規定。換言之,當前電子數據收集提取措施的授權規范是奉行一種能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就不必考量其他替代性措施的立法傾向[28]。對此,學界普遍持肯定態度,認為這種做法符合最佳證據規則、主體情況以及電子數據發展的趨勢[7]。
但在電子數據取證中,載體相關性與電子數據相關性存在本質區別。除儲存介質本身就屬于犯罪工具、贓物等情況外,通常情況下儲存介質是作為電子數據的載體而存在的,其本身與案件并無關聯性。因此,偵查人員扣押原始儲存介質主要是基于提高偵查效率和保證電子數據完整性兩種目的,但上述目的能否賦予概括性扣押正當性有待商榷。就提高偵查效率而言,效率價值與人權價值之間本身存在位階差異,尤其是在偵查程序中,提高偵查效率也不應當以過度犧牲數據持有人權利為實現方式。就電子數據完整性而言,概括性扣押和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在行為目的上存在本質不同,概括性扣押是在缺乏明確目標情況下基于全面取證目的而實施,而扣押原始儲存介質屬于保證電子數據完整的方式之一。
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應當區分載體相關性和電子數據相關性。載體相關性屬于一種推定的相關性,也即日本刑事訴訟中的“偵查相關性”。當偵查人員無法明確儲存介質中是否有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時,若現場確認存在技術性困難(數量龐大、缺乏專業取證人員或工具等)或外在影響(犯罪嫌疑人有毀壞電子數據的舉動或可能性)時,可以進行概括性扣押。此時相關性判斷屬于綜合性判斷,日本學者也將其稱為相關性的蓋然性。若不存在上述情況,偵查人員原則上需搜查儲存介質內的電子數據以明確該電子數據是否與案件事實具有相關性,進而篩選應扣押的儲存介質。此時的相關性判斷不可進行蓋然性認定,屬于證據相關性的范疇。因此,對于能夠進行現場搜查的,偵查機關應對儲存介質進行搜查或對儲存介質進行復制后,返還電子數據的儲存介質。不能現場搜查的可以先行扣押儲存介質,在制作鏡像檔后返還儲存介質。
2.細化電子數據調取的相關性和協助義務
由于電子數據的海量性和技術性,無論是電子數據搜查還是扣押均短暫或持續影響到數據持有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生活和經營秩序。因此,設置相關人員的配合、協助義務有助于減少電子數據取證對其利益的不利影響。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如何協調服務商保護客戶信息的義務和協助司法機關義務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如何避免數據持有人惡意毀壞或隱藏電子數據。對此,應從調取電子數據的相關性審查和細化協助義務的執行條件入手進行規范。
《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第41條規定,公安機關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取電子數據應在《調取通知書》上注明調取電子數據的相關信息,并要求被調取人附完整性校驗值等保護電子數據完整性方法說明。其中電子數據的相關信息作為偵查人員的調取對象和范圍,有待進一步予以細化。首先,調取電子數據作為一種間接性偵查措施,應在立案后針對特定的犯罪事實實施,禁止偵查人員調取與犯罪事實無關的電子數據。其次,應區分內容信息和非內容信息。內容信息由于涉及相對人的隱私權不僅應限定在重罪案件,而且應嚴格限定其與案件的相關性,不得進行蓋然性認定。非內容信息涉及相對人的個人信息利益,對其相關性可以進行蓋然性認定。最后,日本刑事訴訟將這種對數據持有人、網絡服務提供者提出的協助義務視為一種間接強制措施。在針對數據持有人時,是否實施該措施應根據信息的種類、數量、記錄媒體的性質、被處分者的態度來綜合判斷[22]144。在我國,針對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調取應在其本人或第三方的監督下實施。
3.保障電子數據取證中相關人員的在場權與知情權
傳統偵查活動中,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權表現為事前出示令狀和過程在場見證。我國電子數據取證的相關規范也對電子數據取證的規定了見證人制度。如《刑事電子數據規定》第14條規定,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制作筆錄并由電子數據持有人簽名或蓋章。第15條規定,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由符合條件的人員擔任見證人。但在偵查實踐中,偵查人員往往是在現場概括性扣押數據載體后,在公安機關內部進行電子數據檢查。因此,數據持有人僅能在搜查、扣押儲存介質時在場,也只能知悉扣押儲存介質的范圍。然而,電子數據取證的關鍵在于,電子數據而非儲存介質。根據《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第43條規定,對扣押的原始儲存介質或者提取的電子數據,需要通過數據恢復、破解、搜索、仿真、關聯、統計、比對等方式,以進一步發現和提取與案件相關的線索和證據時,可以進行電子數據檢查。可以看出,電子數據檢查實際上包括了電子數據搜查。對此,理應保障相關人員的在場權和知情權。但《電子數據取證規則》僅規定在無法使用保護設備且無法制作備份的情況下應進行錄像,顯然將電子數據的完整性置于權利保護之上。
對此,應對不同電子數據取證類型進行規定。如依照上文所提出的改革建議,原則上,電子數據取證應先搜查電子數據進而決定應扣押的儲存介質,那么電子數據搜查與儲存介質扣押均是在同一時間段和同一空間內。此時,電子數據持有人和見證人應在現場監督偵查人員的取證工作。當無法進行現場搜查,僅能概括性扣押時,對于后續的電子數據檢查環節,域外也并未規定需要在場或見證人。因此,此時僅需要對搜查的全過程進行錄音錄像,并及時將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對象告知犯罪嫌疑人和相關人員即可。
結語
如何推進偵查程序法治化是各國刑事訴訟面臨的共同難題,日本刑事訴訟由精密司法向核心司法的司法改革倡議以及美國刑事訴訟曾出現的正當程序革命,均將矛頭指向與公民基本權利密切相關的偵查程序。我國刑事偵查也面臨著相同的法治化困境。若從實現法治化的最終目標來看,正如龍宗智教授所言,只有建立至少能夠覆蓋大部分強制偵查行為的司法審查、司法救濟和司法令狀制度,才能通過這種“治本之舉”,從根本上實現偵查取證程序正當化,完善偵查程序中的人權保障制度[29]。依此邏輯似乎通過令狀主義限制電子數據取證中的概括性搜查行為更加合理,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以令狀主義架構起電子數據搜查制度若想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順利運行并發揮出預期作用,同時需要具備令狀審查的嚴格性和判例規范的靈活性。對我國而言,上述做法更像是一場借由電子數據而引發的顛覆式變革,而非立足于本國現有制度規范的漸進式改良,不宜作為當前階段我國電子數據取證的改革方案。相較于審判、起訴程序而言,偵查程序的法治化應當充分考量我國打擊犯罪的現實需求,這必然是一場本土化、漸進式的改革。
參考文獻:
[1] 宋保振.“數字弱勢群體”權利及其法治化保障[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6):53-64.
[2] 劉品新.論網絡時代偵查制度的創新[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62-73,162.
[3] 謝登科.電子數據偵查取證措施法治化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J].法治研究,2024(5):90-105.
[4] 駱緒剛.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程序的立法構建[J].政治與法律,2015(6):153-161.
[5] 陳永生.電子數據搜查、扣押的法律規制[J].現代法學,2014(5):111-127.
[6] 易延友.刑事訴訟法:規則原理應用[M]. 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308.
[7] 鄭曦.網絡搜查及其規制研究[J].比較法研究,2021(1):21-32.
[8] 謝登科.電子數據的鑒真問題[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5):50-72,174.
[9] 喻海松.刑事電子數據的規制路徑與重點問題[J].環球法律評論,2019(1):35-47.
[10] 劉品新.電子證據的關聯性[J].法學研究,2016(6):175-190.
[11] 朱赟先.電子數據搜查:規定情境與新經驗主義[J].江西社會科學,2021(3):191-201.
[12] 劉品新.論電子證據的理性真實觀[J].法商研究,2018(4):58-70.
[13] 孫瀟琳.我國電子數據搜查扣押之審思[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96-104.
[14] 約書亞·德雷斯勒.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M].吳宏耀,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24.
[15] 劉品新.論區塊鏈證據[J].法學研究,2021(6):130-148.
[16] 陳永生.刑事訴訟中搜查手機的雙重司法審查機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34-37.
[17] 裴煒.論刑事電子取證中的載體扣押[J].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4):120-136.
[18] 安井哲章.搜索差押えの対象の特定[J].法學教室,2019(1):18-21.
[19] 渡辺直行.刑事訴訟法[M].東京:成文堂,2011:53.
[20] 中園江里人.lt;論説gt;電磁的記録媒體の差押え[J].近畿大學法科大學院論集, 2018(14):65-90.
[21] 石山宏樹.捜査段階における差押えの関連性について[J].東京大學法科大學院ローレビュー,2014(9):120-131.
[22] 高橋則夫.曽根威彥先生·田口守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M].東京:成文堂,2014:455.
[23] 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M].張凌,于秀峰,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44-149.
[24] 吳桐.科技定位偵查的制度挑戰與法律規制:以日本GPS偵查案為例的研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6):72-89.
[25] 劉方權.犯罪偵查中對計算機的搜查扣押與電子證據的獲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148.
[26] 埃里克.W.杜特拉.犯罪現場調查[M].張翠玲,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5:341-342.
[27] 太田茂.捜索差押えの特定性の要求に関するアメリカ合衆國連邦裁判所判例の諸法理とその実情[J].比較法學,2015(1):83-128.
[28] 龍宗智.論司法改革中的相對合理主義[J].中國社會科學,1999(2):130-140.
[29] 潘金貴,李國華.我國電子數據收集提取措施對基本權利的干預與立法完善[J].湖南社會科學,2019(5):71-78.
[30] 龍宗智.尋求有效取證與保證權利的平衡:評“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證據規定[J].法學,2016(11):7-14.
Analysis of restrictions on electronic data search and seizure
WU Tong
(Law School,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 data has changed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search and seizure, the way of search firstly and then seizure has been unable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data, China’s relevant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norms provide that “the original storage medium of electronic data should be seized in principle if it could be seized”. In judicial practice, investigators often understand it as “if the storage medium could be seized, electronic data storage medium should be seized in principle”. This leads to the requirements originally aimed at the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electronic data becoming the basis for authorizing investigators to carry out “general seizures”. General seizure firstly and then search comprehensively has become the practice norm for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Although general collection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many challenges posed by electronic data investigation practice, freedom from arbitrary search and seizure is a fundamental right enjoyed by citizen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collec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method of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specificity of search and seizure objects. In comparative jurisdictions, Japanese and American criminal proceedings have formed two reform programs by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search and seizure: one is restricting general seizure and another is restricting general search. The former insists on the role of physical standards in limiting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and advocates that investigators’ seizures in physical space should be restricted. This can protec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data holders and also maintain the basic position that search and seizure should be public investigative measures. The latter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uthorizing and regulating function of prior warrant review on investigative measures. As long as the investigative act meets the criteria of search and seizure, it can be given legitimacy by a neutral judge issuing a warrant for search and seizure, which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whether its objects are tangible or intangible. Limiting general search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privacy of data holders from excessive infringement, but also deter illegal investigation behaviors through the sanctioning consequences of excluding illegal evidence. How to limit the scope of electronic data search and seizure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in the legal process of China’s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At the normative level, the current procedural rules of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have not ye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In this regard, China need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nic data search and seizure and traditional search and seizure, and construct electronic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with emphasis on limiting general seizure. Specific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the relevance of the carrier and the relevance of electronic data, and the obligation to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access should be clarified, with emphasis on safeguarding the right of data holders to be present or to be informed afterwards.
Key words:
electronic data; general seizure; search;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formed consent(責任編輯"劉"琦)
基金項目:2020年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刑事立法行刑競合下的行刑反轉”(20SFB4036)
作者簡介:吳桐,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導師,法學博士,Email:wutonglaw92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