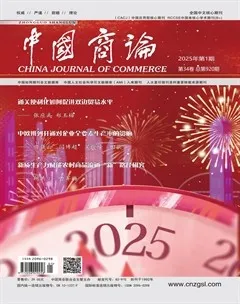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研究




摘要:浙江省作為我國首批數字經濟發展先行示范區之一,連年深化金融數字化改革以提高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助力實體經濟的發展。本文利用2011—2022年浙江省11個地(市)的平衡面板數據,實證研究和探討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機制。結果發現: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存在顯著正向促進作用;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是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的主要中介渠道;異質性分析表明,物資資本投入水平在單向閾值作用下越高,數字普惠金融對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效果越明顯。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實體經濟;平衡面板數據;門檻效應;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3;F06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298(2025)01(a)--05
實體經濟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根基,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壓艙石”。根據黨的二十大報告,必須堅決支持將經濟發展的側重點放在實體經濟上[1]。確保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任務。近年來,實體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2]。2023年10月舉行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了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核心目標的重要性。數字普惠金融被視為金融創新的關鍵方式,如何進一步利用其普惠特點推動實體經濟發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近年來,已有學者探討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例如,魯釗陽等(2023)的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推動中國實體經濟的進步,但并未深層次地闡述其作用機理或潛在差異性的影響因素[3];李林漢等(2022)[4]通過建立系統GMM模型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有積極影響。此外,胡騫文等(2022)[5]也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結合當前研究現狀,國內學者關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經濟影響等多方面問題:從微觀視角來看,包括對居民消費[6]、企業創新的影響。從宏觀視角出發,當前的研究焦點集中于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影響經濟增速、是否可以推動包容性的發展以及其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應等方面。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能夠賦能實體經濟發展,但相關研究缺少深入探討賦能的作用渠道。
浙江省作為數字經濟發展先行示范區,近十年來致力于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本文基于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數據,深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的效應和路徑,結合已有文獻研究,從多角度進一步明晰數字普惠金融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宏微觀主體提出政策建議指導實體經濟發展。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直接作用
國內學者針對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研究較多,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普惠金融的新發展階段,其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值得探討。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縮小金融服務的盲區和死角、擴大服務覆蓋面,彌補了傳統金融“兩頭不助、中間棄之”的缺陷[7],有助于促使企業需求更多地轉化為投資需求,以及實現主要經濟體系的快速增長。普惠金融數字化可以為企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務覆蓋率,有效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更快地獲得融資,增加市場交易[8]。另外,普惠金融數字化可以改善金融保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金融機構引入數字技術可以大大縮短企業融資的提前時間,針對性地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鼓勵企業向前發展[9]。而且,普惠金融數字化還可以改善資金使用和流動規律[9],普惠金融數字化可以使更多的企業獲得融資支持,從而帶動企業更多的加強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據此,本文提出假設:
H1:數字普惠金融能夠賦能實體經濟發展。
1.2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的間接機制分析
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就是創新,推動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只是現階段發展的迫切需求,還是規劃長期未來的重要策略[10]。數字普惠金融提供的多元化、便捷化金融服務有利于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數字金融平臺能將中小企業的融資門檻降至最低,讓更多的企業獲得所需的新興創新資本,從而帶動技術升級和產品創新。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針對性地為企業做市場預判,并實行個性化的金融服務,輔助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數字普惠金融助力企業的研發投入顯著上升,并在新產品研發和技術專利申請領域取得明顯成果,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加強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創、資源共用傳遞,有效提高企業之間的協同創新能力,對促進高質量發展實體經濟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水平和創新能力,從而助推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故本文提出假設:
H2: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科技創新水平賦能實體經濟發展。
實體經濟發展中的數字普惠金融能推動產業升級。一方面,數字化普惠金融可以提供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務,助力實體經濟實現向附加值更高、技術含量更高的新業態新產業的轉變[11];另一方面,在線上兜底的數字普惠金融平臺可以有效整合優化資源配置,吸引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向新興產業、新興領域快速聚集,進一步優化上游的產業結構。據此,本文提出假設:
H3: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賦能實體經濟發展。
2研究設計
2.1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2年浙江省11個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構建面板數據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賦能浙江省地區實體的經濟發展。除數字普惠金融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報告外,相關變量數據均來自《浙江省統計年鑒》,并使用線性插值方法填補缺失值。
2.2變量說明
2.2.1被解釋變量
實體經濟水平(reco)。本文基于浙江省市級層面對實體經濟與數字普惠金融的關系進行宏觀研究,囿于城市層面數據可得性,參考黃群慧(2017)、王儒奇和陶士貴(2022)等的研究,采用第二產業生產總值測度實體經濟發展水平。
2.2.2解釋變量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本文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金融普惠指數作為數字普惠金融的測度指標,這一指標準確度和可信度較高[10]。同時,該指數包含覆蓋深度(difi1)、使用廣度(difi2)和數字化程度(difi3)三個維度指標。
2.2.3中介變量
創新水平(innovation)。創新是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通過提高創新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擴大實體經濟發展途徑,開啟實體經濟發展新篇章。本文選取專利申請授權量的對數值表示該地區創新水平。
產業結構(upgrade)。產業結構升級會間接決定資源分配的高效程度,更合理的產業結構能提升資源利用率及生產力,促進當地實體經濟的發展,本文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來表示當地產業結構。
2.2.4控制變量
除考慮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效應外,實體經濟發展還受宏觀經濟等各方面變量影響。參考相關學者研究,本文選取以下對實體經濟發展造成影響的控制變量:(1)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影響較大,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測度該變量。(2)城鎮化水平(urb)。城鎮化水平對實體經濟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采用城鎮人口除以地區總人口的數值對城鎮化進程加以測度。(3)政府行為(gov)。政府的財政收支會影響當地經濟發展,本文選取地區財政支出與地區財政收入的比值來測度。(4)環境發展(eno)。政策要求地區環境與經濟協同發展,實體經濟也受到環境水平的影響,本文選用城市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來測度。(5)醫療水平(med)。醫療水平的提升促進人力資本的發展,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發展。本文選用地區年末醫院床位數來測度。(6)傳統金融水平(tf)。本文選用地區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生產總值的比值來測度。
對上述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浙江省各地區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均值為16.584,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差距較小,表明浙江省各城市實體經濟發展水平都居于較高水平差異較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變量取對數后均值為5.356,浙江省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雖有差異但差異較小。
2.3模型構建
為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的直接效應,本文構建如下平衡面板數據模型:
recoi,t=α0+α1difii,t+α2controli,t+μi,t+θi,t+εi,t(1)
其中,reco是實體經濟水平;difi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control為控制變量;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μ表示城市(個體)固定效應,θ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
根據研究假設,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中介變量為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為驗證其中介效應,在模型(1)的基礎上拓展構建如下模型:
recoi,t=γ0+γ1difii,t+γ2innovationi,t/upgradei,t+γ3controli,t+μi,t+θi,t+εi,t(2)
innovationi,t/upgradei,t=η0+η1recoi,t+η2controli,t+μi,t+θi,t+εi,t(3)
在上述模型中,中介效應的效果需要結合系數α1、γ1、η1的顯著性進行判斷。
3實證結果分析
3.1浙江省各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根據因素分析的需求,本文先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測試來評估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各層次指標變量的表現。結果顯示,KMO數值達0.706,同時Bartlett球形測試中的卡方值是4592.315,對應的P值低于5%,這表明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對選擇的變量進行評測是合理的。結合因子分析結果,前三個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數值達91.08%,對變量的解釋程度較高。
近年來,浙江省各城市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大幅增長,進一步計算11個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均值和平均增速可知,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處于高質量、高速度發展。杭州作為省會城市,依托于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強大的經濟潛力[12],其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均值為255.512,位居首位。同時,衢州市等均值較低的城市,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增長速度均居于高位,可見浙江省的數字普惠金融在全面迅猛發展,為實體經濟等帶來了積極影響。
3.2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分別運用混合OLS、隨機效應和個體時間雙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直接效應,具體回歸結果見表1(1)—(6)列,其中(2)、(4)、(6)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從核心解釋變量difi的回歸系數來看,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對當地實體經濟發展起到正向作用,并且根據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可知,每單位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能夠提高實體經濟水平約0.180個單位,假設H1得到了驗證。
3.3內生性檢驗
參考謝絢麗等(2018)[10]的方法,本文采用浙江省各地到杭州的球面距離構建地理工具變量,因研究對象為平衡面板數據,僅使用距離作為輔助變量會導致固定效果模型不能被有效地估算。因此,本文采用該球面距離與互聯網普及率進行交乘,把該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檢驗。具體回歸結果見表2列(1),考慮內生性問題后回歸結果依然顯著,說明基準回歸結果可靠。
3.4穩健性檢驗
3.4.1替換回歸模型
本文采用更換計量方法為二階系統GMM進行穩健性檢驗[13],具體回歸結果如表2列(2)所示,其中AR(1)P值為0.07,AR(2)P值為0.92,滿足系統GMM回歸要求,并且通過Hansen檢驗,因此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3.4.2縮短樣本年限
業界普遍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在2013年進入元年,因此本文將樣本時間段縮短為2013—2022年,再次對基準回歸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3列(3),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結果穩健。
4進一步研究
4.1中介效應分析
利用模型(1)—(3)進行中介效應檢驗。首先,對創新水平的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列(1)—(3)。列(2)中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創新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列(3)為數字普惠金融和創新水平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共同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結合相關系數的大小可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會使創新水平提高0.013個單位,從而使實體經濟間接提高0.001個單位,總效應提高0.172個單位。根據表3第(4)—(6)列可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會促使產業結構升級0.179個單位,從而使實體經濟間接提高0.089個單位,總效應提高0.425個單位。因此,中介效應顯著,驗證了假設H2、H3。
4.2異質性分析
4.2.1數字普惠金融二級維度分析
本文選取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下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三個維度[14]來進一步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解釋變量系數均顯著為正,特別在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兩個維度下,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效應最強[15]。
4.2.2固定資本投入的門檻效應
參考錢海章等(2020)把物質化資本水平高低分組進行異質性分析,本文借鑒Hansen(1999)構建門檻效應模型,避免了主觀因素的分類干擾,進一步實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異質性分析,具體的門檻效應模型中,k表示固定資本投入,采用地區固定資本投入的對數值進行測度,r表示門檻值。本文運用Stata軟件進行300次Bootstrap,結果顯示固定資本投入單一門檻的F統計量值為38.22,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雙門檻效應未通過檢驗。固定資本投入在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單一門檻值為11.680[16]。
根據模型回歸結果表4列(4)所示,顯然當固定資本投入大于門檻值后,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加強,系數由原來的0.134增加到0.198,這主要是因為固定資產被視為實體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隨著固定資產投資額度的提高,實體經濟也會隨之增長。因此,數字化普惠金融可以通過評估企業的固定資產狀況來判斷其實體業務的表現,從而更有可能向這些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信貸支持,進一步助力于實體經濟的進步[17]。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11—2022年浙江省11個地級市數據,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浙江省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的效應。研究結論:第一,數字普惠金融是浙江省各地區實體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其通過擴大服務范圍、深化應用及提升數字化水平等方式積極推進該省實體經濟的進步。第二,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傳導效應,實現了對浙江省實體經濟的賦能。第三,固定資本投入的單一門檻效應下,隨著固定資本投入的增加,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正面推動作用也會提升[18]。
針對數字普惠金融如何更好地賦能實體經濟,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一是積極支持和引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特別是在普惠率普及率低、實際運用率不高的地區,政府可通過政策引導以及相關資金扶持等方式,鼓勵其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輔助區域實體經濟實現快速增長。二是持續改善相關政策以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功能,政府需不斷改善有關政策,提振數字金融科技不斷發展,營造有利于數字金融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同時鼓勵金融機構提供更多資源支持給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引導和支持相關產業的轉變。三是對于固定資本對數字普惠金融賦能實體經濟存在的邊際效應問題,政府鼓勵各企業繼續加大對固定資本的投資,尤其是對各種技術創新及產業升級等投資。同時進一步完善金融體系,在給企業提供多渠道融資的同時,降低企業的各種融資成本,更好地激發企業對固定資本投入的需求。四是針對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各種風險進行全面的監管防范。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高速發展,也難以避免地出現各種金融化風險。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做好風險評估與預警,增強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追償不良貸款、查封扣押貿易標的物、終止履行合同等手續,盡量減少不良融資融券,嚴格防范以訛傳訛,確保數字普惠金融的同等待遇穩慎推進。開展區域協同協會。浙江省各地級市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不平衡,可建立區域合作協同機制,資源共享,開展合作,穩定有序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的平衡發展和接入率提升。
參考文獻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J].黨建,2022(11):4-28.
姚登寶,王曉曼,姚玉悅.綠色金融發展對中國宏觀經濟韌性的影響研究[J].山東財經大學學報,2023,35(1):13-26.
魯釗陽,杜雨潼,鄧琳鈺.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J].財會月刊,2023,44(23):128-134.
李林漢,韓明希,侯毅葦.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基于系統GMM與面板門檻模型的實證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22,36(12):14-25.
胡騫文,李湛,張廣財.數字普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效應及異質性研究[J].新金融,2022(10):18-24.
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J].經濟研究,2019,54(8):71-86.
羅茜,王軍,朱杰.數字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22,44(7):72-80.
馬丹,王丹,申琳.數字普惠金融能否改善金融“脫實向虛”局面: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空間杜賓模型分析[J].海南金融,2021(4):67-78.
陸鳳芝,王群勇.數字普惠金融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提升[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34-47.
謝絢麗,沈艷,張皓星,等.數字金融能促進創業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經濟學(季刊),2018,17(4):1557-1580.
江紅莉,蔣鵬程.數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費水平提升和結構優化效應研究[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0,40(10):18-32.
鄒靜,湯蓬濤,聶藝霞.浙江省數字普惠金融的統計測度、時空演化和驅動機制[J].浙江金融,2022(6):3-14.
成學真,龔沁宜.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基于系統GMM模型和中介效應檢驗的分析[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4(3):59-67.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J].經濟學(季刊),2020,19(4):1401-1418.
鄭健壯,虞林震,張魯光.數字普惠金融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浙江省11個地(市)的實證研究[J].商業經濟,2023(3):157-160.
白璐.數字普惠金融、技術創新與實體經濟增長[J].科技和產業,2022,22(11):128-132.
梁榜,張建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激勵創新嗎:來自中國城市和中小企業的證據[J].當代經濟科學,2019,41(5):74-86.
劉京煥,周奎,張勇,等.數字普惠金融、企業生命周期與技術創新[J].統計與決策,2022,38(19):13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