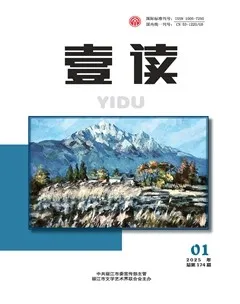大地的脈絡
一
1967年冬,一個普普通通的清晨,晨曦在濃如墨汁的黑夜中緩緩暈開,大地仍然一片晦暗。父親背著簡單的行囊,踏上了去異鄉的路。泥路上結著薄冰,踩上去嘎吱作響,引來一陣有氣無力的狗吠,寥寥幾聲后復歸于平靜。
天空呈一片均勻的鉛灰色,遠山的樹木已被砍伐殆盡,裸露出滿是傷痕的赭紅色的胸膛,看不到一絲綠意。山沖一片寂靜,蒼茫的天地間,只有寒風的呼嘯聲和父親的腳步聲。寂靜讓饑餓的感覺來得稍微慢一些,卻又讓時間變得更漫長。命運總是做出這樣讓人左右為難的安排,自己躲在一隅發笑。寒風肆無忌憚地掠過光禿禿的山脊,穿過死水般寂靜的村莊,一股腦鉆進父親單薄而肥大的衣褲中。父親裹緊了衣服,徒勞地抵抗著寒風的侵襲。出門前喝的一碗粥,早已消化殆盡,轉化為微薄的熱量,肚子又咕咕地抗議起來,越發感覺饑餓。村里的雞打第一次鳴時,祖母就摸黑起床,給父親熬了一小鍋稠粥,又煮了兩個紅薯,讓他帶在路上吃。父親噙著淚把一碗粥喝得干干凈凈,便謊稱自己已飽,起太早吃不進。其實他何嘗不餓,只是那鍋粥已經是一家人一頓的口糧,自己難以下咽。臨行前,祖母又強行將兩個紅薯塞進包裹,此刻正貼著父親的胸膛散發著余溫,這讓他感覺到一絲暖意。常年的饑餓,讓父親尤顯青澀的臉上有著一種病態的蒼白,也讓他的胸膛一如遠山般貧瘠。源自幼年的羸弱無從治愈,就這樣伴隨了父親一生。從我記事起,隔三差五就要給父親涂抹風濕藥。每當他脫下衣服,那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枯瘦如柴的大腿,讓人觸目驚心。
父親這一年二十二歲,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遠行。腳下的路他已經走過無數次,他熟諳路上的每一塊石頭,路邊的每一株野草,今天卻要沿著它去往陌生的地方,去見陌生的人。在公社,父親將和其他新兵匯合,遠赴廣西柳州。祖父輩的赤貧如洗,給了父親一個根正苗紅的身份;在挨饑受凍許多年后,他終于憑借這身份迎來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父親深陷在貧窮的陰影中二十年,到頭來卻要感謝貧窮,生活就是這樣充滿悖論。
木門吱呀一聲,劃破了村莊的寂靜。父親正走到池塘轉角的柳樹下,他回頭看了眼家門,祖母正倚著門抹眼淚。父親沒有掉淚,也來不及傷感;彼時彼刻,父親的內心有一團火在燃燒,這讓他蒼白的臉上有了一絲紅暈。寒風依然凜冽,父親感覺有東西落到臉上,倏忽不見,只剩絲絲涼意。父親抬頭看去,鉛灰色的穹頂不知什么時候撕開了一道口子,隱隱透著光亮,雪花洋洋灑灑落了下來。
父親的背影消失許久后,再次傳來木門吱呀聲。祖母閂了門,蹣跚著走到灶臺前坐下,伴隨她的是無邊的黑暗和無盡的思念。
二
祖母一輩子從未離開過山沖。二十歲那年,她坐著一頂簡陋的小花轎,穿田野,過石橋,翻山林,從鄰村嫁到了小山沖。從此,她在這生兒育女,守望歸人;笑于斯,哭于斯,老于斯,長眠于斯。
故鄉與長沙毗鄰,距首義的武昌不過三百余公里,在中國近代史上,這兩處地方都曾發生過許多激蕩人心的大事、涌現出無數頂天立地的豪杰;但故鄉地處偏僻,既無公路鐵路,也無河運碼頭,僅靠著一條條蜿蜒曲折的小路維系著與外界的聯系。外界的消息總是姍姍來遲,村民的思想轉變更是步履維艱。祖母出生于民國初年,卻因循了裹腳的陋習。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時代,人們以雙腳丈量大地。祖母腿腳不便,如同鳥兒折斷了雙翼。從此,她只能困守一隅,生命的半徑被局限于方圓幾里的小山沖內。她如池塘轉角那棵柳樹般深深扎入故鄉的土壤中,見證著離去和歸來,直至腐朽不堪。
祖母養育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父親是最小的那個。故鄉有句老話,“娘疼滿崽”,這句話在祖母身上尤其為甚。
祖父過世時,父親尚在襁褓之中,排行最長的大伯不過十歲。祖父如一棵大樹轟然倒塌,祖母和她幼小的孩子們暴露于風雨之中,無枝可依。祖母哭干了眼淚,在父親的啼哭聲中回過神來,她看著圍在床邊的孩子們,明白自己必須堅強。由于過度悲傷和營養不足,祖母干癟的乳房已經沒有奶水,情急之下,祖母只好給父親喂米湯。也許是太餓,父親并沒有挑食,從開始的慢慢舔舐,很快就學會了吞咽,這才得以存活。這讓祖母對他的偏愛中又多了一份歉疚。村里人一度勸祖母將小姑媽和父親送人,祖母始終沒有同意。但現實的殘酷,又迫使祖母不得不做出妥協。她托娘家人了解底細后,將大姑媽送去鄰村家境較好的大姑父家當童養媳,離別之際,祖母抱著大姑媽默默流淚,旁邊的孩子們也跟著哭了起來。只有大伯父沒有哭泣,他明白自己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漢,要擔負起照顧母親和弟弟妹妹的重任。他稚嫩的肩膀挑不起重擔,就用自己的雙手給村里人幫忙,以換取成年勞動力幫忙干重活。就這樣靠著一家人的彼此犧牲和相互扶持,以及親戚鄰居的幫襯,祖母終于將幾個孩子都拉扯成人。
這份犧牲,隨著歲月的沉淀和發酵,逐漸吞噬了原本單純的愛。父親去當兵后,頭幾年沒有探親假,寄回的信里逐漸流露出扎根他鄉的念頭。步入暮年的祖母,整日守著灶火沉思,開始無止盡地思索傳宗接代和養老送終的問題。兩個伯父為了支撐起這個家以及種種其他原因,最終都錯過了自己的婚姻,傳宗接代的重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父親身上。在祖母的設想中,兩個伯父為她養老送終;父親也必須回到家鄉娶妻生子,繼承香火,為兩個伯父養老送終;世世代代固守著同一片土地,陷入無窮的輪回。這是祖母的畫地為牢。腿腳的不便限制了祖母的行動,也禁錮了她的思想。她無法理解,也不能忍受,自己最偏愛的滿崽要背離母親和故土,扎根異域他鄉。祖母終于拉緊了手頭的那根線,線的另一頭,在父親腳下,在父親心頭。
在當兵的第五個年頭,父親終于獲得探親的機會。在祖母的安排下,父親與母親見了面,定下了婚期。那一年,父親風華正茂,母親一見傾心;父親心有所思兮在遠方,卻無從抗拒祖母的意志,最終選擇了故鄉的姑娘。次年,母親沿著祖母嫁過來的那條路,嫁到了我們家。簡單的嫁妝中,有一臺老式縫紉機。
三
那是一臺非常漂亮的蝴蝶牌縫紉機,在我的記憶中沉淀出柔和的光澤。機身部分呈漂亮的流線型,黑色烤漆為底,繪有金色圖案,尾部是銀色的上輪,通過皮帶與桌子底下的踏板聯動,也可以手動轉動。桌面呈明黃色,機身嵌于其中,旁邊有一活動擋板,取下時可檢查針線或拆卸機身。桌子坐人的一側有一長而淺的扇形抽屜,沿圓心旋轉而打開或關閉,用來存放直尺等細長的物品。桌子右手側有一方形抽屜,跟桌寬一樣深,里面存放著五顏六色的縫紉線和五花八門的紐扣。桌子下方是鑄鐵制造的桌腳以及腳踏板。
縫紉機靠窗,緊貼著高大的裁剪臺。窗戶是老式的木格支摘窗,朝室內推開,以木棍支撐。
每天晨曦微露之際,母親先撐起窗戶,然后站在裁剪臺前,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格投映在母親臉上,汗毛清晰可見,光影交錯間泛出青春的光澤。她將布料攤開在桌上,一手執直尺,一手拿粉筆,客人的身材尺碼和衣物樣式母親早已成竹在胸,寥寥幾筆,裁剪的脈絡便清晰可循。按劃線裁剪好布料后,母親在縫紉機前坐下,根據布料和衣物類型選擇針頭,調整針距,準備底線。縫紉機大大小小幾十個零件,母親對它們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均了然于胸;她雙手牽引著絲線,飛快地在各個零件間穿梭跳躍,繁復而不凌亂,仿佛彈奏著一曲無聲的樂章。一切就緒后,母親將待縫紉的布料壓置于針下,雙手分置于機針前后,拉抻著布料,隨即踩動腳踏板,根據針速往前勻速推動著衣物。針腳牽引著絲線快速穿梭,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線跡。
這是針腳的痕跡,也是母親的足跡。
在母親的人生軌跡中,她沒有太多機會去遠方。跟祖母一樣,她也成了守望者,年輕時守望丈夫,后來守望兒女。陪伴母親最長久的,反倒是這臺縫紉機。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踩動著腳踏板,在一塊又一塊布料上,在一件又一件衣物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那噠噠的針腳聲,就是母親的腳步聲。
小時候,我們三姐弟的衣服都是母親自己設計裁剪、一針一線縫制成的。等我們進入青春期后,家里雖不寬裕,母親還是盡量給我們買衣服——自己縫制的畢竟不如買的時尚美觀。高考那年,我莫名出現皮膚問題,母親擔心買的衣服含化學纖維,連夜趕制了幾套純棉衣服給我貼身穿。上大學后,這些衣服已經褪色變形,但針線仍然牢固,沒有一處脫線。這些衣服成了我的睡衣,跟隨我的腳步去了很多地方,在異鄉寒冷的冬夜,傳遞著母親的溫暖。
時光也在噠噠聲中流逝。母親的臉上逐漸失去了光澤,又悄悄爬滿了皺紋,這是時光之神吻過母親臉上留下的痕跡。
不知從何時起,噠噠聲響起的時間越來越少,直到再也沒響起過。那臺縫紉機被擱置在母親臥室的陽臺上,每次回家我都會去看一眼,它依然漂亮如昔,光亮如昔——母親仍保持著給它擦拭上油的習慣。我不明白,既然都不用了,為何還要保養,但這個疑問我從沒有問出口。
時間給了我答案。
四
1979年,父親提交了轉業申請,結束了十二年的軍旅生涯。回到故鄉后,他再次站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政府部門和企業單位之間進行選擇。最終,他放棄了去武裝部的機會,進了縣造紙廠,母親的工作也隨之得到安排。殊不知命運的伏筆就此埋下,它像潛伏于深淵中的怪獸,凝視著獨木橋上的人們;等到時機成熟,便露出它猙獰的面孔,將人拽入深淵。
四年后,母親懷了我。迥異于既往的反應告訴母親,這次可能是男孩。全家在短暫的興奮之后,又開始擔心。我上面已有兩個姐姐,按當時的政策,如果再生,父母將雙雙開除;但祖母的殷切期盼,兩個伯父單身的事實,還有母親骨子里的倔強,最終讓我得以問世。全家幾經商議,決定讓母親前往江西姨媽家待產,還未出生的我,就在母親子宮里來了一次長途跋涉。逃離,隨著母親的臍帶,注入我的血液之中。在江西躲避一段時間后,老家依然風平浪靜,父母擔心的告密者并沒有出現,他們的工作得以保全,于是我被送回鄰村小姑媽家,取名為“撿”,欲蓋彌彰地向村人宣稱我是撿來的。
步入九十年代后,下崗潮席卷全國,我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這一年,父親四十九歲,母親四十五歲,正值進退兩難的年紀。他們早已習慣安穩的生活,不能跟村里年輕人一樣,了無牽掛去往南方打工。家里沒了經濟收入,卻還有三個仍在讀書的孩子要供養。無奈之下,他們賣掉了在縣城建的樓房,回到了已經疏遠多年的小山沖。
離開縣城那天,父親蹲在房子前久久不肯起身,他靜靜地看著房子,仿佛要將這一刻永遠定格在他腦海。眼前這幢房子是他和母親共同營建的第一個家,房子的一磚一木,家里的一椅一桌,都是他們胼手砥足、節衣縮食積攢來的。他們見證了這幢房子在大地上扎根,一磚一瓦地成長,最終拔地而起,成為溫馨的家。父親原以為,自己也會像這幢房子一樣扎根于此,終老于斯;而今門口那對大紅燈籠還沒褪色,房子已經易主,自己就要黯然離去。痛苦扭曲了父親的臉,他雙手抱頭,肩膀劇烈地抽動起來。良久,父親緩緩起身,離去的步履蹣跚,他像一棵被連根拔起的大樹,元氣大傷。
故鄉的那條小路依然沒有改變。在馬路上下車,經過樹林,路過幾戶人家,穿過小竹林,在池塘轉角處,一抬頭就望見老宅子一角,只是再也沒有祖母倚門期盼。她已長眠于后山青翠之中。
這年夏天,長期寄養于小姑媽家的我也回到父母身邊,一家人終于團圓。人們背井離鄉,踏上去遠方的路,往往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卻也因此失去一家團聚其樂融融的機會。離別和遷徙,在這個時代成了每個人的宿命。
但葉落歸根,于父母——尤其是父親——而言,是一個極其諷刺的詞語。父親輾轉漂泊數十年,身份幾經轉變,最終卻又回到原點,成為農民,心理上的落差讓他在羞愧之余,又多了幾分怨氣。他將一切歸咎于祖母的安排,后悔自己的選擇,抱怨命運的不公,所有這些情緒,最終轉化為一聲聲嘆息。父親剛回去那幾年,出門干農活都避著人,害怕鄉親們眼神和笑語間隱藏的嘲諷。他木訥寡言,不善交際,昔日的玩伴早已疏遠;母親性格強勢,喜歡念叨,盡力維持著與鄉親們的情誼。在生活的困窘、繁重的勞動和觀念的沖突中,他們的矛盾日益加劇,又顧忌剛回歸家庭的我而刻意隱忍。家里仿佛暴風雨來臨之前的風暴眼,安靜而壓抑。而我,選擇了逃離。
后山郁郁蔥蔥,覆滿了杉木、松樹,以及不知名的矮小灌木。山腳有一條小徑通往山頂,徑旁草木叢中掩映著一座座簡陋的墳塋,連墓碑都少有;越往上,年代越久遠,多數已湮沒于荒草中。中國人生前的富貴,往往體現在死后的墓葬中。山頂依然光禿禿的,裸露出溝壑縱橫的赭紅色堅土,一如父親當年離開時的模樣。雨水沖刷下的細土在溝壑間沉積,從中孕育出一抹抹綠意,默默修復著人類留下的傷痕。
說是山,其實不過是大地微微隆起的土丘,卻可以仰望白云蒼狗,遠眺群山環翠,俯瞰山沖里的屋舍田園。屋舍沿山腳而建,高低錯落。水田、菜園點綴其間,各因地勢,不成方圓。每個山沖都擁抱著一個池塘,這是山沖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池塘邊這條路,于山沖而言,猶如心臟旁的主動脈,最為寬闊。沿池塘堤壩過去,有一小片竹林,再經過幾戶人家,穿過一片樹林,才來到馬路上。馬路蜿蜒曲折,像一條巨蛇匍匐在廣袤的大地上,一直延伸到遙遠的天邊。
路,是大地的脈絡。山沖的路,在門前舍后,在田間地頭,在山根水畔,如同人體最細微的毛細血管,深入軀體最偏遠處,滋養著這片貧瘠的土地。
數百年前,楊氏的先祖歷盡千辛萬苦,在亂世中尋覓到一處與世隔絕的桃源之地,于此辛勤勞作,繁衍生息;數百年后,他們的后裔終于厭倦了這塊土地的貧窮,循著先祖披荊斬棘開辟出來的那條道路紛紛逃離,把青春和熱血獻給了異鄉。
于故鄉而言,父親是一個失敗的逃亡者;但這片土地仍然接納了他,讓他再次扎根于此,汲取賴以生存的養分。我想,也許這才是父親不愿踏足這片土地的真正原因吧。
生命仍在傳承,逃離的故事仍在繼續。
五
每個人都要踏上陌生的路,去往陌生的地方,遇見陌生的人。在路上,是我們這代人的宿命。
大學畢業后,我幾經輾轉,去了深圳那座晝夜不息的城市,每天奔波于臟亂破舊的城中村與富麗堂皇的寫字樓之間,難得有機會閑逛。公交車,是穿梭于兩個世界之間的擺渡者。
每天清晨,休憩了一晚的年輕人從各自的巢穴走出,精神飽滿,穿著自認為最得體的衣衫,穿梭在觸手可及的樓宇之間,如魚群一樣匯聚在路口,沉默而一致地向公交站臺漫游。站臺上人頭攢動,仿佛等待包裝的沙丁魚,等待著下一趟公交車的到來,將他們送往目的地。在商業區和科技園耗盡所有精力后,他們各自步入城市那半透明的黑夜中,背后是燈火通明的寫字樓。他們臉上寫滿了倦容,拖著沉重的軀殼,奔向各自的站臺,等待公交車將他們送往棲息地。這讓我想起許多年前,高中生物老師在黑板上畫下的那幅人體血液循環圖。紅細胞通過毛細血管將氧和營養物質傳輸給組織細胞,帶走二氧化碳和廢物,供人體正常的新陳代謝。許多年后,在異鄉漂泊的兩點一線的生活中,我重溫了這一課。
在日復一日的邂逅中,這些陌生的面孔變得熟悉起來,卻沒有人用言語打破這種默契——我們不過是彼此人生路上的陌生過客而已。時光荏苒,有些老面孔漸漸消失,又有新面孔不斷涌現、逐漸變成老面孔。二十多歲的我曾理所當然地認為,漂泊于城中村擠著公交車去往科技園CBD的肯定是和我一樣的年輕人,直到我看到人群中那張略顯拘謹的臉。他看起來四十多歲,挎著老氣的黑色公文包,廉價的襯衫西褲已然掩蓋不住發福的身軀,吃力地跑在公交車后面,奮力地掙扎于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中,漲紅了臉。我開始憂慮自己的未來,不知道腳下這條路自己能走多久,路的終點又在何處。
有時公交車會晚到許久。小小的站臺滯留的人越來越多,站臺無從立腳了,就往馬路蔓延。沒有人往后站,往后意味著主動放棄。遲到的公交車,下一輛也許會遲到更久;擁擠的公交車,下一輛也許會更擁擠。我們能做的,只有奮力擠上眼下這趟車,仿佛抓住命運賜予的難得機遇。
公交車終于到了,在站臺前緩緩滑行,人潮隨之分流,往前后車門蠕動。我淹沒于人潮中,身不由己;車門突然在我面前打開,背后一股暗流涌來,我被擠上了車,仿佛溺水的人,被水流送回了岸邊。每個人都覺得命運之門朝自己而開,近在咫尺;我們卻被命運的暗流裹挾著前進,身不由己;沒有人知道終點在何處——也許是岸邊,也許是深淵。
2017年,離我初次抵達深圳已經過去十一年。深秋的某個夜晚,加完班的我剛好趕上末班車,車上仍有不少乘客,我在車的后排找到一個位置坐下。我從沒有機會以這樣的視角看我每天經過的道路,這讓我感到無比的陌生。窗外霓虹閃爍,透過車窗在我的眼眸投下斑斕的色彩。天上一輪孤月,隱現于高樓之間,在城市燈光的映射下,顯得無比黯淡。這年六月,旁邊的房價從6萬多飛漲到8萬多,本已同意回深圳的妻改變了主意,決定留在駐地昆明。我不愿放棄深圳的希望和多年的堅持,妻害怕漂泊如浮萍的生活和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就此發生無數次爭執,卻說服不了彼此。直到此夜,我選擇了放棄。
深夜的道路暢通無阻,公交車飛馳在一盞盞路燈之間,猶如穿梭在時光的隧道中。深圳的日與夜在我眼前快速閃過,交織著我和妻各自的念頭,淚水不可抑制地浸潤了我的眼眶,窗外的一切變得模糊起來。我想起了1994年,父親賣掉縣城房子回到山沖的那一天。許多年后,類似的場景又在我的身上上演,這一刻,我才真正懂得父親當時的心情。那是一種被連根拔起、斬斷了與土壤聯系的痛,我們的根須越多、扎根越深,斬斷時就越痛。
在這座城市漂泊十一年后,我終于決定離開,飛往妻所在的城市安定下來。從最初的綠皮火車,到后來的動車高鐵,到現在的飛機,路上的速度越來越快,我離故鄉越來越遠。
六
飛到昆明后,我火速在這邊買了房。房子毗鄰二環,晚上隔窗眺望,高架橋上燈火明亮,車流晝夜不息。從這里到機場,只需半個小時。黃昏日落時,暮色逐漸吞噬了天際,點點閃爍的燈光從機場方向升起,越過一座座樓頂,最終消失在茫茫暮色中。那是飛機在天空留下的足跡。
搬進新房后不久,父母過來小住。在高鐵站看到父親步履蹣跚,我以為他風濕病又犯了。第二天,父親疼痛加劇,我帶他去醫院檢查。在醫生的示意下,父親解開衣服,露出貧瘠的胸膛,灰白的皮膚松松垮垮覆在嶙峋瘦骨上,愈加讓人觸目驚心。醫生按壓了兩處關節,父親痛苦地呻吟起來,扭曲的臉上落下了淚水,堅決不肯再讓醫生碰觸。回去時,我扶著父親站在路口,眼看著滴滴司機從我眼前開過,我一心急松開父親去攔車,他已然站立不穩,摔倒在地。我趕緊去扶父親,他以手撐地,想自己站起來,卻無能為力,只好任我施力將他拉起。父親的嘴唇滲出一絲鮮血,臉上交織著委屈和責備的神情,他囁嚅著,似乎想說什么,終究沒有說出口。
回去的路上,我和父親各自看著窗外,沉默無語。幼時的我已經見證過死亡,那是一種安靜而決絕的告別。我從沒想到,衰老和疾病會如此迅猛地擊垮父親,讓他像一個孩子一樣因疼痛而流淚,因失去攙扶而摔倒。我更沒有意識到,父親已經走到他人生路的盡頭。
回到家后,也許是意識到病情不好,父親執意要回老家治療,我只好向公司請假,陪同父母回到老家,在中醫院辦了住院。父親穩定下來后,催促我回去工作,我跟大姐約定,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她回去照顧父親。
此后父親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一個多月后,我再次回到老家,父親已然陷入昏迷。談及父親的后事時,母親說他想回村里,我默然。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對老家并無特殊的眷戀之情,是祖母的意志與命運的無常,讓原本已經矢志不再回頭的父親再次回到了山沖。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過,我已無從與他印證,這究竟是他的本意,還是母親的意志。
父親走之前,我一直靜靜地坐在病床前看著他。
我看著他的臉,大部分時間因痛苦而扭曲著。但在失去知覺和意識混亂之際,那張充滿苦痛的臉竟奇跡般地舒展開來,洋溢成一朵花兒,口齒不清地跟探病的“客人”告別。在水腫和無意識的加持下,這張笑臉竟莫名地和藹甚至可愛——是的,這是我唯一一次將可愛用于描述我的父親——以至于后來無論我多努力地回想父親的笑容,腦海中卻始終只記得這一刻。
我看著他的臉,痛苦中偶然浮現出暴戾和不甘的陰霾。父親究竟是在詛咒命運,還是不甘病痛?也許兼而有之。這于我其實是更為熟悉的一幕。時代的變革,家庭的不幸,或許還有自己的不爭,讓父親這一輩子過得很壓抑。好不容易熬到暮年,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轉變,父親展顏的日子終于多了起來,病痛卻無情地擊潰了他,這讓他如何甘心?
我看著他的臉,在短暫恢復清醒之際,聽到我的低聲呼喚而自然流露出慈祥和平靜的神情。一直以來,我與父親的關系都很冷淡,以往但凡能坐在一起平靜地聊幾句工作,便是難得的融洽。懂事后我曾草草嘗試與父親和解,稍稍碰壁后便知難而退,轉而敬而遠之。而今在父親彌留之際,兒子卸下冷漠的面具,父親放下威嚴的架子,也算是父子間終于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和解。
暮色漸沉,黑暗終于接管了病房,只有儀器屏幕猶自閃爍著微弱的光亮。我沒有開燈,父親已然承受不住刺眼的燈光。他躺在病床上,胸口輕微起伏著,發出悠長而粗重的呼吸聲。胸口和手腳接滿儀器,將他的生命體征轉化為一條條曲線或數字,投映在屏幕上。父親已完全陷入昏迷,只有儀器上那些冰冷的符號,證明他還活著。我靠著病床,聽著儀器的滴滴聲和父親的呼吸聲,沉沉睡去,隨后又被父親的呻吟聲和儀器的預警聲驚醒。我打開燈,看到父親的臉因痛苦而扭曲成一團,濁淚縱橫,我的心也隨之一緊,不忍再看下去。我讓醫生加大止痛藥的計量,過了半小時后,父親才逐漸恢復平靜,只是眉頭仍然緊鎖,時不時傳來一兩聲輕微的呻吟聲。我關了燈,房間再次被黑暗吞噬,我知道,是時候做出抉擇了。我讓醫生停了白蛋白,只保留止痛藥和鎮靜劑。
父親去世后,我捧著他的骨灰,踏上了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山沖。山林環抱間,一幢幢洋樓拔地而起,一輛輛摩托車、汽車呼嘯而過。腳下原本熟悉的泥路,早已不堪現代化交通工具的重負,終于在前兩年集資修起了水泥路。那條父親和我走過無數次、并最終由此走出山沖的泥路,已走到它生命的盡頭,長眠于混凝土下。
父親的墓地選在后山山腳處,旁邊是通往鄰村的山路。許多年前,祖母和母親沿著這條山路嫁到了我們家。許多年后,這條山路早已無人踏足,湮沒于雜樹蔓草間,仿佛預示著這里就是父親人生路的盡頭。
我想,路也是有生命的。人踏上的第一腳,便賦予路以生命;當人不再踏上這條路時,路的生命從此終結。沒有人真正關心過腳下的路,每個人都是匆匆過客。人們所關心的是,路的終點在哪里,路上會遇到什么樣的人,發生什么樣的事。路也不會關心踩在它身上的每一個人每一匹馬每一輛車,它所關心的只有永恒,天上的白云蒼狗,草木的青黃榮枯,時光的黑白交錯。它目睹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命運的輾轉反復,卻始終一言不發。它不會告訴人們想知道的關于路的那些答案,也不會安撫那些因選錯道路而懊悔痛哭的人們。
處理完父親的喪事后,母親把老宅子鑰匙交給我。我檢視了一遍房間,祖母、伯父、父親的身影一一在我眼前浮現。我輕輕拉上木門,吱呀聲悠遠,黑暗逐漸吞噬了房間。
我坐著表姐夫的車回縣城。汽車經過池塘轉角處時,我最后看了一眼老宅子,掩映在山林與洋樓間,格格不入;我仿佛看到了父親和我站在村民中滿臉堆笑卻無所適從的樣子。很久以前,我跟自己說出來了就不會再回去;現在,我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辦完父親喪事第二天,我和兩個姐姐都匆匆返回各自所在城市,留下母親獨自一人面對孤獨和哀傷。我們都勸她隨我們一起走,但母親堅持要把家里收拾好才放心。她將所有的床上用品都拆洗、曝曬、收納,她把房間每一個角落都擦拭得一塵不染,她檢查每一樣電器、每一個水龍頭、每一把鎖……也許母親這輩子擁有的太少,她珍惜著她所擁有的每一樣東西,大到這套房子,小到那臺縫紉機……
處理完家里的事情后,母親曾來我的城市住過一段時間,我悲哀地發現,家里的每一樣器物,都成為橫亙在母親與城市之間的一道鴻溝。不必說復雜的電器,即便是浴室的水龍頭,母親都需要我教三四次才能記住。看著她笨拙而努力地使用這些器物,我眼前又浮現出母親年輕時在縫紉機上穿針走線的樣子,心里涌起無盡悲涼。
我和妻上班的日子,母親經常坐在窗邊發呆,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我擔心母親的精神狀況,常勸她去小區走走,她卻依然如故。母親不會講普通話,我本以為,她是因為言語不通,所以不想跟其他人交流;正好妻有個同事是我老鄉,她母親也在這邊帶小孩,于是介紹母親和她認識,想著她們語言相通,可以經常走動。母親剛得知有老鄉時也很激動,認識后卻沒了結交的心情,我這才意識到,真正的障礙來自母親內心。她累了。
母親已步入她的暮年,身體器官逐漸衰竭,常年伏案裁剪縫紉對健康的戕害也日益凸顯,母親開始出現頭痛頭暈等癥狀,體檢時醫生告知她腦供血不足。正如母親沉重的雙腳無力支撐她行遠路,她衰老的心臟也無力將血液送往遠方;更何況她身體內的部分血管已經阻塞,就如同后山那條被荒草灌木所湮沒的路,這些血液所不能至的脈絡,其實已經局部死亡。
母親最終決意獨自回去。在她人生的暮年,她已沒有精力去適應陌生的城市生活,記下陌生的道路,認識陌生的人。生性要強的母親,不愿看到自己離開兒女就無所適從的樣子,她要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獨自老去。我知道母親在此并不開心,只好遵從她的意思,安排好回去的行程。
黃昏時,母親打來電話,我站在窗邊接聽。母親的聲音疲憊中帶著愉悅,絮絮叨叨地說著,自己四點多到家了,今天先收拾了臥室,接下來幾天還要大掃除……暮色漸沉,窗外亮起萬家燈火,二環上車流如織,在遠處的某個地方,有一盞燈火等著他們歸去。
責任編輯:尹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