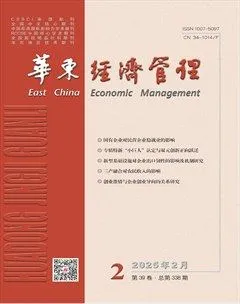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金融化











[摘 要:活躍資本市場、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激活社會生產活力的重中之重。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探索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機制檢驗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發揮積極的“信息治理效應”,可以通過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進而降低企業金融化水平,同時機構投資者持股還存在“成本治理效應”,可以通過降低代理成本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進一步分析發現,企業ESG表現和內部控制質量對機構投資者持股及抑制企業金融化均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研究結論為政府和監管機構引導資金“脫虛向實”以及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啟示。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持股;企業金融化;信息透明度;代理成本;ESG表現;內部控制
中圖分類號:F275;F832.51"""""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7-5097(2025)02-0119-10""" ]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and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FENG Bao, WEN Yuechun, ZHAO Songhui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Revitalizing capital markets and fost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re paramount to invigorating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Utilizing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2012 to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on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significantly curbs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exerts a positiv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effect\", which enhances corporat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consequently reduces financialization levels. Furthermore, there is a \"cost governance effect\", whereby the pres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shareholders diminishes agency costs, thereby restraining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Addition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a company'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along with the quality of its internal control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in curbing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iming to channel investments into the re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at underpin it.
Key words: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gency costs; ESG performance; internal control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體經濟部門產能過剩加上產業鏈低端沖擊,實體投資收益率急劇下滑,虛擬經濟日益膨脹,誘發企業金融化和結構性失衡問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尤甚。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就金融而言,要把金融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促進實體經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勁支撐。
從宏觀視角來看,近年來,廣義貨幣(M2)保持同比高增速的同時,狹義貨幣(M1)同比增速卻處于偏低水平,截至2023年11月底,M1同比增速1.3%,M2同比增速10%,大量資金滯留于金融層面運作,未能高效進入實體經濟循環;從微觀層面來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攀升,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自2008年來持續下滑;從數據層面來看,金融面的“資產荒”與實體面的“資金荒”仍存在矛盾,工業制造業企業擴大生產經營的意愿不強,融資需求疲弱,流動性淤積在金融體系內部,導致不同產品間多層嵌套,在我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背景下,相繼引發并加劇了市場脫實向虛[1]。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的關鍵階段,政府實施寬松貨幣政策所釋放的流動性并未完全惠澤實體企業經濟投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企業“脫實向虛”、實體企業“空心化”等現象。參考蔡明榮和任世馳(2014)[2]以及劉偉和曹瑜強(2018)[3]的研究,本文將企業金融化定義為非金融企業減少實體經濟投資而增加金融資產(包括房地產等具有投資屬性的商品)投資的趨勢,主要指微觀企業將可得資金注入虛擬化程度較高的金融資產項目的投資行為。
自我國股權分置改革完成,資本市場邁向健康發展階段,機構投資者市場不斷擴大。金融市場的發展、公司內部董事會治理功能的缺陷和法律制度的變遷為機構投資者行使積極股東主義提供了有利環境[4]。然而,機構投資者能否發揮公司治理效應存在爭議,主要有三種假說:①有效監督假說:機構投資者作為企業重要股東,其行為對企業的發展和治理具有重要影響。李爭光等(2014)[5]研究發現,穩定型機構投資者會指導公司管理層關注長期盈利,是公司的有效監督者。Chen等(2007)[6]認為,更穩定的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有更好的了解,對管理層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比其他機構人員更有可能參與監督工作。②無效監督假說:機構投資者以交易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短視行為,不干預公司治理。龍振海(2010)[7]研究發現,在減弱非市場化因素干擾的背景下,受制于本身機制設計的機構投資者并不能顯著提升目標公司的價值。③利益合謀假說:機構投資者與公司管理層為了侵占分散的小股東利益而進行合謀。例如,在公司績效較差面臨經營危機的時候,機構投資者往往會利用手中職權干預決策,維護與現任高管的“合謀”關系[8]。
從機構投資者“積極治理效應”視角來看,周泰云等(2021)[9]研究表明,機構交叉持股等監督以及約束管理者金融投機行為的非正式制度發揮了協同治理效應,抑制企業金融化。Wang和Mao(2022)[10]研究發現,非金融企業金融化與企業風險承擔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這種負向關聯在機構所有權較低的企業中更為明顯。張云等(2024)[11]認為,機構投資者會為了長遠利益而主動干預公司決策,向管理層施壓從而使其專注企業長遠發展,進而減少金融資產投資。然而,也有學者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可能會加劇企業金融化程度。謝家智等(2014)[12]實證研究發現,我國機構投資者加劇了上市公司經營行為的短期化。陸蓉和蘭袁(2020)[13]發現,在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較高的企業中,機構投資者持股能顯著提高企業金融化程度。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是否能夠發揮積極治理作用并未得出一致結論,且未對其作用機制進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從積極股東視角出發,選取2012—2022年我國上市公司樣本數據,研究分析機構投資者持股如何影響企業金融化,深入挖掘其內在影響機制。同時,探究在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激勵下,企業ESG表現以及內部控制質量環境是否對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產生調節作用,旨在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防范化解過度金融化負面危機提供經驗證據。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在理論層面上,拓展對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的理解。同時,通過2012—2022年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數據分析,驗證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的顯著抑制作用,為政府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提供參考。第二,分析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存在的“信息治理效應”和“成本治理效應”,揭示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機制,為理論上和實踐中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機構投資者持股來調控企業行為提供創新路徑。第三,研究ESG表現和內部控制在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中的調節作用,為全面理解ESG的可持續表現作用以及內控質量環境的影響提供參考。此外,對于機構投資者而言,為將ESG納入投資決策中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
金融化趨勢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和資金來源。然而,過度金融化可能會導致企業忽視主業發展,過度追求短期收益,產生“投資替代”效應,進而影響企業業績[14],甚至可能會引發股價崩盤風險[15]。機構投資者作為企業的重要股東,其行為和決策對企業的發展和治理結構具有重要影響,被視為公司治理中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之一。
基于委托代理理論,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對稱,往往會導致管理層采取一些不利于股東和企業長期發展的行為或決策。機構投資者通過持股成為企業股東,與管理層形成委托代理關系,利用專業能力和資源優勢,對企業進行持續監督,降低管理層過度金融化的風險[16]。同時,機構投資者通過持股參與公司治理,引入股權激勵、業績獎金等長期激勵措施,優化管理層的激勵機制,使管理層的利益與股東利益趨于一致,緩解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沖突[17],激勵管理層更加關注企業的長期發展。
基于成本效益理論,機構投資者會充分考慮項目的投資成本,包括資金成本、時間成本、人力成本等。通過精確估算,可以發現企業金融化帶來的潛在風險,進而調整投資策略,通過構建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實現風險分散和收益最大化。在投資組合中,機構投資者會考慮不同資產之間的相關性、風險和收益等特點,實現整體投資組合的最優化[18]。通過降低金融資產的配置比重,增加實物資產的配置比重,實現投資組合的優化,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另外,機構投資者還通過向資本市場或行業內部共享信息和協調分配資源的方式,幫助企業拓寬融資渠道,降低對金融市場的依賴程度,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由此,提出假設1。
H1:機構投資者持股抑制企業金融化水平。
(二)信息治理效應:機構投資者持股通過提升信息透明度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
機構投資者持股不僅帶來了對企業運營的持續監督,還通過對股價和管理層決策的影響,形成市場壓力,迫使企業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此外,他們積極倡導和推廣最佳的信息披露實踐,并通過與監管機構、審計師和分析師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推動企業提升信息透明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為投資者和市場提供了更多關于企業運營、財務狀況和未來規劃的信息,使得管理層在作決策時更加謹慎,減少過度金融化的傾向,從而對企業金融化行為產生直接的監督和約束作用。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投資者能夠基于更全面的信息進行投資決策,從而促使企業回歸實體經濟的本質。此外,透明的信息環境有助于提高分析師的預測準確性[19],加強市場紀律和外部治理,如分析師、評級機構和競爭對手的監督,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施加壓力。同時,改善投資者預期和降低融資成本,引導管理層和投資者關注企業的長期價值創造。這些因素共同產生間接影響和市場激勵,抑制企業金融化行為。由此,提出假設2。
H2:機構投資者持股通過提升信息透明度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
(三)成本治理效應:機構投資者持股通過降低代理成本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
機構投資者持股向市場傳遞了關于企業治理和經營策略的信號。如果管理層的行為與股東利益相悖,機構投資者可以通過增持或減持股票來影響股價,進而對管理層構成約束,迫使其調整決策,以降低代理成本[20]。同時,這也改善了公司的治理結構并加強了對管理層的監督。這種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有助于促使管理層專注于企業的主營業務和長期增長,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
從資源配置層面來看,代理成本的降低對企業而言,意味著管理層能夠更加高效地配置企業資源。在代理成本較低的環境下,高管等實際控制人能夠根據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和市場需求,將有限的資源投入最具潛力和價值的投資項目中,以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這種高效的資源配置不僅有助于企業專注核心業務,減少對金融資產的依賴,還能夠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增強其市場競爭力。通過高效的資源配置,企業能夠更好地把握市場機遇,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降低金融投資,并增加實體投資,從而降低金融化的傾向[21]。綜上,提出假設3。
H3:機構投資者持股通過降低代理成本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
(四)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ESG表現的調節效應
近年來,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各國開始重視對環境的保護。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投資者開始關注ESG投資,企業社會責任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機構投資者能夠關注到企業ESG責任表現,且具有明顯的ESG責任偏好,ESG表現良好的企業可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信心和信任。因此,機構投資者更愿意溢價投資ESG表現良好的企業,以實現長期價值的創造和投資回報的持續增長[22]。
具備良好ESG表現的企業通常高度關注環境,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并在公司治理方面展現出較強的意愿和較多的投入[23]。對于ESG表現越好的企業,機構投資者對其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大。一方面,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不斷提高,其與企業內部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的契合度越來越高,企業內部信息越來越透明,各利益相關者均以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為導向,受此影響,機構投資者在作出決策行為時也會考慮企業長期價值而減少短視行為,從而將更多可用資源和信息投放至實體經濟領域,減少金融化趨勢。另一方面,企業ESG表現較好也意味著各項信息披露更加完善,隨著ESG信息披露的增加,機構投資者能夠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環境表現、社會表現和治理表現,尤其是對企業金融化產生影響更大的公司治理信息,通過深入分析從而更全面地評估企業的價值和風險,有助于機構投資者作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并減少對企業金融化的過度關注。由此,提出假設4。
H4:ESG表現在機構投資者持股抑制企業金融化過程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五)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內控質量的調節效應
內部控制質量是衡量企業管理和風險控制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有效的內部控制,企業能夠顯著降低違規行為發生的風險,從而提高財務報告的披露質量。樹成琳(2016)[24]研究發現,良好的內部控制質量可以顯著降低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在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健全且執行有效的情況下,可以實現降低財務舞弊和錯誤的風險、提高財務報告質量的目的。另外,內部控制質量也影響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通過加強企業內部的監督和制約機制,確保企業遵守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減少因“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給投資者帶來的損失,最終為投資者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和安全的投資環境。這對機構投資者而言,意味著投資風險和監督成本相對較低,同時能夠實現更好的運營業績和更高的公司價值[25]。由此,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市場,形成強大的內部監督效應,防止管理層因個人利益而過度金融化,從而損害企業的長期發展潛力。由此,提出假設5。
H5:內部控制質量在機構投資者持股抑制企業金融化過程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2012—2022年中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搜集數據時,按照2012年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剔除ST、ST*和金融業的上市公司。同時,為了消除極端值干擾,增加研究結果的說服力和可信度,本文還剔除了主要變量存在缺失值和異常值的數據,并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經過篩選,共得到3 634個上市公司22 440個樣本觀測值。本文數據大部分來自國泰安和Wind數據庫,內部控制數據來自迪博首創的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與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數據庫,所采用的數據處理軟件為Stata 17.0。
(二)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企業金融化(firmF)
本文選擇金融資產包括:短期投資凈額、長期股權投資凈額、長期債券投資凈額、持有至到期投資凈額、投資性房地產凈額、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凈額,加總求和之后并用總資產標準化來衡量企業金融化程度。
2. 解釋變量: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
機構投資者持股指機構投資者持有流通股的份額占總股份的比例。包括:基金持股比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銀行持股比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持股比例和其他機構持股比例等。
3. 中介變量
(1)信息透明度(Opaque)
本文借鑒Hutton等(2009)[26]和王化成等(2015)[27]的方法,通過修正的Jones模型從會計盈余透明度的視角來衡量信息透明度指標。公司財務報表中,會計盈余是核心的財務特征,其透明度受多種因素影響,如盈余的過度激進、對損失的回避以及盈余平滑等,盈余管理行為是導致會計盈余不透明的關鍵因素。而操控性應計項目被廣泛用于衡量企業盈余管理的程度[28]。因此,分析操控性應計項目可以幫助判斷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若企業的操控性應計項目波動顯著,且其絕對值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通常表明,存在較大的盈余操縱風險,會導致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下降。因此,本文采用企業近三年內操控性應計項目的絕對值累計總和(Opaque)來衡量企業信息透明度。Opaque值越高,表明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越差。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步:運用公式(1)進行分年度分行業回歸,接著,將估算回歸系數代入公式(2),計算操控性應計項目DisAcc。
[TACitTAi,t?1=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PPEitTAi,t?1+εit] (1)
[DisAccit=TACitTAi,t?1?α11TAi,t?1+α2?salesit??AritTAi,t?1+α3PPEitTAi,t?1] (2)
其中:[TACit]代表公司i在第t期的總體應計利潤;[TAi,t?1]表示公司i在第t-1期期末的總資產;[?salesit]指的是公司i在第t期的銷售收入增加量;[PPEit]表示公司i在第t期的固定資產原始價值;[?Arit]表示公司i在第t期的應收賬款增加額。
第二步:將第一步計算所得的操控性應計項目(DisAcc)代入公式(3),從而計算出信息透明度(Opaque)。
[Opaque=AbsDisAcci,t?1+AbsDisAcci,t?2+AbsDisAcci,t?3] (3)
(2)代理成本(AC)
參照Singh和Davidson(2003)[29]的做法,本文以企業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之和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衡量代理成本。
4. 調節變量
(1)企業ESG表現(ln ESG)
本文采用華證ESG評級數據庫,該ESG評級從“C、CC、CCC、B、BB、BBB、A、AA、AAA”,依次對其進行賦值“1-9”,數值越大,則表明企業ESG表現越好。接著,為了方便展開比較和數據分析,對其評分取自然對數得到本文所用的調節變量ln ESG指標。
(2)內部控制質量(Control)
本文的第二個調節變量為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指標Control。本文參考迪博公司公布的內部控制質量評分,將其千分化之后加1取自然對數,即得到所用的內部控制質量指數,該指標數值越大,表明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越高,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和體系越規范,越能有效地實現其預期目標。
5. 控制變量
除解釋變量和中介變量之外,還存在一些外生因素可能對被解釋變量產生影響,需要在回歸分析中加以綜合控制和考慮。因此,本文參考彭俞超等(2018)[30]的研究,從企業層面出發,引入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企業成長性(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產權性質(SOE)和企業價值(firmvalue)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定義說明見表1所列。
(三)模型設定
為了探索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金融化之間存在的關系,驗證H1,本文構建模型如下:
[firmFit=α+β1,tInstit+β2,t∑control+∑Yeart+Indi+εit] (4)
其中:firmF衡量了企業金融化程度;Inst衡量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強度;i表示上市企業樣本個體;t表示時間;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Year和Ind分別表示控制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式(4)為本文的基準計量模型。
在式(2)的基礎上,為了考察可能存在的中介機制,驗證H2和H3,本文引入中介變量信息透明度(Opaque)和代理成本(AC),并進一步構建模型(5)至模型(8)如下:
[Opaqueit=α+β1,tInstit+ β2,t∑controls+Yeart+Indi+εit] (5)
[firmFit=α+β1,tInstit+β2,tOpaqueit+β3,t∑controls+Yeart+Indi+εit] (6)
[ACit=α+β1,tInstit+β2,t∑controls+Yeart+Indi+εit] (7)
[firmFit=α+β1,tInstit+β2,tACit+β3,t∑controls+Yeart+Indi+εit] (8)
(四)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所列。從表2可以看出,企業金融化(firmF)的均值為0.080,中位數為0.040,最小值為0.000,最大值為0.543,標準差為0.105,可看出樣本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的均值為0.453,中位數為0.469,標準差為0.247,數據離散程度較小。從整體而言,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相對穩定。其他變量的統計結果也均與Liu等(2023)[31]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四、實證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3展示了基準回歸結果。由列(1)、列(2)可以看出,在未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后,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1和-0.013,并且兩者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驗證了H1,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可以抑制企業金融化。且機構投資者持股每增加一個標準差,企業金融化會減少0.003。表3列(3)和列(4)考慮了不同融資約束程度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其中,融資約束小的上市企業機構投資者持股回歸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但融資約束大的企業機構投資者持股回歸系數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融資約束小的企業通常具有更為完善的內部治理結構和風險控制機制,完善的機制遏制了企業進行高風險金融投資的能力或意愿,機構投資者更傾向于穩健的投資策略,認為過度金融化會分散企業資源,影響主營業務發展。因此,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的增加,其會通過行使股東權利或與管理層溝通來降低企業的金融化程度。而在融資約束較大的企業中,機構投資者面臨更大的投資風險和不確定性,導致投資者在投資決策中更加注重短期收益和風險控制,最終沒有足夠的動機或能力去影響企業的金融化決策。
(二)內生性檢驗
1. 工具變量法
為解決基準回歸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關系,同時緩解遺漏變量等相關問題,本文擬構造工具變量以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參考溫軍和馮根福(2012)[32]、梁上坤(2018)[33]和杜劍等(2023)[34]的研究,選用滬深300指數虛擬變量(HS300)構造機構投資者持股的工具變量,若屬于滬深300指數所涵蓋公司,則HS300為1,否則為0。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來進一步識別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在相關性方面,滬深300指數的成分股通常是市場上表現較為突出、規模較大且股票流動性較好的公司,這些公司往往具有較高的市場關注度和較完善的治理結構,是機構投資者更加偏好的標的,因而與機構投資者持股存在一定關聯性;在外生性方面,滬深300指數的構建是基于對上市公司市值和股票流動性的加權排名,排名前300的企業被納入其中。上市公司通過對自身的市值和流動性進行操控以入選該指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企業金融化不屬于決定公司能否被納入HS300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該指數具有一定外生性與隨機性。
表4列(1)與列(2)為2SLS回歸結果。列(1)為第一階段,工具變量HS300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工具變量HS300與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在回歸中,LM統計量為731.320,對應的P值為0.000,通過了不可識別檢驗;且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量的值為815.690,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為740.720,均大于Stock-Yogo檢驗10%的臨界值16.38。因此,拒絕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說明本研究所構造的工具變量合理可靠。列(2)為第二階段,可以發現工具變量HS300對于企業金融化的回歸系數為負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進一步驗證了H1。
2. 被解釋變量一階差分
考慮企業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參考Anderson和Hsiao(1981)[35]的做法,在回歸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一期滯后項(laglnfinan),即擬對企業金融化相鄰時期做差分所構成的對時間序列的轉換,即用后一時期減去前一時期,進而緩解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回歸結果見表4列(3),Inst的回歸系數為-0.359,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說明基準回歸結果相對可靠。
3. 解釋變量滯后一期
為避免上一期行為對當期解釋變量產生影響,對研究結果造成干擾,本文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滯后一期后進行分析,結果見表4列(4),L1_Inst的回歸系數為-0.016,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從以上檢驗結果來看,在綜合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進一步驗證了H1。
(三)穩健性檢驗
1. 替換被解釋變量
為了對企業金融化進行更加全面的描述,本文去掉長期股權投資凈額對企業金融化指標計算并重新進行回歸得到被解釋變量firmF1,作為企業金融化的替代變量。重新回歸后的檢驗結果見表5列(1),Inst的回歸系數為-0.005,且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即機構投資者持股會抑制企業金融化,說明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2. 更換研究方法
參照杜勇等(2019)[36]的做法,使用截尾回歸模型(即Tobit模型)將原本的OLS回歸方法調整為Tobit回歸,以更好地捕捉金融化程度為0的企業在模型中的特征。回歸結果見表5列(2),機構投資者持股回歸系數為-0.015,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與基準回歸檢驗結果基本一致。
3. 剔除新冠疫情的影響
新冠疫情使我國實體企業的生產經營受到較大影響。為剔除新冠疫情對實證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刪除2020年及之后的樣本,結果見表5列(3)。由結果可知,Inst的回歸系數為-0.018,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基準回歸結論是穩健的。
五、進一步分析
(一)中介機制檢驗
1. 信息治理效應
為驗證H2,本文使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表6第(1)、第(2)列匯報了逐步回歸法下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Sobel檢驗結果顯示,Z統計量的值為-3.120,對應的P值為0.000。表6列(1)中Inst的回歸系數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顯著提升了信息透明度。表6列(2)表明,在加入中介變量信息透明度之后,Inst 回歸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系數-0.012的絕對值小于表3列(2)中Inst回歸系數-0.013的絕對值。這說明,信息透明度在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中起到中介作用。為進一步驗證中介效應是否存在且顯著,本文使用Bootstrap法進一步檢驗,在原始樣本中進行1 000次抽樣并求出Bootstrap置信區間。Bootstrap檢驗結果顯示,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應顯著。H2得以驗證。
2. 成本治理效應
為驗證H3,本文同樣使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表6第(3)、第(4)列匯報了檢驗結果。Sobel檢驗結果顯示,Z統計量的值為-5.624,對應的P值為0.000。列(3)中Inst的回歸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顯著降低了代理成本。在列(4)中,當代理成本作為中介變量加入模型后,Inst回歸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系數-0.011的絕對值小于基準回歸中Inst回歸系數-0.013的絕對值。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通過降低代理成本,進而有效地抑制了企業的金融化行為,代理成本在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金融化之間起到中介作用。接著,運用Bootstrap法進一步驗證,結果發現,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即代理成本在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金融化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H3得以驗證。
(二)調節效應檢驗
1. 模型設定
為驗證ESG表現和內部控制質量是否對機構投資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存在調節效應,本文構建模型如下:
[firmFit=α+β1,tInstit+β2,tln ESGit+β3,tln ESGit×Instit+β4,t∑controls+Yeart+Indi+εit] (9)
[firmFit=α+β1,tInstit+β2,tControlit+β3,tControlit×Instit+β4,t∑controls+Yeart+Indi+εit] (10)
其中,模型(9)中的[ln ESGit×Instit]以及模型(10)中的[Controlit×Instit]為調節變量和解釋變量的交乘項。若模型(9)和模型(10)中的[β3,t]均顯著為正,則說明調節效應存在,H4和H5得以驗證。
2. 調節渠道一:ESG表現
根據上文分析,ESG表現在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之間存在調節效應,表7列(1)和列(2)報告了ESG表現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當機構投資者發揮治理作用時,機構投資者持股和企業ESG表現的交乘項[ln ESGit×Instit]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企業ESG表現越好,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強。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機構投資者在持有企業股票時,會通過各種方式來影響企業決策,例如,通過股東提案等方式來促進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ESG表現好的企業往往更傾向于透明、完整的信息披露。這種高質量的信息披露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性,使機構投資者能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真實價值和潛在風險。因此,機構投資者更愿意持有這些企業的股票,從而降低企業過度金融化的可能性。以上結果驗證H4成立。
3. 調節渠道二:內部控制質量
表7列(3)和列(4)驗證了內部控制質量環境是否存在調節效應,當機構投資者發揮治理作用時,機構投資者持股和內部控制質量的交乘項[Controlit×Instit]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環境越好,機構投資者持股抑制企業金融化的作用程度越大。原因在于,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體系可以規范財務管理流程,確保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防止和發現財務報表中的錯報、漏報和舞弊行為,保障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同時減少信息不對稱,提升機構投資者治理決策的可靠性,從而精準抑制企業金融化行為。以上結果驗證H5成立。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運用2012—2022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了機構投資者持股如何影響企業金融化,深入挖掘兩者間存在的影響機制。同時,探討企業ESG表現以及內部控制質量環境是否產生調節作用。研究結果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顯著抑制企業金融化。機制檢驗發現,在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的過程中,信息透明度和代理成本分別基于“信息治理效應”和“成本治理效應”起到中介作用,即機構投資者持股可以通過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降低代理成本從而抑制企業金融化。進一步分析發現,企業ESG表現和內部控制質量在機構投資者持股影響企業金融化過程中均有正向調節作用,即企業ESG表現越好,內部控制質量越高,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于抑制企業金融化的程度也就越強。基于以上結論,得出如下啟示:
第一,機構投資者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的參與者,其決策和行為對市場穩定和企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政府及相關金融監督管理局應加大鼓勵力度,引導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要求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通過提供稅收優惠、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激勵機構投資者持有更多股份并積極參與公司決策。同時,建立健全機構投資者退出機制,保障機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以便其在必要時采取退出威脅策略,從而對企業形成積極有效的監督,關注和參與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建立,進而促進資本市場穩定發展以及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
第二,建立健全統一的ESG信息披露標準,“軟硬兼備”規范企業披露ESG相關信息,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和透明度,為機構投資者提供全面、準確的數據支持。監管機構也應加強對企業內部控制體系的監管,推動企業建立健全內部控制體系,提高內部控制質量,降低企業“脫虛向實”的風險。
第三,建立健全資本市場監管體系和投資者保護機制,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實體企業提供全方位的資本市場服務。同時,通過政策引導和激勵機制,鼓勵各類投資者將資金投向實體企業,特別是創新型、成長型的中小企業。加大對科技創新、制造業等領域的支持力度,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杜直前,趙春艷.大數據政策治理企業“脫實向虛”——基于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準自然實驗[J].華東經濟管理,2024,38(5):1-12.
[2]蔡明榮,任世馳.企業金融化:一項研究綜述[J].財經科學,2014(7):41-51.
[3]劉偉,曹瑜強.機構投資者驅動實體經濟“脫實向虛”了嗎[J].財貿經濟,2018,39(12):80-94.
[4]伊志宏,李艷麗.機構投資者的公司治理角色:一個文獻綜述[J].管理評論,2013,25(5):60-71.
[5]李爭光,趙西卜,曹豐,等.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績效——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4,29(5):77-87.
[6]CHEN X,HARFORD J,LI K. Monitoring:Which Institutions Matter?[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6(2):279-305.
[7]龍振海.機構投資者與公司價值關系研究——來自上市公司要約收購的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10,13(4):35-43.
[8]潘越,戴亦一,魏詩琪.機構投資者與上市公司“合謀”了嗎:基于高管非自愿變更與繼任選擇事件的分析[J].南開管理評論,2011,14(2):69-81.
[9]周泰云,邢斐,李根麗.機構交叉持股與企業金融化:促進還是抑制[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1,41(12):33-48.
[10]WANG J H,MAO N. Does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Promote or Prohibit Corporate Risk-Taking?[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2022,58(7):1913-1924.
[11]張云,呂纖,韓云.機構投資者驅動企業綠色治理:監督效應與內在機理[J].管理世界,2024,40(4):197-221.
[12]謝家智,江源,王文濤.什么驅動了制造業金融化投資行為——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8(4):23-29.
[13]陸蓉,蘭袁.中國式融資融券制度安排與實體企業金融投資[J].經濟管理,2020,42(8):155-170.
[14]杜勇,張歡,陳建英.金融化對實體企業未來主業發展的影響:促進還是抑制[J].中國工業經濟,2017(12):113-131.
[15]彭俞超,倪驍然,沈吉.企業“脫實向虛”與金融市場穩定——基于股價崩盤風險的視角[J].經濟研究,2018,53(10):50-66.
[16]吳曉暉,姜彥福.解決第二類委托代理問題的雙核心理論觀點研究[J].經濟管理,2006(24):23-27.
[17]馮曉晴,文雯.國有機構投資者持股能提升企業投資效率嗎?[J].經濟管理,2022,44(1):65-84.
[18]張萌,魏云捷,張永珅.機構投資者、私有信息傳遞與投資—股價敏感性——基于盈余公告期間凈買入的研究[J].管理評論,2022,34(5):265-280.
[19]王亞平,劉慧龍,吳聯生.信息透明度、機構投資者與股價同步性[J].金融研究,2009(12):162-174.
[20]王謹樂,史永東.機構投資者、代理成本與公司價值——基于隨機前沿模型及門檻回歸的實證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16,24(7):155-162.
[21]湯龍,李光武,吳海軍.社保基金持股能促進企業脫虛向實嗎?——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金融論壇,2024,29(5):3-13,25.
[22]周方召,潘婉穎,付輝.上市公司ESG責任表現與機構投資者持股偏好——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科學決策,2020(11):15-41.
[23]侯聰聰,胡國強,韋琳.ESG評級能抑制企業金融化嗎?[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39(1):53-64.
[24]樹成琳.內部控制、內部人交易與信息不對稱[J].當代財經,2016(8):121-129.
[25]BROWN L D,CAYLOR M 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25(4):409-434.
[26]HUTTON A P,MARCUS A,TEHRANIAN H. Opaque Financial Reports,R2,and Crash Risk[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4(1):67-86.
[27]王化成,曹豐,葉康濤.監督還是掏空: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價崩盤風險[J].管理世界,2015(2):45-57,187.
[28]袁知柱,王澤燊,郝文瀚.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行為選擇[J].管理科學,2014,27(5):104-119.
[29]SINGH M,DAVIDSON W N. Agency Costs,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J]. Journal of Banking amp; Finance,2003,27(5):793-816.
[30]彭俞超,韓珣,李建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金融化[J].中國工業經濟,2018(1):137-155.
[31]LIU Y,LIU J Z,ZHANG L C. Enterprise Financialization and Ramp;D Innovation:A Case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 Electronic Research Archive,2023,31(5):2447-2471.
[32]溫軍,馮根福.異質機構、企業性質與自主創新[J].經濟研究,2012,47(3):53-64.
[33]梁上坤.機構投資者持股會影響公司費用粘性嗎?[J].管理世界,2018,34(12):133-148.
[34]杜劍,滕丹妮,楊楊.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刺激企業氣候轉型風險信息披露嗎?——基于企業年報文本的實證分析[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3,43(6):56-77.
[35]ANDERSON T W,HSIAO C. Estimation of Dynamic Models with Error Component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1,76(375):598-606.
[36]杜勇,謝瑾,陳建英.CEO金融背景與實體企業金融化[J].中國工業經濟,2019(5):136-154.
[責任編輯:劉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