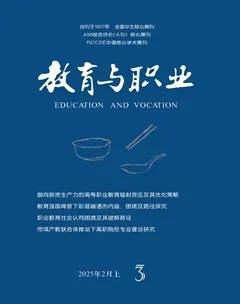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及其破解路徑

[摘要]高質(zhì)量發(fā)展職業(yè)教育必須提升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可度。針對當(dāng)前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可度不高、吸引力不足等現(xiàn)實問題,基于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對影響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三要素——教育制度、勞動力市場、企業(yè)和職業(yè)教育的知識基礎(chǔ)——技術(shù)知識和抽象知識等兩方面因素,對職業(yè)教育認(rèn)同危機(jī)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邏輯做出解釋。基于此,需要確立職業(yè)教育專業(yè)的排他性與自主性,逐步改革現(xiàn)代企業(yè)的組織結(jié)構(gòu)方式,堅實職業(yè)教育技術(shù)知識的基礎(chǔ)地位,提升職業(yè)教育對抽象知識的管轄權(quán),以有效化解職業(yè)教育認(rèn)同危機(jī)。
[關(guān)鍵詞]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認(rèn)同困境;職業(yè)系統(tǒng)
[作者簡介]王佳昕(1994- ),女,山西長治人,山西師范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學(xué)院,講師,博士。(山西" 太原" 030031)王志遠(yuǎn)(1993- ),男,甘肅隴西人,陜西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部,助理研究員,博士。(陜西 西安" 710062)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2022年度教育學(xué)重點項目“國際比較視野下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的提升策略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AJA220023,項目主持人:祁占勇)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5)03-0022-08
當(dāng)前,我國正處于立足新發(fā)展階段、貫徹新發(fā)展理念、構(gòu)建新發(fā)展格局的重大戰(zhàn)略時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和經(jīng)濟(jì)增長方式轉(zhuǎn)變急需大量技術(shù)技能人才。然而,長期以來,社會對職業(yè)教育的認(rèn)同感普遍不強(qiáng),職業(yè)學(xué)校 “就業(yè)不體面”“技術(shù)技能人才地位不高”等刻板印象,阻礙了職業(yè)教育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是在社會大眾對職業(yè)教育目標(biāo)、性質(zhì)、內(nèi)容、社會價值與個體意義以及職業(yè)教育生態(tài)環(huán)境等都極為熟悉和認(rèn)可的情況下形成的,既不是單純?yōu)榱俗非缶蜆I(yè)、升學(xué)等,也不是一味迎合當(dāng)事人、媒體或公眾而偏離職業(yè)教育的過程[1]。增強(qiáng)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是高質(zhì)量階段我國職業(yè)教育改革發(fā)展的重要目標(biāo),對于提升職業(yè)教育吸引力、促進(jìn)我國職業(yè)教育高質(zhì)量發(fā)展、服務(wù)區(qū)域和國家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本研究基于職業(yè)系統(tǒng)的視角,嘗試對職業(yè)教育認(rèn)同困境背后產(chǎn)生的社會制度因素進(jìn)行挖掘,并就破解職業(yè)教育認(rèn)同困境提出相應(yīng)的建議。
一、基于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的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分析框架
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由美國當(dāng)代社會學(xué)家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提出,他認(rèn)為職業(yè)的本質(zhì)是工作的合法性規(guī)制和專業(yè)知識的制度化過程。首先,工作的合法性規(guī)制體現(xiàn)為社會規(guī)制和文化規(guī)制。文化規(guī)制是在工作中與業(yè)務(wù)同時出現(xiàn)的,由扎根于根本價值之中的正式知識加以合法化。當(dāng)職業(yè)在公共領(lǐng)域、法律領(lǐng)域和工作場所中主動提出管轄權(quán)要求時,社會規(guī)制就出現(xiàn)了。社會規(guī)制和文化規(guī)制是排他性的[2]。一個職業(yè)要想獲得管轄權(quán),就只有兩種辦法——尋找管轄權(quán)空位或者去與他人爭奪。因此,各種職業(yè)就構(gòu)成了一個相互依賴的系統(tǒng),一個職業(yè)的變動必然會影響其他職業(yè)。其次,專業(yè)知識的制度化過程體現(xiàn)在技術(shù)本身和職業(yè)變遷過程中產(chǎn)生的抽象知識合法化的過程。職業(yè)的演進(jìn)是職業(yè)之間不斷競爭導(dǎo)致的結(jié)果,一種職業(yè)的地位與其兩種規(guī)制方式息息相關(guān)。一是技術(shù)本身,群體通過壟斷技術(shù)實現(xiàn)對某行業(yè)的規(guī)制。換言之,技術(shù)生長、發(fā)展的直接動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需求,職業(yè)的生長空間與技術(shù)的市場需求存在直接聯(lián)系。二是抽象知識,對行業(yè)的規(guī)制是通過規(guī)制催生實踐技術(shù)的抽象知識來實現(xiàn)的。抽象知識有利于增強(qiáng)在一個競爭性職業(yè)體系內(nèi)部的生存機(jī)會,抽象知識使得職業(yè)得以幸存,能夠增強(qiáng)一個職業(yè)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與延續(xù)性。一個職業(yè)要在職業(yè)系統(tǒng)中存活,就離不開一定程度的抽象知識,且抽象程度隨著時間和地點而變化。
質(zhì)言之,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一方面關(guān)注影響職業(yè)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另一方面關(guān)注影響職業(yè)發(fā)展的知識基礎(chǔ)。通過考察與職業(yè)發(fā)展最緊密相關(guān)的兩大要素——社會環(huán)境與知識基礎(chǔ)的制度化過程,可以探明職業(yè)在社會中的地位、職業(yè)發(fā)展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guān)系[3]。職業(yè)教育作為與職業(yè)變遷與發(fā)展最緊密的教育類型,“工作”“職業(yè)”和“教育”始終是貫穿職業(yè)教育理論體系的三個核心概念[4]。作為體現(xiàn)技術(shù)技能人才能力的各類職業(yè)工作,既規(guī)范了職業(yè)勞動的維度,又規(guī)范了職業(yè)教育的標(biāo)準(zhǔn),是檢驗與判斷職業(yè)教育質(zhì)量的最直接體現(xiàn)。基于此,本文借助職業(yè)系統(tǒng)的核心觀點來建構(gòu)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從更為宏觀、整體和系統(tǒng)化的視角來考察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問題,圍繞影響職業(yè)教育發(fā)展最核心的社會因素——教育制度、勞動力市場、企業(yè)以及知識基礎(chǔ)——技術(shù)知識和抽象知識等兩方面因素展開討論,試圖澄明當(dāng)前職業(yè)教育存在認(rèn)同困境的內(nèi)在邏輯。
二、職業(yè)系統(tǒng)外部:社會環(huán)境規(guī)約產(chǎn)生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困境
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所關(guān)注的影響職業(yè)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因素,為分析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提供了基本路徑。職業(yè)教育發(fā)展最核心的教育制度、勞動力市場、企業(yè)等社會因素,本身會對職業(yè)教育產(chǎn)生一定的規(guī)約,而部分規(guī)約將會使社會降低對職業(yè)教育的基本認(rèn)同,產(chǎn)生職業(yè)教育的認(rèn)同困境,這就是社會環(huán)境對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的影響。
(一)教育制度的規(guī)約:正式知識高度編碼化與技能知識難以編碼化的矛盾
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除了受到自身組織結(jié)構(gòu)的影響之外,還受到更廣泛的社會和制度因素的影響。首先,教育制度對職業(yè)教育的社會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專業(yè)知識的正式化程度。自正規(guī)學(xué)校教育產(chǎn)生以來,以知識高度抽象和學(xué)術(shù)導(dǎo)向為特征的教育體系產(chǎn)生了一種狹隘的“知識”概念,只承認(rèn)理論知識部分是專業(yè)知識和資格的基礎(chǔ)。通過這種教育體系獲得的專業(yè)知識往往是高度專業(yè)化的,但通常遠(yuǎn)離實踐問題,由此導(dǎo)致學(xué)術(shù)知識占據(jù)絕對的支配地位,并通過教育制度得到鞏固。例如,學(xué)術(shù)證書的持有者會通過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從而與解決實際問題的人劃清界限,以此確保其在社會中地位的合法性。二是正式的專業(yè)知識與實踐經(jīng)驗的聯(lián)結(jié)程度。職業(yè)教育體系關(guān)注將正規(guī)教育與實踐經(jīng)驗相結(jié)合進(jìn)行知識與技能的傳授,逐漸衍生出寬泛的“知識”概念。知識不僅建立在通過學(xué)習(xí)獲得的形式理論基礎(chǔ)上,而且建立在與工作相關(guān)的環(huán)境中積累的實踐技能和經(jīng)驗基礎(chǔ)上。換言之,職業(yè)教育體系認(rèn)為正式知識和實踐技能對于完成任務(wù)同等重要,甚至對于某些技術(shù)難題而言,隱性技能知識更有用。由此一來,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的價值得以有效凸顯。職業(yè)培訓(xùn)體系的建立為更多的勞動力提供更加廣泛而嚴(yán)格的普通教育和職業(yè)教育,有利于形成工作組織的分散化模式,促進(jìn)在勞動力中更均勻地分配能力,為互動學(xué)習(xí)和培養(yǎng)作為組織能力來源的隱性技能知識提供了更好的基礎(chǔ)。
從歷史實踐來看,盎格魯—撒克遜教育體系清晰刻畫了理論知識與精英地位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正式知識成為區(qū)分地位的基礎(chǔ)指標(biāo)[5]。例如,美國與英國的精英教育體系一直以來極為重視學(xué)術(shù)教育,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了和生產(chǎn)勞動相關(guān)教育的底層地位。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技能的隱性化和語境性使得勞動者難以證明其技能知識是一個可編碼的“知識庫”,即其技能知識難以高度編碼化。而德國和日本的國家制度賦予“實踐經(jīng)驗”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并將其視為能力和資格的來源,直接激勵了對職業(yè)教育與培訓(xùn)的投資,從而產(chǎn)生大量的技能人才,使得行業(yè)企業(yè)能夠以更加合作和分散的方式組織工作,極大地促進(jìn)了隱性知識與技能的傳遞和調(diào)動。
可見,在現(xiàn)行教育制度影響下,學(xué)校教育中正式專業(yè)知識的高度編碼化使得普通教育一軌中學(xué)術(shù)證書的持有者往往在勞動市場中更有競爭力,確保其在社會中地位的優(yōu)越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
(二)勞動力市場的規(guī)約:制度信號與信息信號的失衡
勞動力市場是驗證職業(yè)教育質(zhì)量的重要場域。知識和學(xué)習(xí)嵌入在勞動者的職業(yè)生涯中,其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很大一部分是在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或公司內(nèi)部職業(yè)培訓(xùn)中發(fā)展起來的。正式的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和培訓(xùn)在產(chǎn)生直接相關(guān)的職業(yè)能力方面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對行業(yè)企業(yè)的知識基礎(chǔ)具有直接的影響,由此所產(chǎn)生的資格證書類型一般是高于特定任務(wù)的,基于標(biāo)準(zhǔn)化的、先進(jìn)的知識和技能“包裝”。或者說,職業(yè)教育在市場中發(fā)揮的作用具有基礎(chǔ)性和廣泛性的通識教育功能,能為勞動者提供可以適應(yīng)和應(yīng)用于各種工作環(huán)境和任務(wù)的“元能力”。其中,正式學(xué)校的職業(yè)教育任務(wù)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所需的知識可以在初始培訓(xùn)計劃中預(yù)先編碼和系統(tǒng)整合。而企業(yè)內(nèi)的教育培訓(xùn)主要基于特定的任務(wù)環(huán)境,所需知識是流動的和情境的,不能被輕易捆綁到職業(yè)系統(tǒng)中,因此需要一個基礎(chǔ)廣泛的技能培訓(xùn)體系,使個人能夠追求更多樣和更靈活的方法來持續(xù)學(xué)習(xí)。
當(dāng)前,隨著產(chǎn)教融合步伐的不斷深入,加之個體的職業(yè)并不是固定的,其獲得知識的透明度和可轉(zhuǎn)移性對于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適應(yīng)性至關(guān)重要。個體的職業(yè)流動極為依賴自身掌握技能和知識的類型和質(zhì)量,并能夠通過制度信號和信息信號得以識別。制度信號是指一般化的知識和技能可以被識別和編纂,可以應(yīng)用于很多工作任務(wù)或問題解決中。在任務(wù)高度流動和不可預(yù)測的工作情境下,隱性知識的運用占據(jù)絕大比例,導(dǎo)致制度信號失效。因為隱性技能只能通過實踐和工作表現(xiàn)出來,這時個體知識和技能的轉(zhuǎn)移流動依賴基于共享的行業(yè)或職業(yè)規(guī)范的社會和專業(yè)網(wǎng)絡(luò),這就是信息信號的作用[6]。目前,我國職業(yè)教育在勞動力市場的有效轉(zhuǎn)移和積累還缺乏“包容性社會結(jié)構(gòu)”的支持,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信號作用還未得到充分發(fā)揮,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個體隱性知識技能的“市場化”,從而出現(xiàn)“技能錯配”與“技能浪費”的現(xiàn)象,直接影響了職業(yè)教育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
(三)企業(yè)的規(guī)約:正式知識與技能知識重視程度的差異
勞動者從事特定工作之后,知識和學(xué)習(xí)嵌入在公司內(nèi)部的職業(yè)生涯中,大部分知識和與工作相關(guān)的技能是通過公司在職培訓(xùn)獲得的。通過職業(yè)教育獲得的正式知識和大部分技能知識僅作為一種入職資格,為其在企業(yè)內(nèi)部與工作相關(guān)的技能奠定了基礎(chǔ)。因此,企業(yè)內(nèi)職業(yè)教育與培訓(xùn)在定義企業(yè)的知識基礎(chǔ)方面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在精英主義教育體系和大眾主義教育體系兩種不同的教育模式下,可以明晰企業(yè)技能培訓(xùn)的發(fā)展情況及對技能培訓(xùn)的影響。
在精英主義教育社會中,職業(yè)主要圍繞基于正式入職資格的分層邊界的工作等級進(jìn)行組織分類。例如,19世紀(jì)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勞動者通過接受高等教育習(xí)得正式知識來獲得工作,企業(yè)內(nèi)職業(yè)教育與培訓(xùn)減少個人經(jīng)驗的多樣性,從而限制了創(chuàng)造性思維和隱性知識產(chǎn)生的范圍[7]。與此同時,這些正式知識與更高的職位聯(lián)系起來,意味著通過實踐經(jīng)驗積累的隱性技能知識將被低估,不會被認(rèn)為是晉升的基礎(chǔ)。個人積累隱形技能知識的動機(jī)被削弱,組織也無法挖掘“邊干邊學(xué)”的潛力,從而對企業(yè)發(fā)展起到負(fù)面影響。
相反,在德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影響下,通過積累廣泛的技能和組織經(jīng)驗,可以實現(xiàn)向高層職位的晉升。正式知識在確定能力標(biāo)準(zhǔn)和進(jìn)入高級職位方面只起到有限作用,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企業(yè)特有技能和實踐經(jīng)驗的長期積累。這樣一來,企業(yè)內(nèi)職業(yè)教育與培訓(xùn)的知識基礎(chǔ)更加廣泛,與個人職業(yè)發(fā)展有機(jī)聯(lián)系在一起,促進(jìn)了有效技能的產(chǎn)生和開發(fā)。尤其是日本企業(yè)內(nèi)培訓(xùn)制度實行“輪崗制”,有助于縮小不同類別勞動力之間的工作距離,也為個人通過實踐經(jīng)驗積累知識從而實現(xiàn)職位晉升給予了有效激勵。因此,企業(yè)組織制度與文化對職業(yè)教育發(fā)展具有重要影響。如果一個企業(yè)能夠重視隱性技能知識對企業(yè)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性,那么這個企業(yè)就可能表現(xiàn)出強(qiáng)大的漸進(jìn)式創(chuàng)新能力,專注于企業(yè)核心競爭力[8],這對于鼓勵形成認(rèn)同職業(yè)教育系統(tǒng)培養(yǎng)下的職業(yè)工作系統(tǒng)具有積極意義。
三、職業(yè)系統(tǒng)內(nèi)部:技術(shù)知識與抽象知識的失衡導(dǎo)致職業(yè)教育的認(rèn)同困境
社會環(huán)境維度對于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危機(jī)的分析主要考慮危機(jī)生發(fā)的環(huán)境場域。當(dāng)然,任何外部環(huán)境場域的影響并不必然引發(fā)事物本身內(nèi)部的變革,事物內(nèi)部本身的構(gòu)成要素對于事物變革發(fā)揮著更為直接的作用。因此,從知識基礎(chǔ)這一職業(yè)系統(tǒng)內(nèi)部出發(fā),探討技術(shù)知識與抽象知識對職業(yè)教育的社會塑造,對于分析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極為必要。在知識基礎(chǔ)維度,導(dǎo)致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技術(shù)知識與抽象知識之間的平衡性缺失,并由此使得知識背后所對應(yīng)的職業(yè)缺乏知識依賴。
(一)過度強(qiáng)化技術(shù)知識降低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
在勞動分工高度發(fā)達(dá)的現(xiàn)代社會中,高質(zhì)量發(fā)展背景下所專注的專業(yè)技能是一種具有合法性與壟斷性的專業(yè)化商品,其社會基礎(chǔ)既包括學(xué)術(shù)知識,也涵蓋在職業(yè)工作中的漸進(jìn)式積累與推理實踐等社會過程。邦格(Bunge M)認(rèn)為,技術(shù)的本質(zhì)在于關(guān)注有效性或無效性,即技術(shù)知識能否在實際應(yīng)用中有效地實現(xiàn)預(yù)期目標(biāo)[9]。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專業(yè)技能無論是“診斷”還是“治療”,都具有很強(qiáng)的實踐性,需要專業(yè)技能人員根據(jù)不同實踐情景靈活處理,從而形成對特定技術(shù)難題的針對性解決辦法。在此層面,技術(shù)知識的有效性就在于某項技術(shù)能夠被成功應(yīng)用于實際生產(chǎn)和服務(wù),從而提高生產(chǎn)和服務(wù)的質(zhì)量、效率、效益,以此證明技術(shù)知識的可靠性與有用性。因此,技術(shù)知識的有效性是為現(xiàn)代生產(chǎn)和服務(wù)提供有力支持的關(guān)鍵。
然而,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技術(shù)知識的可靠性,技術(shù)工人的工作回報相對較少。在柯林斯(Collins R)看來,醫(yī)生和律師這類職業(yè)主要是政治勞動,技術(shù)工人的工作主要是生產(chǎn)勞動,前者更多操控外在表現(xiàn)和信仰,后者生產(chǎn)真正的產(chǎn)品。比起政治領(lǐng)域的不可預(yù)測和神秘化,恰恰是生產(chǎn)領(lǐng)域技術(shù)知識的可靠性使相對回報較少,技術(shù)職業(yè)恰恰因為個體技能的成功而處于劣勢[10]。質(zhì)言之,掌握現(xiàn)代生產(chǎn)技術(shù)核心的職業(yè)反而缺乏最關(guān)鍵的資源,即無法通過組織文化群體獲得正式認(rèn)可的權(quán)力,從而無法流動到社會分層中靠上的位置,這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導(dǎo)致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度不高。
(二)抽象知識缺位弱化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
知識變遷是通過職業(yè)的內(nèi)部機(jī)制實現(xiàn)的,知識更多是內(nèi)部資源,很少受外部影響,這樣生產(chǎn)出來的知識能夠用來對抗其他職業(yè),如高等教育知識。知識的增長包含知識的變遷,一種是新知識的增長,另一種是舊知識的更新。在很多領(lǐng)域,單個專業(yè)人懂的知識會越來越多,同時借助新工具或新概念來認(rèn)識,既存知識可以細(xì)分為更加精細(xì)的范疇[11]。而知識的更新更多體現(xiàn)在從具體事實或方法到更新范式或一般性方法。這兩者對職業(yè)產(chǎn)生的影響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知識增長迫使職業(yè)進(jìn)行細(xì)分,并把某個既定專業(yè)的知識結(jié)構(gòu)總量維持在穩(wěn)定水平。另一方面,范式或一般性方法的更新則迫使很多職業(yè)不斷發(fā)展出屬于職業(yè)內(nèi)部的抽象知識。因為這些抽象知識的存在時間相比關(guān)乎具體事實和方法的知識更長久,從而增加對這一職業(yè)的控制權(quán)與話語權(quán)。正如阿伯特(Andrew Abbott)所認(rèn)為的:“不管社會結(jié)構(gòu)如何,只要在日常工作場所具備對核心工作的合法性控制,職業(yè)自主性就能得以保障。而這種合法性控制的根源正是基于職業(yè)的學(xué)術(shù)知識體系,即學(xué)術(shù)知識的制度化是形成專業(yè)技能的關(guān)鍵過程,如果一個職業(yè)的學(xué)術(shù)知識過于簡單或過于復(fù)雜,都會弱化對職業(yè)的合法性控制。”[12]
當(dāng)前,在發(fā)展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的背景下,只懂生產(chǎn)操作而不了解技術(shù)原理的傳統(tǒng)工人已然不能適應(yīng)急劇變化的技術(shù)生產(chǎn)環(huán)境。產(chǎn)業(yè)發(fā)展過程中所需要的抽象知識正在不斷衍生與增長,技術(shù)知識也變得越來越復(fù)雜,本科職業(yè)教育應(yīng)時而生。它更注重培養(yǎng)勞動者從工作實踐過程中掌握自下而上的理論化、抽象化和全局性的知識體系,這需要以相關(guān)的科學(xué)知識為基礎(chǔ)[13]。技術(shù)萌芽要成為具有廣泛社會應(yīng)用的實用技術(shù),除了依賴科學(xué)原理、技術(shù)原理以及技術(shù)經(jīng)驗等技術(shù)核心知識外,還必須配備大量的技術(shù)外圍知識,如設(shè)計、裝配、調(diào)試、生產(chǎn)、管理等方面的知識。當(dāng)產(chǎn)生一個新的技術(shù)設(shè)想,還有相應(yīng)的外圍配套知識時,才能保證技術(shù)的生長空間。技術(shù)核心知識與技術(shù)外圍知識相輔相成,共同構(gòu)成技術(shù)生長的完整體系。技術(shù)核心知識為技術(shù)萌芽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chǔ)和創(chuàng)新源泉,而技術(shù)外圍知識則為技術(shù)的實際應(yīng)用提供必要的支撐和保障。但是,目前為了更加突出職業(yè)教育的類型特征,總是會將技術(shù)知識的實踐性,或者將實踐性的技術(shù)知識等抽象化程度相對較低的知識擺在突出位置,而削弱對相關(guān)抽象化程度比較高的理論化、抽象化、全局性知識的觀照,以及對這些知識體系的建構(gòu),使得其缺失對所屬專業(yè)的管轄權(quán)。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職業(yè)教育“文憑”的地位。
四、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的破解路徑
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提供了分析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的重要框架,基于這一分析框架,可以使得對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的認(rèn)識更為具象化。分析問題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基于職業(yè)系統(tǒng)理論的分析框架,如何破解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困境便成為分析路徑的落腳點。
(一)確立職業(yè)教育專業(yè)的排他性與自主性
弗雷德遜(Freidson)和約翰遜(Johnson)強(qiáng)調(diào)專業(yè)作為一種相對固定的職業(yè)群落,其內(nèi)部成員擁有共同的制度(institutional)、意識形態(tài)(ideological)屬性以及市場保護(hù)(market shelter)機(jī)制,使得各專業(yè)領(lǐng)域之間壁壘分明、各有特色。這種專業(yè)化不僅體現(xiàn)在職業(yè)身份的差異上,更在于其所需的深厚知識與技能的獨特性[14]。
一方面,要確立職業(yè)教育專業(yè)的排他性。職業(yè)教育的專業(yè)應(yīng)當(dāng)確保提供高深的知識與技能。當(dāng)然,這些技能與知識能夠通過系統(tǒng)的教育和培訓(xùn)獲得。同時,職業(yè)教育的專業(yè)也應(yīng)當(dāng)致力于為客戶提供高品質(zhì)、無私的服務(wù)。這既是專業(yè)精神的體現(xiàn),也是專業(yè)價值的所在。伴隨著職業(yè)分工越來越精細(xì),勞動也逐漸繁雜,人們從事某項勞動需要“專攻術(shù)業(yè)”。這種“專攻術(shù)業(yè)”彰顯了從業(yè)者的勞動技能長處、資源占有優(yōu)勢以及穩(wěn)固的個人綜合品質(zhì),不僅增強(qiáng)了從業(yè)者在社會勞動中的壟斷性和排他性,也為其帶來了從業(yè)的優(yōu)越性,從而有效增強(qiáng)對職業(yè)教育專業(yè)的管轄權(quán)。
另一方面,應(yīng)逐步提升職業(yè)教育專業(yè)的自主性。一個專業(yè)若處于強(qiáng)勢地位,意味著其涵蓋的科學(xué)知識已經(jīng)高度專門化、復(fù)雜化和結(jié)構(gòu)化,以至于外行不能挑戰(zhàn)專業(yè)人員的技術(shù)判斷,實現(xiàn)專業(yè)自治。但是,任何專業(yè)在證實其對公眾有好處之前,并不會立刻被授予自治權(quán)[15]。因此,職業(yè)教育專業(yè)獲得自主性的主要前提就是要有真正的技術(shù)能力。只有如此,專業(yè)才能通過控制誰來接受教育訓(xùn)練而壟斷技能。同時,這種專業(yè)性還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在技能本身獲得的復(fù)雜性上,即必須通過足夠?qū)I(yè)的訓(xùn)練才能獲得。通過賦予職業(yè)教育專業(yè)性內(nèi)涵,能夠改善公眾對職業(yè)教育所面向崗位和從業(yè)者的看法,提升職業(yè)教育的社會地位[16],從而增強(qiáng)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
(二)逐步改革現(xiàn)代企業(yè)的組織結(jié)構(gòu)方式
企業(yè)的組織結(jié)構(gòu)方式對技能工作的地位有重要影響,進(jìn)而影響著社會對職業(yè)教育的整體認(rèn)同。例如,與泰勒制通過不斷細(xì)化工作分工不同,德國企業(yè)普遍采納了一種扁平化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獨特的勞動分配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生產(chǎn)線上的維修工人被賦予更多的職責(zé)和自主權(quán),他們擁有較高的自由度,并具備復(fù)合型的職業(yè)技能。這些工人不僅能夠勝任基本的操作和裝卸任務(wù),還能參與工作的準(zhǔn)備、規(guī)劃以及后續(xù)評估。鑒于對工人復(fù)合技能的需求,企業(yè)自然會有動力參與人才培養(yǎng)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值得一提的是,在協(xié)調(diào)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下,德國企業(yè)更傾向于通過非市場手段來協(xié)調(diào)與其他利益相關(guān)者的關(guān)系。例如,雇主協(xié)會等代表和協(xié)調(diào)雇主利益的相關(guān)機(jī)構(gòu)能夠采取相應(yīng)措施有效地促進(jìn)企業(yè)間的合作,減少相互挖墻腳的情況,同時建立一種自我激勵和約束機(jī)制,維持“高技能均衡”狀態(tài),進(jìn)一步保障和強(qiáng)化了企業(yè)對學(xué)徒的需求[17]。這樣一來,德國企業(yè)通過組織結(jié)構(gòu)方式的調(diào)整和完善,維護(hù)了企業(yè)與學(xué)徒之間,以及與其他相關(guān)利益者之間的平衡,提升了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度。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要增強(qiáng)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還需要提高職業(yè)教育與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匹配度。而在此過程中,企業(yè)的自我組織變革勢在必行。
企業(yè)要利用組織結(jié)構(gòu)扁平化的過程重建以職能為主導(dǎo)的組織結(jié)構(gòu),重組網(wǎng)絡(luò)化協(xié)同作業(yè)的管理流程以實現(xiàn)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建立更具競爭力的產(chǎn)品利潤分配及薪酬制度,組建以知識技術(shù)技能型人才為核心的管理干部團(tuán)隊,以及符合新知識經(jīng)濟(jì)的企業(yè)文化,凸顯復(fù)合技能知識對企業(yè)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性。在實現(xiàn)自我變革的過程中,企業(yè)逐漸形成其獨特的勞動者知識與技能需求,這些需求與行業(yè)內(nèi)其他企業(yè)有所不同,從而孕育出企業(yè)專用的技能。這種專用技能不僅增強(qiáng)了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還促使企業(yè)更深入地參與職業(yè)教育。同時,為更好地滿足企業(yè)的實際需求,應(yīng)在職業(yè)教育政策制定、實施和監(jiān)管上賦予行業(yè)企業(yè)更大的自主權(quán)。這樣一來,企業(yè)就能根據(jù)自身的需求和愿景,影響甚至塑造職業(yè)教育的形態(tài)和內(nèi)容,從而實現(xiàn)自己的訴求和期望。這樣的變革不僅有利于企業(yè)的長遠(yuǎn)發(fā)展,也為職業(yè)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進(jìn)一步消解職業(yè)教育的社會認(rèn)同困境。
(三)堅實職業(yè)教育技術(shù)知識的基礎(chǔ)地位
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進(jìn)步,技術(shù)人工物越來越復(fù)雜和精細(xì)化,技術(shù)知識也變得越來越系統(tǒng)且多類型。實際上,技術(shù)知識是關(guān)乎技術(shù)客體、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實踐的系統(tǒng)知識,必須作用于人類實踐其有效性才得以展現(xiàn),因而有效性是技術(shù)知識最重要的特征。技術(shù)知識如果能夠經(jīng)人的實踐下達(dá)到成功改造或制作技術(shù)人工物的目的,就是有效的、有用的[18]。從這一角度來說,技術(shù)知識為個體提供功能價值,同時對個體的綜合能力培養(yǎng)也極為重要。例如,意念的表達(dá)與理念轉(zhuǎn)化為操作方案的能力,知識的整合、應(yīng)用及物化的能力,面向真實世界和物質(zhì)世界進(jìn)行創(chuàng)造的能力,基于可靠性、性價比的方案權(quán)衡和優(yōu)化的能力,以及把有形的創(chuàng)造物轉(zhuǎn)化為無形的智慧、把無形的智慧轉(zhuǎn)化為有形的創(chuàng)造物的過程與能力,等等。這些能力對學(xué)生技術(shù)能力結(jié)構(gòu)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19]。當(dāng)然,這些能力同樣會影響勞動者在市場中踐行技術(shù)知識的行為,并維護(hù)其技能工作的地位。
職業(yè)教育的存在以技術(shù)知識為基石,這決定了職業(yè)教育仍要堅持以培養(yǎng)實用型和應(yīng)用型技術(shù)技能人才為核心目標(biāo)。從本質(zhì)上看,技術(shù)萌芽要想開辟自己的生長空間,成為具有廣泛社會應(yīng)用價值的實用技術(shù),除了需要一定的科學(xué)原理、技術(shù)原理以及技術(shù)經(jīng)驗等技術(shù)核心知識外,還必須有充足的技術(shù)外圍知識,如設(shè)計、裝配、調(diào)試、生產(chǎn)、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作為依托。當(dāng)有一個新的技術(shù)設(shè)想時,圍繞這一核心技術(shù),又有相應(yīng)的外圍知識配套,這一技術(shù)的生長空間才能有一定的知識保證。這就說明現(xiàn)代技術(shù)不僅對人的技術(shù)知識掌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關(guān)注對某一技術(shù)的全盤操控能力、人與機(jī)器的協(xié)同操作能力以及個體對背景知識的熟練掌握程度等。基于此,一方面,要面對不確定的工作世界,扎根于職業(yè)實踐特征,深化技術(shù)知識的教學(xué)。通過科學(xué)系統(tǒng)的教學(xué)安排,使學(xué)生全面掌握相關(guān)技術(shù)領(lǐng)域的基礎(chǔ)知識、原理和前沿動態(tài)。另一方面,注重技術(shù)知識與具體工作項目的聯(lián)結(jié),增強(qiáng)學(xué)生的技術(shù)實踐應(yīng)用能力。通過持續(xù)深化校企合作、產(chǎn)教融合等,為學(xué)生提供置身于真實技術(shù)情境的技能習(xí)得環(huán)境,從而加深其對技術(shù)知識的理解和掌握。
(四)提升職業(yè)教育對抽象知識的管轄權(quán)
一個職業(yè)保持管轄權(quán)的能力部分取決于其學(xué)術(shù)知識的權(quán)力和聲望。事實上,學(xué)術(shù)型抽象知識的作用往往是符號方面的,而非實踐方面的。學(xué)術(shù)型抽象知識通過澄清職業(yè)工作的基礎(chǔ),并把基礎(chǔ)上溯到主要的文化價值,從而使職業(yè)工作合法化。在大多數(shù)現(xiàn)代職業(yè)中,這些文化價值表現(xiàn)為合理性、邏輯和科學(xué)所具有的價值。學(xué)術(shù)專業(yè)人士證明職業(yè)工作具有嚴(yán)密性、明晰性和科學(xué)的邏輯性,從而使之在更高的價值構(gòu)成的背景下獲得了合法性[20]。質(zhì)言之,專業(yè)的嚴(yán)密性與邏輯性體現(xiàn)在專業(yè)知識的結(jié)構(gòu)體系建立在科學(xué)知識體系的組織引導(dǎo)下。反之,專業(yè)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據(jù)。
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新興專業(yè)不斷產(chǎn)生,不斷賦予職業(yè)需求以新的內(nèi)容,越來越細(xì)化、高效的職業(yè)服務(wù)成為現(xiàn)代需求。韋伯(Weber M)認(rèn)為,從事專業(yè)性工作的勞動者具備獲得、積累專業(yè)知識的權(quán)利,以及在市場中實踐這些知識的權(quán)利[21]。這要求職業(yè)教育向?qū)I(yè)教育學(xué)習(xí),不斷提高其專業(yè)的權(quán)威性,尤其要賦予職業(yè)本科教育專業(yè)教育的深刻內(nèi)涵,并通過知識建構(gòu)來保證受教育者及其將來從事專業(yè)工作的合法地位。因此,在職業(yè)本科教育課程體系中,要注重對系統(tǒng)性技術(shù)知識的統(tǒng)籌與傳授,其主要包含系統(tǒng)性的技術(shù)理論與技術(shù)原理。當(dāng)然,這類知識具有與科學(xué)知識相同的普適性,是任何技術(shù)活動開展都需要遵循的基礎(chǔ)性知識,能夠幫助學(xué)習(xí)者掌握、運用乃至發(fā)明技術(shù)科學(xué)規(guī)律[22]。要強(qiáng)調(diào)掌握相對系統(tǒng)的專業(yè)理論知識的重要性,把實踐能力培養(yǎng)建立在掌握系統(tǒng)科學(xué)理論的基礎(chǔ)上,保障職業(yè)教育課程的嚴(yán)密性與邏輯性,逐步提升職業(yè)教育學(xué)位的含金量,增強(qiáng)職業(yè)教育的社會合法性。同時,工作場所中所需技能的變化關(guān)鍵在于不同工作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日益分化,以及在不同工作崗位上都適用的“軟技能”的重要性不斷增加[23]。“軟技能”是從事一項職業(yè)的重要技能、間接技能和用以提升水平的促進(jìn)性技能,可以為個體提供避險價值,降低被代替的風(fēng)險,并且提升職業(yè)彈性,其作為抽象知識的一種無疑能幫助個體增加社會競爭力。
[參考文獻(xiàn)]
[1]祁占勇,馮嘯然.職業(yè)教育社會認(rèn)同的理論模型與提升策略[J].教育研究,2024(7):108-121.
[2][11][20](美)安德魯·阿伯特.職業(yè)系統(tǒng)[M].李榮山,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6:56-57,260,87.
[3]劉思達(dá).職業(yè)自主性與國家干預(yù)——西方職業(yè)社會學(xué)研究述評[J].社會學(xué)研究,2006(1):197-221.
[4]姜大源.工作、職業(yè)和教育若干概念疏釋[J].職教發(fā)展研究,2022(4):1-11.
[5]Gerpott T J,Domsch M.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management of salaried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0, 24(2):207-226.
[6]Marler J H,Milkovich G T,Barringer M W .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s and Boundaryless Careers: A New Market for High-Skilled Temporary Work[J].CAHRS Working Paper Series,1998:1-28.
[7]Nonafka I.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5(1):14-37.
[8]徐建中,冷單.基于隱性知識管理的制造企業(yè)核心競爭力評價模型構(gòu)建[J].圖書情報工作,2011,55(14):68-72.
[9]張思琪,匡瑛.從技術(shù)知識論看職業(yè)教育的類型屬性[J].教育與職業(yè),2023(12):21-26.
[10](美)蘭德爾·柯林斯.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xué)[M].劉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300-301.
[12]劉思達(dá).新發(fā)展格局下的當(dāng)代中國職業(yè)研究——從勞動分工到專業(yè)技能[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23(4):63-82+205.
[13]王佳昕,潘海生,郄海霞.技術(shù)論視域下職教本科定位與人才培養(yǎng)邏輯[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5):141-146.
[14][15]趙康.專業(yè)、專業(yè)屬性及判斷成熟專業(yè)的六條標(biāo)準(zhǔn)——一個社會學(xué)角度的分析[J].社會學(xué)研究,2000(5):30-39.
[16]徐國慶,王笙年.職業(yè)本科教育的性質(zhì)及課程教學(xué)模式[J].教育研究,2022,43(7):104-113.
[17]李俊,李東書.德國企業(yè)究竟為何愿意深度參與職業(yè)教育?——經(jīng)濟(jì)社會學(xué)視角下的分析[J].教育與經(jīng)濟(jì),2022,38(2):88-96.
[18]林潤燕,吳國林.技術(shù)知識的認(rèn)識論追問[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23):258-262.
[19]顧建軍.技術(shù)的現(xiàn)代維度與教育價值[J].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18,36(6):1-18+154.
[21]Weber M.Economy and Socie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45.
[22]孫小梅,周應(yīng)國.本科層次職業(yè)教育專業(yè)課程開發(fā):三維邏輯、應(yīng)然特征與實踐依循[J].職業(yè)技術(shù)教育,2023,44(35):29-34.
[23](英)邁克爾·揚.把知識帶回來:教育社會學(xué)從社會建構(gòu)主義到社會實在論的轉(zhuǎn)向[M].朱旭東,文雯,許甜,等,譯.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19: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