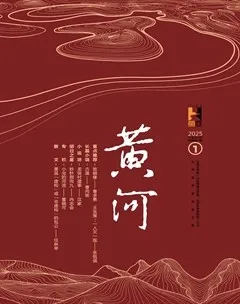小蟲的河流
河流,是大地的靈魂。每一條河流不僅淌過時間,也穿越空間。世界上有多少條河流,就有多少種美麗與憂傷。河流是村莊,河流是月亮,河流是女子,河流也是硬漢……
那么,人呢?請原諒,我無意從古老的《詩經》起興傳統出發,但我相信,每個人都是一條河流。尤其是,在這個訊息驚濤駭浪的時代,我們生命的河流不再無風自動,不再自然流淌,甚至會變為斷裂的、干涸的、枯槁的玫瑰。于是,在晝夜不舍中,我們惟有在生命不斷的流轉倚徙之間,方能得以完成對于一條河流的敘述。沒錯,在接下來的紙箋中,我要完成的是對一條詩人之河的敘述。他原名吳小龍,筆名吳小蟲,而私下里,朋友們也常常親切地叫他小蟲。一條“小蟲”,從晉北大地出發,輾轉騰挪于太原、西安、重慶、成都之間,用凹凸不平的足跡,爬過了歲月的河流。
一、春水、流徙與遠方
每一條河流,都有自己的起點,詩人小蟲的河流,是從這里開始的:
2004年,時任《新作文》(高中版)編輯兼詩人的麥堅與執行主編續小強一起倡導詩教中國,在刊物上專門開設詩歌欄目,并配有點評。在一堆自由來稿中,他發現了一封“詩質尚可”的詩歌稿件,并在當年的第11期將這名來自山西省應縣四中40班的學生的“處女作”予以發表:
我認識一個抒情詩人
他已寫了十幾年詩
昨天他出于義憤打了人
電話中他說
這是他這么多年
唯一的杰作
沒錯,詩人署名吳小龍,也就是后來的吳小蟲。這首名為《杰作》的詩歌,應該是目前可查的小蟲最早的詩作(當然,另據詩人宋憩園的訪談,小蟲的詩歌創作應該可以推至更早的1997年)。從這首“詩質尚可”的處女作中,我們或許可以觸摸到小蟲詩歌源流的一些原初秉性:敏感,激憤,真性情。而這背后,也許或多或少地隱藏著他心靈深處的一些記憶。比如,在后來《憶我早年的一件恥辱》一詩中,詩人便寫道:“就在中午,我突然憶起了早年/成長過程中的一件恥辱/一個人打了我,無緣無故/我尚還不明白他為什么問我的家庭/問我父親的職業和權力/然后就開始暴風驟雨的痛擊/我的肉體,無緣無故……”。身體的瘦弱,性情的溫和,造就了他童年時代被人欺侮的傷痛。但如同早年間見慣了兵士殺人場面的沈從文,在后來的作品中并沒有展現出暴力恣睢,而是選擇更多地發掘人性之美一樣,這件事之于小蟲的生活抑或詩作,也并未生成爆裂反擊效應。而換一個角度來看,托馬斯·曼之于卡夫卡“表情捕捉”的征引,或許能從另一維度說明一條“詩人之河”抑或“作家之河”的共通秉性。據說,作家托馬斯·曼善于捕捉人的神情,有一次當他看到卡夫卡生前最后的那張相片,頓覺四十多歲的卡夫卡看起來儼然一個大孩子:“一張稚氣、羞澀而肅然的臉龐。”應該說,這種稚氣與羞澀,在詩人小蟲臉上也存在著。事實上,據小蟲太原的師友回憶,早年間每每在其他人“詩人時刻”的狂歡中,他總是低調的、謙和的,這個“一喝便醉”的人,在飯局上卻總能照顧他人的感受,也能在大家眾聲喧嘩之后不會忘記買單。
無論如何,《杰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視作小蟲詩歌河流的巴顏喀拉之春水,是他詩歌發表的開端。在此之后,小蟲開始慢慢踏上在詩之途。大概在2009年至2013年,小蟲居住在太原河西一個名叫前北屯的城中村,混跡于一些由打工人、扒竊者、風塵女子,以及不明來歷的蕓蕓眾生構筑的“城市暫住者”中間,書寫著畸形繁華現代城市病癥的“前北屯系列”詩歌。及至后來,他一次次背起行囊,倚徙于天邊流云與城市霓虹之間,在華巖寺里抄碑,在寬窄巷子游走……直到2018年,他那凝結了多年心血的詩稿入選了“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并以《一生此刻》為名出版,至此這位不事聲張的80后實力詩人日益得到詩壇和讀者的廣泛認可。在詩集開首的《序曲》中,小蟲寫下了如是詩行:
總要在一個地方
感受冷暖四序
看草木枯榮三兩回
你的心里才有甘露半滴
總要在一個地方
交一些朋友
醉上許多回
你才能再去另一個地方
是的,他于數個城市間美麗遠行的旅程,其實也是情感日漸豐盈、語言之河日益豐美的過程。而這條河自然蘊含著屬于小蟲的春生、夏長、秋收與冬藏,既有著他溫婉的叮咚,也有著他激流的風暴,既有他對自身宿命的觀照,也有他對他者命運的悲憫。及至后來出版的風華正茂的《花期》與待出版的富有煙火氣息的《云的第一課》中,他逐漸將對生活與生命、詞與物、詩與思的感悟融合,呈現出潛沉的詩歌格調、美學風范與精神維度。而這,也使其奔騰不息的情感河流,終于流淌為巴蜀山水間曲折而緩慢的心靈成長史。
二、木塔、母親與土地
故鄉,是詩人根脈性的存在。依此出發,小蟲的河流,不是蕭紅那飽含童年記憶的呼蘭河,也不是黃永玉筆下靈動著浪蕩漢子的無愁河,而是那條源自晉北應縣老家的河。然而,從另一向度來看,這條“老家的河”又和呼蘭河、無愁河一樣,是一條不斷回望、不停構筑的故鄉情感之河。而在這條虛實交織的河流上,木塔、母親與土地是三個最重要的有機生命體。
小蟲故鄉的應縣木塔,是享譽世界的奇跡之塔。甚至就在前陣子,木塔上那些神出鬼沒的“貓看護”也因被人“發現”,瞬間升格成為“網絡紅貓”。倘若從普通百姓的視角來看,這該是平原大地上多么奇特的一種存在。在此,我甚至忍不住想要引用成向陽散文《天使在人間》中由太原北出雁門觀望木塔的一段神來之筆:
廣大而寂寞的平原上空無一物,除了那一針安靜而濃黑的遠遠矗立在地平線之上的遼金木塔。車在冬天的原野上會走很久,你如果一直貼著車窗看,那著名的木塔就一直在你眼前。當終于看不見木塔的時候,車就出了應縣。看看表,竟然走了一個半小時。所以,我在第一次遇到應縣人吳小蟲的時候,想都沒想就說:“你們應縣真大啊,坐車看木塔能看一個半小時。”
是的,這便是作為神跡的木塔的存在。而小蟲,作為木塔下長大的孩子,幼年時于佛聲縈繞之中,于北方寺廟的青磚上打鬧奔跑之間,或許一定蒙受過佛塔之光的恩澤。因而,在作為其詩人之河締造緣由的長詩《一個詩人怎樣成為詩人的》中,便有諸多此類禪悟式的表達,比如詩作中“因緣和佛塔的鐘聲/他在閻王面前承諾了什么……他看見永恒的前世/發出在這一世最初的啼哭”“青山綠水,道路緩慢,千里外的山上狐貍修行/佛日漸無聲,棄塔而去”“有幸與一只山羊一面之緣,后來她成了盤里的晚餐,而我成了祭壇上的香燭與燈盞”等隨處可見的語句;再比如《回鄉記》中“半路上,隱隱又望見木塔/卻聽塔下游樂場濺起的喧鬧/香客日少神像蒙塵/我心中那剛有雛形的半個舍利呀”的獨白,以及后來一系列飽經風霜漫漫漂泊的旅行與重慶華巖寺一遍遍的碑刻抄經,他都將其看做冥冥中的宿命磨難與修行安排,是他來到這個世界上必須要承受的“刑具和尖刀”,也是他通往詩歌之河的助益與考驗。而這種超越世俗的佛禪感悟,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小蟲今后漫長歲月中的整體風格與精神氣質,即一種流浪意識、悲憫情懷、現實妥協與罪感融化合力造就的浮生意念。
與木塔形而上意味的精神佛光對照,母親與土地則更多地承載了詩人之河的世俗疼痛。無疑地,在母親過世之前,小蟲的河流是充滿著歡快的童年之聲的。在這片故鄉之地上,曾幾何時,“羽翼下他爬上大樹捉天牛”“白天他和表哥在河里撲騰,夜晚/一條巨龍在水底穿行,震耳的長吟”(《一個詩人怎樣成為詩人的》)。甚至,在后來他鄉漂泊的歲月里,當詩人一次次折返應縣故鄉,依然能感受到“天藍得正好/云隨意成形”與“雜草盡望,花大姐水包頭”這樣心交給手、夢交給路的“人生第一課”的美好。(《云的第一課》)然而,伴隨著母親彗星墜落般的離開,小蟲的河流開始山崩地裂洪水滔流,他一次次在死神面前質問能否持續一生,一次次拷問靈魂何時蘇醒,一次次于凌晨聽著蛐蛐的歌聲入睡、在落滿歲月灰塵的早來的大雪中體會著“歲月流逝中的罪與罰”(《疼》)。自此以后,“龍卷風卷掉了夢想和愛情”,他感受到了“疾風吹勁草,時代如鐮刀”的痛楚。他幻想著“一個大漢推門而入/只在椅子上睡了睡/只叫了聲母親”的美好奢望(《清明近》),然而現實卻是“北風吹著我的缺口/發出嗚嗚的響聲”的讓人哭泣的“互相傷害的愛”(《回鄉記》)。
一個詩人,無論他走多遠,總是穿著孩提時的鞋子。這像極了古希臘神話中那個名叫安泰俄斯的大力士,他只要雙腳站在大地上,便會獲得無窮無盡的力量,因為那里有他作為“大地之神”(亦稱“地母”)的溫暖襁褓。這個具有隱喻性的神話傳說,似乎可以借用來詮釋小蟲之河生命力的來源。在詩作《清明近》中,小蟲留下了類似于蕭紅《呼蘭河傳》結尾處回環往復的故園之思:“我的姥姥姥爺爺爺奶奶/都去世了/我媽媽也去世了/有一天,我也將閉上眼睛/黑暗的泥土里/與小蟲子在一起/(對于死亡,沒有任何思想)/一只紅杏探出墻來/另一只也探出來”。而后,他珍藏著故鄉的土地根脈,在日漸消逝的流水中漂游向遠方。
三、龍泉驛山頭———三月桃花
詩人的生命流轉,很多時候會淬生其詩風的涅?與超越。在小蟲的河流中,如果說早年間溫熱的青春潮動與嚴酷的情感寒冬,更多意義上造就了跳動的泥土氣息。那么,他2013年底悄然南下重慶,于西南名剎華巖寺中整理古代佛經文獻五年之久的“渝漂”之旅,則在根本上開慧了他的靈性,并留下了一系列富有佛禪意味的精短詩作與曼曼長詩。
“心碎于野,我為露水的恩澤活著”(《正午時刻》),小蟲如是說。在詩人宋憩園的訪談中,他談到自己對于何為詩人的理解。在他看來,詩人好比一個容器,“有的裝酒,有的裝茶,有的裝著山川萬物,有的裝著一叢小雛菊,風一吹,就搖曳了起來。”而對于他,一生,一滴露水已經夠了。在此時段,我們能看到小蟲河流中一樹繁花的詩意。他一方面接續了中國古代,尤其是宋詩中化理趣為詩思的傳統,一方面又氤氳著晚唐詩人那份倏忽縹緲、蘊藉幽夢的化境。這些,都使得他的詩歌如同龍泉驛山頭的三月桃花,淡然而悠遠。
是的,此時小蟲的河流中確乎飄蕩著林林總總如是風格的小詩。品讀這些小詩,你首先會感受到一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不斷辯難、不停詰問的玄禪意味。但細究你會發現,這絕非單純的譏誚之語,而是最終通向了對于眾生的悲憫之情。在小蟲的河流中,這些作為“詞與物”結合體的佛禪式美學散步,有些類似于日本俳句大師小林一茶“孤獨/四面八方都是/紫羅蘭”抑或“四十九年浪蕩/荒蕪/月與花”的物哀色調,但又有所不同。如同戴望舒在《論詩零札》中的述說那樣,這并非單純的“字句上的nuance(細微的差別)”,而是“詩情上的nuance(細微的差別)”,其中有著中國古典與現代詩味交融的中和、哀傷與愛意。比如,在《正反》中,詩人以莊周與蝶的互換詩辯入題:首先是“許多時候我感覺自己已經死了/我是在代替一只貓,或者代替另一個人/活著”與“一個事實是,一只貓或一個人/可能在代替我們死去/死去我們的悲傷、寒冷和灰燼”的互為交互,進而由此生發出自我反駁與自我放空后“死者的心態”:“從墓地返回的幽靈提醒世界/輕點,輕點,別讓天平傾斜”;在《適得其反》中,詩人則用波瀾跌宕與適時反轉的推進方式入手:“男人找尋著女人,女人找尋婚姻/兒子找尋著母親,母親找尋父親/花朵找尋露水,夢找尋現實/呵,一切應該適得其所……”,但在他們臉上洋溢的幸福笑容中發出呼喊:“但風找尋什么,她吹來吹去/但月亮找尋什么,她兀自散發清輝/請告訴我,請不要伸出手來安慰”。而在更多的時候,此種小詩也以三月桃花浮于水上的片片詩意,展現了微小事物、瞬間感受中的情感悸動、心靈征戰與語言暴動。這些詩意所蘊含著的,或許是歷史的罪感(如《曹植:點燃燈,會更看見黑暗的事實》《慈壽寺塔》),或許是性靈的律動(如《書生與女鬼》《凝視———香積寺門前的乞討婆婆》),或許是靈魂的震顫與普遍的幻滅(如《山間來信》《大象之死》)……而凡此種種,都很好地詮釋了小蟲的河流中“一生”與“此刻”的關系,一生便是此刻,此刻便是一生,而在此隱秘世界的瞬息詩情捕捉中,基于眾生的良善、寬容與愛,顯得尤為可貴。
長詩,是詩人華巖寺階段,同樣重要的存在。如果說,小詩是小蟲河流中瓣瓣飄落的桃花,那么長詩則是詩人“燕山雪花大如席”式語言風暴呼嘯搖曳下漫山遍野的桃花雨。這其中,除卻我們前面提及的《一個詩人怎樣成為詩人的》,最有分量的便是寫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間的、有著60節之多的《本心錄》。在此,“本心錄”化用了《景德傳燈錄》中唐代瑞峰神祿禪師關于“本來心”的偈語:“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弦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而根據詩人所附的《本心錄札記》可知,此處的“本心”所“錄”,是褪去了自我之蔽與懺悔之心后的最初之心、嬰兒之心、不退轉之心,而與之相適應,其詩風呈現出褪去機巧之心、放空歡喜之心后以“鈍”為特色的粗糙的、笨拙的、渾厚的天然之境。在《本心錄》的開端,詩人留下了這樣的詩行:
走,下了這坡,一片樹林
走,過了馬路,十字路口
草帽消失在左手邊
沿著墻根沿著
碰上蛐蛐兒向蛐蛐兒問好
碰上水,與她相愛
有次我立在站牌邊
終于決定去買紅薯
需要回到家安睡需要走,走到哪是哪
在這種遵從本心的隨遇而安中,小蟲的河流真正做到了物我一體的自然流淌,于是,在接下的俯拾皆是、靜寂開放與凋落的龍泉驛山頭的桃花中,每一瓣都仿佛有了慧根,無所留駐、無所依托卻又飛舞著自然物候的往還,葆有著陽光雨露的恩澤。在此,詩人看到了“一只螞蟻取來的露珠”,感受到了“落葉寫進詩里”的模樣,也體味到了“天和地交談過了”“你和我也愛過了”后的坦然。而另一層面,“本心”也并不意味著超然物外,在此種閑適與恬淡的同時,小蟲的河流還以赤子之心融合著“前路難行后路不退”的靜水深流的生命的重量、靈魂的重量、歷史的重量與思想的重量。比如他從寺里那位圓寂的比丘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寂滅,比如他由藏經樓前掃地的老人想到了俗世的執念,比如他從“褲腿濺了泥的羊腸小道/建文帝攜幼”的歷史傷痛中想到了“痛徹心扉的愛人”與“洶涌的波濤滾滾而來”。如是,華巖寺五度春秋輪回中“本心”的找尋,既是自然之心開悟的過程,亦是塵世之心度化的過程。而在此五載之后,小蟲的河流再度折返紅塵大地,繼續遵從本心流淌。
四、寬窄巷子———陌上之塵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陶潛的詩極為精準地描述了生命存在的真實狀態。事實上,人生在世,不過是大地上數十年的短暫寄宿而已,盡管面對不可歸去的田園“遺夢”,海德格爾借用荷爾德林的詩句曾滿懷希冀地吟唱出了“詩意棲居”的憧憬,但其實沒人可以擺脫現代城市文明的羈絆,這就如天才詩人蘭波“生活在別處”的箴言一樣。在鋼筋混凝土構筑而成的冰冷城市,在為生計奔波的無數個日子里,越來越多人處于“自我”與“世界”的加劇“割裂”中。而面對這種愈加增多的靈肉割裂的滾滾紅塵,小蟲的河流并未在華巖寺的鐘聲中停滯為一口幽泉,也沒有以“心遠地自偏”的旁觀者心態冷漠處世,而是選擇再度以“陌上之塵”的凡塵之心融入世俗,這是多么難能可貴呵。有時我甚至想,小蟲多么像宮崎駿童話故事里那些灰塵精靈,雖然身披塵灰,但卻心性純凈。
如同雷平陽所說,當你從一個菜單中看出了詩意,那么你就是一個詩人。在重歸陌上之塵的日子里,小蟲的河流常常能有“一沙一世界”的俗世發現。自《此生》《傷秋》《修傘》《配合春天》《我明白是愛情》《一個周末和曼德爾斯塔姆》等詩作中,他常常能在車水馬龍,人潮熙攘之中,于肉體在指針和雨滴的跳蕩之間,透過具體而細微的塵世之物,去探尋瞬間感受下生命存在的意義與不乏佛禪之思的隱秘空間。而在這些詩作中,2024年創作的《美食與方言》(12首)與《冰雪敘事》(9首)是尤為值得關注的兩組詩歌。因為它們,不僅征兆了小蟲的河流由佛禪之水朝向世俗之水的河道更改,也在某種程度上是他以俗世之物入詩,而詩境走向純熟的標志。在閱讀這些世俗之作時,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維特根斯坦那句名言: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是的,在這種由玄入實的“語言的岔口”中,小蟲實則是在建構晉北故鄉與川渝雙城之間,別一種富有煙火氣息的在地性坐標。前者,在對于小面的自謙(《小面》)、魔芋的深藏(《魔芋》)、泡菜處于客體位置的安然(《泡菜》)等秉性的發掘中,他常常通過觸摸方言俗語與風土民情,來展現一個浪子對于家族血脈和種群靈魂之鹽的找尋。這其中所暗含的,不但有情感層面的生生不息,也有對人類秉性中短視與愚昧的省視;后者,在《威海暴雪》《雪的聲音》《雪,作為一種背景》《雪人》等詩作中,詩人于情感的淺吟低唱與思想的死亡賦格里,實則是以悲愴的抒情深度,來呼喚深藏在凡俗世界縱深處的人間至情。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美食與方言》是一種熱氣騰騰的贊美,那么《冰雪敘事》則呈現為一種寒氣凜冽的忖度。此一冷一熱的雙向開掘,正表明了小蟲的詩歌在世俗之河中,朝向寬廣與縱深兩個向度的努力。
而從更深層來看,個體與世界的命運關聯無疑是根本的。在小蟲之河于晉北大地與巴蜀之地,華巖寺與寬窄巷子之間曲曲折折的往返流動中,無疑承載了我們這個時代極具更迭、流動性質的靈肉縮影。這正如他自己所言,成為一個詩人,仿佛冥冥中的安排,而所有命運遭際的千百流轉,一切世間萬物的生生不息,之于作為生命個體的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偶然集合、共振交感與悄然轉化。或許,同為詩人的王夫剛對于小蟲詩路人生的美好期待,是較為理想的狀態,那便是“背負著華巖寺的風聲和教誨,做寬窄巷子的常客偶爾一醉方休”。
五、而此刻停筆,聽著蟲鳴
在2024年《青年文學》的第9期,小蟲發表了題為《燈盞或古老的心》的文章,來表達自己“燈傳無盡”的虔敬詩藝觀。在他看來,詩歌最美妙的境界便是佛家所言說的“拈花一笑以心傳心”。而從生命個體出發,詩人與詩心又是一個融合性載體,唯有像杜甫那樣有著心系蒼生、大悲同體的“古老的心”的燈盞,從一只手傳遞到另一只手,方能建立起廣闊的人文視野和精神高度,也才能接近詩歌峰頂的那顆明珠。在小蟲的詩藝觀中,我們能感受到他走過的一條繼承古典詩學、朝向現代詩歌邁進的路徑。這種對于古典傳統的傾慕之情,讓人不由想起前輩詩人沈奇2010年在《美麗的錯位———鄭愁予論》中的一段話:
新詩九十年,我們走得很輝煌,也很匆忙。空前的繁榮之下,是空前的駁雜。各種主義紛爭、流派紛呈之后,是新的無所適從。僅就命名而言,我們已經有了“白話詩”“傳統詩”“現代詩”“朦朧詩”“實驗詩”“口語詩”以及“后現代詩”等等,而每一個命名之下的詩學定位和詩體指認,又總是那樣含混不清和充滿歧義。
而今,百年新詩歷程已過,倘若我們靜下心來細細思量,公允評判,便會發現,一代代詩人在“新詩”的疆場篳路藍縷,其心血和成績不可謂不深、不大,然其中也不乏諸多形式至上、概念繚亂的喧囂,從而背離了詩歌純真的詩性。對此,小蟲的詩歌創作不見得沒有缺憾,然而,其沒有在一味西化中截斷古典滋養的活水,沒有在現代批判中喪失東方文化中的“渾然一體”的精髓,這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北風卷地,白草折斷
我的一生,將在漫天的星斗
引來地上的流水
在潦草漫漶的字體
等無心的牧童于草地中辨認
或者不等,高山幾何
塵埃幾重,人在鬧市中笑
在夢中醒來———
我的一生已經漂浮起來
進入黑暗的關口
而此刻停筆,聽著蟲鳴
這,是他《夜抄維摩詰經》中的一段詩句。惟愿這條小蟲的河流,在往后的日日月月,在紛紛擾擾的塵世里,能夠恪守本心,靜聽蟲鳴,將詩歌的古老燈盞傳遞下去。
【作者簡介】董曉可,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在《小說評論》《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物發表評論作品50余萬字,曾獲“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出版有評論集《蓋茨比的鞋子》。
責任編輯:王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