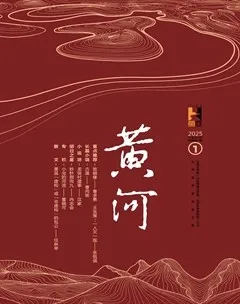大愛
婆婆是上天贈予我的第二個親娘。我十四歲時,我的親娘暴病身亡。沒娘的日子,無論我爸怎樣盡心,也不如親娘貼心的撫摸。
1971年底,我22歲,第一次踏進(jìn)婆婆的家門。
老兩口把我迎進(jìn)來,他們上上下下仔細(xì)打量我,我呀,完完全全的學(xué)生樣,兩條落肩小辮,一副白框眼鏡,不諳世事,傻乎乎樣。大概也算可他們的心吧,他們送給我的是自家人的笑臉。
看到婆婆的第一眼,我的心頭一震,恍如我的親娘回來了!
她跟我娘幾乎同齡,同樣是瘦俏身材,大襟襖,剪發(fā)頭,解放腳,慈眉善目。不同的是她操著一口地道河北方言,有些字眼接近北京話,還有的字眼仿佛在《紅樓夢》的文字里見到過。
落座后,婆婆遞給我一碗熱氣騰騰的掛面湯,上面靜臥著兩只白生生的荷包蛋。這么多年了,我在家,在學(xué)校,在單位,都吃食堂,到哪里能吃上荷包蛋?
“忙吃,忙吃!”碗到,筷子也到。
“還有餑餑,剛出鍋的。”
我含著眼淚吃下了這碗飯,不知道婆婆看到我眼中的淚水沒有。
這頓飯和愛人給我手工制作的那只煤油爐,決定了我的婚姻,我將走進(jìn)一個善良人家。
1972年5月,我結(jié)婚了。這年,婆婆即將跨入60歲。婚房是公公的友人幫我們借到的,就在距離婆婆家不遠(yuǎn)的市政大樓1單元4層。踏進(jìn)這間屋子的那一刻,我驚詫到兩眼放光。滿滿的情調(diào),在那個年代,略顯小資了點,桌子、椅子和床都是從單位借來的。桌上鋪了一條淺色的臺布,臺布上放一排他常看的書,書的旁邊還有一臺綠殼電唱機(jī),窗簾和床幃都是淡綠色帶碎花的綢布,淡雅溫馨。床上紅紅綠綠的鮮亮鋪蓋,一定出自于婆婆的巧手,每一件都是蓬松的新棉絮成,松軟厚實,針腳均勻;兩只大蓋箱里,是為我們備的換季被褥和床單,還有為我量身定做的新棉襖。為了這一天,婆婆準(zhǔn)備了多久?按票證供應(yīng)的年代,她該省了多少自己用的,大概所有積蓄都用到我們身上了。
老兩口將我當(dāng)作自己的女兒,他們不叫我“小云”,直接就是“云”。我心里清楚,他們是可憐我這個沒娘的孩子,后來我成了孩他娘,他們依然這樣叫我。
與他們相處幾十年,我在他們眼里心里,一直是被寵愛的“云”。
一
1974年2月,我的長子出生。這個月子,我跟婆婆住在了一起,我和兒子的吃喝拉撒都?xì)w婆婆脋飭。
也就是從那個月子起,婆媳倆結(jié)成了她嘮嗑我傾聽的結(jié)構(gòu)。還別說,這個結(jié)構(gòu)堅持了幾十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階段,我都是她嘮嗑的傾聽者。
她把她的家鄉(xiāng)都搬給我了,盡管,我根本沒有機(jī)會跨越太行山落腳華北大平原。這個月子,我的胃口大開,婆婆的幾種帶河北印記的“好吃的”,我不但嘗鮮了,還吃得我下奶多多,孩兒吃得胖胖的,而且將其要領(lǐng)學(xué)到手,成了我們這個小家的傳家特色飯,以至于倆兒子時不時會提請我滿足他們的味蕾。
這個月子,大部分時間是我躺著,婆婆坐在一側(cè)講她的家鄉(xiāng)和往事。聊啊聊,聊到該做飯的點了,她就在床上鋪一層油布,擺上面板,她邊搟面邊嘮嗑。她和面是真“三光”,面光,盆光,手光,利利索索。圓圓的一團(tuán)面,不大功夫便搟成了有棱有角的四方形,搟到紙一般薄時,抽出搟面棍,折疊成厚厚的長條形;然后,左手壓面右手持刀,只見一疊面,隨著手的輕移,而成條;再然后,她握住切好的面條輕輕抖動,面粉落下,把粗細(xì)均勻的面條放在一個用高粱桿制作的蓋貼上。要知道,這面條從第一根到最后一根,一樣的粗細(xì)一樣的長短。這簡直是絕活,整個過程,出神入化。
婆婆做的烙餅忒好吃,這個“忒”字就是《紅樓夢》里常出現(xiàn)的詞。就在這個月子里,我枕頭邊上放著全套《紅樓夢》,目的就是想找公公婆婆口語里冒出來的“紅”詞。家里人隔三差五要吃婆婆做的烙餅,還禁不住邊吃邊感慨“忒好吃,忒好吃”。烙餅一層脆脆的外皮,數(shù)層嫩嫩的里囊,還有大油的香味,由不得我總是吃著手里的,還要算計盤子里的,能給我再留點嗎?
有一天,我的肚子著涼了,婆婆給我端來一碗熱氣騰騰的飯,她說,你吃一碗“餃子粥”,暖肚!哈,棒子面粥里,煮著幾個餃子,還有紅薯?這是什么飯?我從來沒有聽過,更沒有吃過呀!餃子和紅薯煮在一鍋玉米面糊糊里,這該是什么味道?
我一口餃子,一口粥,再咬上一口甜甜的紅薯,咸咸甜甜,還燙燙的。一碗“餃子粥”下肚,肚子里的涼氣全消。幾十年后,“餃子粥”成了我家的傳家飯,兒子,兒媳,孫女,在寒冷的冬日里,經(jīng)常要求我做餃子粥。
顯然,面條、烙餅、餃子粥,是他們的家鄉(xiāng)飯。
他們的家鄉(xiāng)在哪里?我始終沒有去過,但從婆婆口中知道,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們那里家家有地道,村連村戶連戶,地道連成片;婆婆還說,他們家無山有水,有蘆蕩。他們離開家鄉(xiāng)時,正值發(fā)大水,就搖著船兒到保定。由此,我想起了孫犁的小說《白洋淀紀(jì)事》。婆婆還說,在老家時,我公公就加入了共產(chǎn)黨,我就構(gòu)思畫面,公公就是白洋淀里的水生,婆婆就是水生嫂子,白洋淀里的故事,有他也有她;我還將公公想象為地道戰(zhàn)里的高傳寶,在村子里帶著大家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前些年,我們還專程到保定,到白洋淀,到冉莊跑了一趟,目的是想將婆婆給我講的一系列故事形象化。其實,婆婆給我講的故事,并沒有那么驚天動地的,她周圍的人物也非常簡單,簡單到也不過就是一二三。
婆婆說,在老家時,不管在娘家還是婆家,灶臺上的活兒都靠她,一大家子,二十幾口人,下地回來,坐在炕沿吃的,站在當(dāng)屋吃的,蹲在門檻上吃的,都會發(fā)出不間斷的哧溜哧溜的聲兒,婆婆心里不知有多滿足。
婆婆是在鄉(xiāng)下長大的,她的家鄉(xiāng)在河北大平原上。娘家在任丘縣的西汜水村,因為處在四條小河匯聚處而得名,她嫁到距此處十里左右馬家村的楊家,當(dāng)然是媒妁之言。婚前她對夫家一無所知,幸虧她嫁給一戶門風(fēng)甚好的人家,夫君識文斷字還善解人意,她這一輩子,沒有受過夫家人的氣,心胸展展的。
她是家里的長媳,四世同堂,她用她的行為贏得了大家的認(rèn)可和尊重。在她的嘮嗑中,我掌握了這一大家子的輩分和名字,婆婆有公婆,還有兩個小叔子,兩個小姑子。不過,在我們的聊天中,她嘴邊流出最多的是她的兩個妯娌。大小叔子的媳婦叫大珍,二小叔子的媳婦叫秀閣,秀閣那時還沒有生孩子。婆婆和大珍的孩子,夜里會躺在各自娘親的被窩,但白日里,不分誰是誰家的,大點的帶小點的,大人們就不用操心了。有一次,大珍的女兒帶著婆婆的女兒在門前追逐玩耍,跑啊跑,經(jīng)過了不遠(yuǎn)處的蘆葦塘,掉進(jìn)了水塘。婆婆扯出了女兒,大珍的女兒后怕,惴惴不安,生怕大娘訓(xùn)斥她。大娘呢?摸摸她的頭,給她擦擦眼淚,安慰她,孩子哪有不碰不摔的?明兒,你還帶她玩兒!
三個妯娌嫁到一個屋檐下,朝夕相處,無話不談。那是她們的青春歲月。婆婆的社會交往圈不大,盡管她隨夫到過東北和北京,最后落腳于山西太原;盡管她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見到過日本鬼子掃蕩,直視過日本鬼子用步槍對準(zhǔn)了她和她的母親及懷中的孩子;盡管她在夫家三兄弟分家后,面臨著男人外出打工,她自己主持并請人蓋幾間瓦房的大事件,請短工幫著春種秋收打場,甚至踩著那雙纏過又放開的小腳帶著自己織的小布到張家口集市上去賣……但她始終出色地飾演著屋里人、母親、大嫂、奶奶(姥姥)、鄰家大娘這樣的角色,在她心目中,沒有形形色色這一說。我特別注意到,在可以數(shù)得見的關(guān)系中,只要提及大珍和秀閣,她就會繪聲繪色。我在她的繪聲繪色中,對大珍和秀閣還曾勾勒出一幅帶有動感的圖畫,那是她此生相處最好的姐妹,值得一輩子回味。
我與婆婆心理融匯從這里開始,一位沒有摸過書本,沒有點滴文化的鄉(xiāng)下女人,送給我一本厚重的書,此書蕩漾著河北大平原上樸素的民風(fēng)。
二
婆婆離開家鄉(xiāng)后,自己剛剛主持蓋起的這幾間瓦房被冷落了。她時不時提起老家的三間瓦房和院子里的那株槐樹,那是她的鄉(xiāng)愁。她也曾回去過幾次,每次離開時,都會自己問自己,那株槐樹,怎么才能天天看到?于是,她吩咐她弟弟將這株樹砍伐并鋸成板材,她聽說大兒媳婦的弟弟利生要開大卡車到天津辦事,那就委托他順道到任丘老家一趟,把這些板材拉回太原。
我曾在平房院里見過這些板材,似乎不關(guān)我什么事,也就是掃一眼而過。婆婆家搬到樓房里后,這些板材放到何處,我也沒有操過心。
可是,有一天,老家舅舅的兒子小國從天而降。
見到小國,我還開玩笑:小國來看大姑啦?
小國說,我還要到嫂子家去一趟呢!
一頭霧水,但我還是表示歡迎小國光臨寒舍。
我們剛搬家,住進(jìn)了新建的一套樓房里。那天,小國進(jìn)得門來,拉開米尺,丈量起我們的臥室。我仍然不知他的目的。
過幾天,小國畫了一幅草圖,說是草圖,但很規(guī)矩,是一張漂亮的組合柜圖,有高有低,中間還有一個桌面,算是我的書案。估計,老人跟他有交代,她這個兒媳婦是個書呆子。
圖紙上的每一個部位都標(biāo)著標(biāo)準(zhǔn)的尺寸,他征求我們的意見,看這樣的設(shè)計成不成?
原來,婆婆要把這株老槐樹送給我們了,我們的新家,正需要這么一套組合柜。
打造組合柜,要拉大鋸扯小鋸,從板材到成柜,丁零咣啷,就在婆婆家樓前那塊空地上進(jìn)行。
小國將做好的組合柜,精心上漆,風(fēng)干后,還是請利生幫著拉到我們家。恰好的位置,耀眼奪目,我們家的檔次立時提高了。
那次,小國還悄悄地跟我們說,他最親他大姑了。
這件事發(fā)生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這套組合柜跟了我們近四十年,睹物思親,該我給孫輩叨叨老奶了。
婆婆把她的最愛,給了我們這個小家。
她的心偏向于我們,左鄰右舍和家里的第三代都有這個說法。說來說去,我知道,婆婆還是憐我沒有親娘,憐我是個捧書本的人。
婆婆有三個子女七個孫輩,早就說好,以她的力量,一家能給幫襯著帶一個,可是,輪到我家了,婆婆的老主意松動了。
我的長子兩歲多時,次子出生了。既然婆婆只能帶一個,那次子就跟著我到單位,上單位的托兒所也可以呀!可是,有一個周日,我們帶孩子回家,婆婆抱著孩子來回看,不對呀!這孩子的屁股是不是坐盆盆坐大了,不行,給我送回來。
也不知道婆婆怎么就能摸出孩子屁股被“坐”大了,但我知道,托兒所里孩子多,阿姨忙不過來,就一個孩子一個便盆,坐在盆上吃喝拉尿。那也不至于把屁股坐大呀!
婆婆下令了,我當(dāng)然高興,省我多少事呀!正好,長子也該上幼兒園了,那就換個個兒。
1982年的一天,次子感冒了。我接回來,帶他到醫(yī)院。醫(yī)院的護(hù)士邊聊天邊給孩子注射,一下子,傷了孩子的神經(jīng),當(dāng)下就癱倒在地上。我沒想到那么嚴(yán)重,還是把孩子抱回了家。接下來的事就麻煩了,孩子站立不住,更別說行走了。我們帶著孩子到兒童醫(yī)院,未查出結(jié)果,又到華衛(wèi)所做檢查,確診是坐骨神經(jīng)受損,只好到北京,先后住在我大姐和愛人的堂姐(大珍的女兒)家,大姐給我找關(guān)系,跑了幾家醫(yī)院,都說是神經(jīng)受損,最好是慢功夫針灸治療。我們選擇了北京兒童醫(yī)院,一位非常和善慈祥的老大夫,堅持用漫長的三個月的時間給孩子針灸。
這三個月我們付出的辛苦自不必說,我婆婆也是經(jīng)受了日日煎熬。
有一天,我在北京收到公公的信,我念了一遍又一遍,也給孩子念,可他太小,聽不明白。許多年后,我將信找出來,發(fā)到我們自己家群里,已入中年的兩個兒子都看哭了。
公公的信,抬頭就是二民,二民是次子的小名。
信中說,你去北京已有36天了(多準(zhǔn)確呀!),我們想念你,尤其是前一個時期,想得厲害,你奶奶都夢到你回來了。我每過你們幼兒園門口,還有每當(dāng)英英、小波來找你的時候,心里就不平靜了。有一天,電視里演北京兒童商品展銷會,我和你奶奶瞪著眼看,看是不是你和你媽媽去了,看到有坐飛機(jī)、坐汽車的兒童,總想著有你們的鏡頭才好。后來看中央領(lǐng)導(dǎo)也去了,估計你們?nèi)サ牟皇沁@一天。
我們家倆老人,也有天真的時候,好像我們在北京,就會出現(xiàn)在北京的新聞鏡頭里,居然每天會眼巴巴地看著電視屏幕找他們的小孫子。
我們在北京時間長了,婆婆不放心,幾次欲動身,親自到北京來陪著孫子,似乎這樣她才放心。期間有一天,我大姐到太原出差,專門到我婆婆家看望她,并向她匯報孩子治療的效果,她才打消了親赴北京的念頭。終于,她度日如年般地將我們等回來,看到了她能活蹦亂跳的孫子。
我的兩個兒子就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有一天,他倆不小心做了一件出格的事。
那天,婆婆到后邊老王家有點事,這倆孩子居然自作主張,開火煮荷包雞蛋。坐上鍋,裝上水,再打開煤氣灶,看著水開了,倆人從冰箱里取出一小笸籮雞蛋,你一個我一個,鍋邊上輕輕一磕,水水的雞蛋就脫殼掉進(jìn)了鍋里。倆人玩得高興著呢,根本不顧及往鍋里甩了多少個雞蛋。一個小笸籮呀,怎么也有十大幾個甚至二十個,那是老人安排全家人個把月吃的雞蛋。
老人回來了,看到熱氣騰騰的場面,欲哭無淚,倆孩子恍然間知道闖禍了,靠墻根站著,準(zhǔn)備挨揍。可是,老人遞給他們的只是瞬間的無奈。
倆兒子讀中學(xué)的時候,每天午飯要回到婆婆家吃。兩個壯小伙兒,飯量可想,還得不斷變花樣啊!要按時讓倆孫子吃上飯,飯后,還必須留出充足的時間,讓他們一人一屋睡個午覺,倆小伙兒初高中各六年,中間又有倆人同回奶奶家的時間,這該是多少年啊?那些年,老兩口都是七十大幾,接近八十歲,體力支不支?似乎我們都沒有在意,真后悔。若干年后,當(dāng)我看到公公的日記本時,才知道,這期間,老兩口都曾感冒過,而且,公公還骨折過,可他們一天也沒有中斷過兩個孫子的午飯。
婆婆八十歲的那頓生日宴,我們一大家子十四五口人都聚在家里,那年,我的長子已入大學(xué),他為奶奶寫了一封信,弟弟代他念;他還給爺爺寫了一封信,爺爺自己念。我特別注意婆婆聽這封信的表情,一臉的笑容,好慈祥,好滿足,三家人依次舉杯敬祝老人身體健康時,她都要站起身來,把手中的酒杯遞至敬酒的方向,當(dāng)她聽到重孫子脆生生地喊她老太太時,尤為興奮,臉上都放光了。
三
很多年前,婆婆到北京竇店去給妹妹過六十歲生日,妹妹遞給姐姐一包石榴籽,說,咱們都這歲數(shù)了,見面的機(jī)會也不多了。這包石榴籽,也就是個念想吧。她還說,這是中南海的石榴籽,結(jié)出來的石榴個大籽粒豐腴。
婆婆很珍惜這包石榴籽,回來后,將其撒在一只大花盆里。不久,嫩芽破土而出,長枝,須根,分杈,沒兩年,大花盆顯小了,婆婆又將其移至淺缸里,順手掰下一枝壯點的,插于原來的花盆里。這枝還長得真快,沒多久,一株變兩株,成小樹了。樹上伸出了彎彎曲曲梅樹樣的枝干,枝干上繁衍出數(shù)不清的枝枝杈杈,開滿了清新靚麗的紅花綠葉,就像精致的根雕有了鮮活的生命。老兩口百般呵護(hù)細(xì)心捉弄,又在想,下一步該讓其在哪里生長?就在石榴樹4歲那年,公公單位分了新樓房,他們得到了一層靠西邊的一套,前無遮攔旁空闊,陽光充足。老兩口又在陽臺外建了臺階,臺階的兩側(cè)有兩片不足2平米的空地,他們便將此處作為石榴樹的棲身之地。為了給石榴樹生長提供良好的土壤以吸收充足的養(yǎng)分,年近七旬,即將離休的公公用小平車從郊外拉回了熟土,換掉了原來修建樓房積淀的層層灰渣。之后,施肥,澆水,營養(yǎng)土壤,再將石榴樹從缸中移出,植于其中。從此,隨著季節(jié)的更替,兩株石榴樹竟各顯其芬芳,成為家屬院的一道風(fēng)景。到了冬天,老兩口又不顧寒風(fēng)襲人,相互配合,用草墊子和草繩子將還不甚壯實的石榴樹嚴(yán)嚴(yán)實實包裹起來,以防受凍。為了不致石榴樹孤單,他們還在陽臺內(nèi)外培植了許多種盆花,諸如君子蘭、吊金鐘、串串紅、虎皮海棠、仙人掌、月季、文竹等。這些花種,大多是友人相送,不論什么習(xí)性,竟是栽一盆活一盆,四季都有色彩,四季都有芬芳。有一次,不知哪位路過的人,吃完一只杏,順手將核扔到我家小園子,居然奇跡般長起一株杏樹。
每年中秋過后,婆婆都會沐浴著暖暖的秋陽,觀賞窗外掛滿枝頭的即將咧嘴和已經(jīng)咧嘴呈現(xiàn)出成熟笑臉的石榴,她準(zhǔn)備在上凍前采摘石榴。
清晨,她喊醒還在沉睡的我的兒子,祖孫倆開始動作。小的踩著凳子,從上往下,遠(yuǎn)一個近一個高一個低一個,彎腰伸臂煞是忙碌;老的一個一個接過來,小心翼翼放在備好的笸籮里。小的摘完了一株樹,又轉(zhuǎn)戰(zhàn)另一株樹;老的,放滿了一只笸籮又找來另一只笸籮,雙眼還幫著孫子搜羅“漏網(wǎng)分子”,晌午時分,將近200個石榴被婆婆精心分成若干份,數(shù)量不等。夜晚,趁著人們都在家,婆婆借著月色,邁動著小巧的金蓮,按照自己既定的方案,將分好的石榴送到前樓后樓左鄰右舍相處有緣、對她和老伴有過些許照顧的人家,用以回報或是溝通。這些年齡都不及她的同輩或是晚輩早已將我家這兩株石榴樹當(dāng)做觀賞物,春天里,枝繁葉茂如同碧波蕩漾;夏日里,數(shù)不清的紅瑪瑙一樣的花瓶般的骨朵上綻開著光華耀目的鮮花,目擊者定然會從心中升騰出熾熱的生命感受;金秋到來時,密密麻麻的骨朵怦然長大,金樽玉盞倒掛垂懸,忽然,有幾只就像早戀的少女羞澀地咧開了櫻桃小嘴,露出了里邊的皓齒,既酸又甜的味道引誘著過往行人。當(dāng)他們從老人手中接過為數(shù)不多、但情誼甚濃的石榴時,無不為侍弄石榴樹的兩位老人投以欽佩的目光。
自然,老人還是將大部分的石榴留給了自己的七個孫子一個重孫,并作等分。為了正在成長的后代,他們永遠(yuǎn)樂此不疲。
公公婆婆離開人世已經(jīng)二十多年了,我家門前石榴樹依然茂盛。前些年,小區(qū)物業(yè)整頓院內(nèi)環(huán)境,樓前的柵欄一律拆除,但是,他們還是將我家的兩株石榴樹當(dāng)“非遺”一般保留下來,這兩株石榴樹承載了這個大院里幾代人的回憶,頗具風(fēng)骨卻又青春常駐。
四
公公先婆婆離別人世,婆婆一下子接受不了,受刺激而癡呆,曾兩次走失,我們動用了電視臺廣告找回了老人。
不明白她為什么執(zhí)意要出門,要遠(yuǎn)走,是不是她又念叨起自己的家鄉(xiāng)?她從哪里來,也將回到哪里去?
第一次丟失,這個想法就得到了確認(rèn)。她從上午就出發(fā),不知疲憊和饑餓,從市中心一直走到城南二營盤附近。夜晚,乘涼的人們看到無助的她,跟她對話時,一位操著相同口音的中年人,跟她搭上話。她心里那個高興呀,鄉(xiāng)音即知音,好像是回到馬家村。人家把她請到家里,給她喝水同她聊天,忽然間,從電視上看到了我們發(fā)的尋人啟事,馬上給我們電話聯(lián)系,我們方才開車把她接回來。
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哪怕是夜里。
有一次,我陪她過夜。她很精神,整理了一個包,對我說,你看好家,我去去就回來。沒辦法,我攔不住她,她在前邊走,我在后邊跟,我怕她摔跤,想扶又不敢,她交代我的任務(wù)是看家呀!當(dāng)她走到大門口,看到鐵門緊鎖,竟然雙手把著鐵門,要翻門而過。那種義無反顧,真的阻攔不住。我想起我大伯子也遇到過這樣的事,當(dāng)時,我大伯子跟她說,咱們回去套好車,一起走。這話,她聽得懂,在老家出門時,不就要套上馬車才能上路?我也這樣說,還真起作用。回到家,她又把包兒打開,對我說,云,你記住,這個是給大珍的,那個是給秀閣的……
她的思維完全回到了青年時代。
她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外走,有過兩次走失的教訓(xùn),身邊不敢沒有自家人。我們都還在職,輪流著來吧。她每天走的線路基本是,出院門往西,拐入半坡東街,再拐到府西街,然后,進(jìn)奶生堂,再到羊市街。少也有三五公里。回來的路上,她已經(jīng)累得癱靠在了我身上,一身疲憊的我,也只能用自己的身子把她拖回到大門口。給她買根雪糕,在大門口的石凳上稍稍休息后,她居然又重振旗鼓,欲繼續(xù)走。這時候,我真的無奈了,可她還振振有詞。有時候是街坊們用句分散她思維的話打岔,她才跟著我回家。
累了,她會乖乖地把雙腳放進(jìn)熱水盆里,任我給她搓搓腳,腳心腳背地給她按摩一下。她懂得,我把左腳給她搓完,她就會將右腳給我伸過來。那個時刻,她又那么乖順。我很難受,一雙小時候纏裹過的腳,腳背凸起,腳心彎弓,五個腳趾有四個腳趾也殘忍地貼在一起,連腳掌都看不到,怎么能落地?又怎么走南闖北的?臨終這三年左右,她每天不知疲倦地走在同一線路上,那雙腳該有多疼?如果心中無信念,她斷然不會這樣不管不顧。她真的是在想家,想她河北的老家。
我和婆婆相處幾十年,非常了解她,她在家說一不二,所有的人都聽她的。我沒有見她吼過誰,有時候,她想說誰不好,頂多就是三個字話“那行子”,這三個字怎么寫?字典里查不到,我也就只從她嘴里聽到過。幾十年,她對我說過最嚴(yán)重的一句話,是說我“燒包”。那是因為我想戴那只愛人給我買的梅花表。當(dāng)初我舍不得戴,先讓婆婆鎖起來,當(dāng)我想戴,跟她開口要的時候,她來了一句“燒包”。是玩笑,我先笑了。有意思,這只婚前愛人給我買的梅花表,是婆婆給我戴到腕上的。
婆婆一生沒有進(jìn)過醫(yī)院,是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無疾而終的。那些天,思維總沉浸在遙遠(yuǎn)年代的婆婆,居然對我,她這個兒媳婦心中有數(shù)了,好像她知道我買好到了武漢開會的飛機(jī)票。她算好了日子,在我出發(fā)的前四天,在睡夢中靜靜地走了。那是2001年,她88歲。
知我者,我的婆婆,我的娘親!
我的婆婆,名叫李大愛。三十年了,我在這個家庭得到的愛,是無盡的大愛。
【作者簡介】劉小云,網(wǎng)名蕾怡,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中國金融作家協(xié)會、中國散文學(xué)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陸家兒女》(合作)、文學(xué)評論集《云心思雨》、人物傳記《層林盡染》、散文集《情到深處》《峰高水底清》《曉云秋語》《曉云散語》等。
責(zé)任編輯:曹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