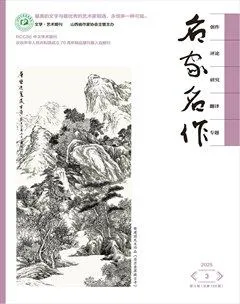貓去哪兒了
我問母親:“如果要跟別人講那只小貓的故事,會從哪兒開始說呢?”
“有什么好講的,都不知道跑哪兒去了,小破貓。”
的確,已經三天沒見到它了。喂養成習慣后,母親每天都會把中午剩下的飯菜挑選一遍,然后裝在一個小罐子里,放在門前的臺階上。她和那只怯生生的小貓似乎形成了某種默契:把食物放下后就走,等她一進門,小貓立刻就不知從哪兒竄出來大快朵頤。
母親對那只小貓的記憶似乎只剩下它的不辭而別。這也難怪,她小時候家里養過一貓一狗,那只黑色的貓悄然離開,只有那只大狼狗陪著他們一家直到返城——對了,來我家的這只小貓也是黑色的,不知是否讓她想起了小時候家里那只出走的貓呢?
打我記事起,聽母親講這一貓一狗的事不下十遍,以及每遍講完都要加上的一番感嘆:貓都是嫌貧愛富的,只有狗會一直忠誠。
不過,當看到那只跟巴掌差不多大、瘦得幾乎只剩一層皮的小貓出現在院子里時,她并未驅趕,而是每天一次從未間斷地投喂。直到有一天,她進門時興奮得像個小孩:“小貓現在好像沒那么怕人了,就一直蹲在旁邊,盯著我把碗放下。”
于是我也興沖沖地買了貓糧,有小魚干、鴨小胸。不過可能是因為小貓和我不熟,每每我靠近它經常棲居的快遞盒子時,它會先從盒子里小心翼翼地探出小腦袋,本就不小的一雙眼睛在對上我的目光后又迅速地睜大,然后以極其敏捷的動作從盒子里跳出來,躲進車棚看不見的角落里。
我明白,如果我不從它的視線里消失,它絕對不會從那個角落里放心地出來。于是我把食物放在它的盒子上就離開了。過了大概半個鐘頭,我再回去查看,盒子上的食物已經不在,便放下心來——我和小貓也形成了一種默契。
母親說:肯定是幾天前被旁邊人家那個調皮的小孩嚇到了,所以不來了。
根據我一進車棚小貓就被嚇得四處逃竄的幾次經歷看,它的確很容易受驚嚇。
有一次下班到家時已夜深,小貓大概是沒想到這個點還有人會來打擾自己,正放心地橫在院子中間打滾,隨即被我這個不速之客嚇得魂飛魄散,想立即尋個隱蔽的角落鉆進去。幾次碰壁的它腳步明顯慌亂起來,最后猶豫再三,從車棚底下的那條縫里鉆了進去。整個過程也就短短幾秒,等我回過神來,它早已無影無蹤。
我想起母親曾經說過的:貓的身體是軟的。所以每晚就算關上車棚門,第二天早上去看,小貓都在里面睡覺。
它鉆門縫的動作好像不是那么的順暢,即便身體是軟的,而且幾乎沒有一點多余的脂肪,但想要從那狹小的縫里通過也確實要費點勁。可能對于流浪動物來說,一個能遮風擋雨的地方,足夠它們拼命。不過,如果這只小貓慢慢長大,那它可能又要尋找新的居處了——身體再軟、再瘦,面對那條縫也會無能為力。
譬如它的貓媽媽——母親稱呼其為“老貓”。至于它們的親屬關系,是我們根據二者的花色推測的,都是通體黑色中零星地夾雜幾縷棕黃——只能暫住在旁邊的空調井里。它應該是從空調井外側通風板底下的空當里潛入的。
那里面的空間對于老貓來說,應該足夠舒適,因為它很少出來,連叫都沒幾聲。聽母親說,每天基本都是小貓睡醒后鉆出來,在空調井外面“嘰嘰哇哇”地叫喚許久,老貓才懶洋洋地爬出來。母親不由得又感慨一番:難怪兩只貓都那么瘦,這么懶怎么找吃的呀?
這個“疑惑”很快就解開了。有一天,母親照例把小罐子放在臺階上,小貓先歡快地跳過來,誰知還沒吃幾口,老貓突然沖出,一下子就把小貓擠到邊上。聽母親說,最后只給小貓留了一點點殘渣而已。
這讓母親怒不可遏。
“這老貓,還搶小貓的東西吃!”
人憤怒時興許會改變對事物的既定認知,這時候母親就想起了老貓在空調井里的“暫住”。
“把里面弄得臟‘死’了!”
母親富有智慧且行動力十足,她先是鋸了一段木板擋在那段空當上,然后每天喂食時,把小罐子放在車棚里——這樣只有小貓能進得去。
每天看著小貓吃飽喝足,而老貓只能在外面晃悠,母親就像打了勝仗一樣滿意。
不過母親并沒有滿意太久。老貓離開后沒過幾天,小貓就再也沒出現在那個盒子里。母親放在臺階上的小罐子,里面的食物也沒有被動過的痕跡。
還好,手機里存了不少之前偷偷拍下的照片。當我翻閱相冊時,發現幾乎都是一老一小兩只貓在院子里玩耍,小貓特別喜歡鉆在老貓的尾巴底下。
作者簡介:張存寬,男,現居江蘇南京,南京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