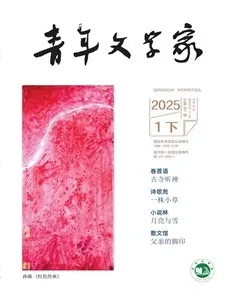黃庭堅吉州送別詩作試析
送別詩是詩人酬和應贈的重要品類。自古以來,送別總能激發詩人不同尋常的感情,在交通、書信等條件狀況極度不發達的情況下,離別也變成了具有“很長時間再難相見”的特殊意味的場景。詩人在這一刻迸發出的情感是促使其進行創作的極大因素。送別詩是詩人面對人與人的交際中一項重大事件的思想展現,對于送別詩的賞鑒,也是分析詩人思想流變與心境的重要途徑。
對于《黃庭堅詩集》中送別主題的詩歌關注,可以從一個角度理解黃庭堅的交際思想、個人選擇等;而分析其送別詩的思想內涵與情感傾向,也可以體現黃庭堅在特定的歷史和時代條件下內心世界的發展變遷,管窺其精神世界的一隅。黃庭堅早年在吉州地區做官,他的思想底色很大一部分源于在吉州任上的思考與學習,通過黃庭堅在吉州地區所作的送別詩篇,也可以看出后來黃詩的精神雛形。
一、黃庭堅送別詩分析
(一)《贈別李次翁》
《贈別李次翁》是黃庭堅在元豐五年(1082)壬戌所作。黃庭堅在元豐四年(1081)到達吉州太和縣任職,其間,他親眼所見民生疾苦,產生出對新政的不滿。但是,現實政治也帶給他巨大的心理矛盾。身為政府官員,他必須執行上級布置的收鹽任務,但目睹百姓生活的困苦與凄慘,他的仁政之心又與自己的職責發生巨大的沖突。“飽食愧公家,曾無助毫末”(《二月二日曉夢會于廬陵西齋作寄陳適用》),“既來授政役,謠詠謂余欺”(《丙辰仍宿清泉寺》)等詩句都反映了他處在現實政治下矛盾的心理狀態。在這樣的心理矛盾之下,他在這一時期所寫就的《贈別李次翁》便帶有濃厚的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色彩:
利欲薰心,隨人翕張。
國好駿馬,盡為王良。
不有德人,俗無津梁。
德人天游,秋月寒江。
映徹萬物,玲瓏八窗。
于愛欲泥,如蓮生塘。
處水超然,出泥而香。
孔竅穿穴,明冰其相。
維乃根華,其本含光。
大雅次翁,用心不忘。
日問月學,旅人念鄉。
能如斯蓮,汔可小康。
在俗行李,密密堂堂。
觀物慈哀,涖民愛莊。
成功萬年,付之面墻。
草衣石質,與世低昂。
開篇即言“利欲薰心,隨人翕張”,這一句可以明顯看出黃庭堅對于求利的官員的大肆抨擊。黃庭堅首先目睹了任職期間官場的腐敗,官員們中飽私囊與百姓生活困苦的對比,官府為了斂財而賣鹽的利欲熏心的表現,方在贈別時提筆便將此現狀點出。但是,身處這一體系內的黃庭堅并不能對現狀作出影響與改變,反而遭遇雙方的排斥與拒絕。對于百姓而言,他屬于征收者的立場,天然與群眾站在對立面;而身為政府的一員,他又從內心質疑秩序的合理性。現實中的苦痛使他逃向道家與佛家思想,尋求精神上的皈依與純粹。他不愿再在流俗中遭受心靈、道德與職責的多方面譴責,而盼望辭官歸隱,歸于佛道的思想也在后文展現:“于愛欲泥,如蓮生塘。處水超然,出泥而香。孔竅穿穴,明冰其相。維乃根華,其本含光。”這幾句化用的是《圓覺經》《維摩經》《超日經》。黃庭堅在向李次翁訴說他的建議,這也是他希望自己成為的樣子。他希望身處于世俗的泥潭中仍能保持蓮花一樣的清凈自然,自身的現實無法抽離,就必須讓精神獲得救贖,達到超然的境界。從這個角度來看,黃庭堅也頗有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其五)的鬧市中處世的追求,希望自己首先做到修心。而在最后,黃庭堅又回歸到對俗世的關注,認為做到像蓮花一樣的品性,便可以達到一種“小康”的境界:“能如斯蓮,汔可小康。在俗行李,密密堂堂。觀物慈哀,涖民愛莊。成功萬年,付之面墻。草衣石質,與世低昂。”學會在俗世中自處,學會使民敬己的方式“莊”,最后臻至“與世低昂”的境界,這才是黃庭堅所要追求的,也是他用以在現實矛盾中尋找支點的方式。他將這個思想傳遞給他送別的朋友,與友人“共勉”的意味則更加明顯。
(二)《送劉季展從軍雁門二首》其一
《送劉季展從軍雁門二首》其一寫于元豐六年(1083)。此時,黃庭堅尚在太和縣任上,在與公家事的糾纏之中,他隱逸的思想日漸強烈。《登快閣》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詩中寫道:“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與此相應的,《送劉季展從軍雁門二首》其一體現出黃庭堅與朋友交往的側寫:豪爽、肆意。
劉郎才力耐百戰,蒼鷹下韝秋未晚。
千里荷戈防犬羊,十年讀書厭藜莧。
試尋北產汗血駒,莫殺南飛寄書雁。
人生有祿親白頭,可令一日無甘饌。
黃庭堅不吝惜夸贊好友的筆墨,“劉郎才力耐百戰”。他將仕途通達之愿慷慨地贈予友人,祝愿友人此去建功立業。同時,在夸贊、祝愿之余,他也沒有忘記對友人的規勸:“試尋北產汗血駒,莫殺南飛寄書雁。”不要殺南飛的大雁,不要以貨取得官職,要廉潔奉公,對得起自己,無愧于天地。在面對青云直上的友人時,黃庭堅能夠順著世俗場中的期望,為友人獻上祝福。這世俗祝愿里也摻雜著黃庭堅對廉政的期待,他將理想寄托在友人身上,希望友人可以做到無愧于心,無愧于百姓,這種風格也頗體現出黃庭堅耿介而風骨崢然的特點。而在結尾,黃庭堅在承續對友人為官的贊美與期待書寫的同時,也透露出頗為“黃庭堅式”的為官思想。“人生有祿親白頭,可令一日無甘饌”,此句闡述了為官的目的。黃庭堅認為,為官是對父母的報答,是孝的體現。這句詩雖說闡述為官的意義,卻透露出黃庭堅難以抑制的歸隱之思與矛盾情緒。隱逸的思想不能直接應用,對于歸隱的追求也只好屈從于現實物質。只要黃庭堅仍處于官場中,他就經歷著割裂的苦痛,而像陶淵明那樣卸去所有負擔完全放任自流,對于黃庭堅來說又有著諸多牽絆。“人生有祿親白頭,可令一日無甘饌”,這不僅是黃庭堅在勸說友人,更是黃庭堅在勸說自己。他向自己的內心反復確認,他的為官是為家人、為父母,以此來為自己艱難的現實處境尋找動力。因此在面對友人離別時,用作告別的話語便自然地傾瀉而出。黃庭堅完成了對自己的心理暗示,但其中更深層透露的,還是他在官場中的痛苦與難以逃離的無奈,展現出隱逸的深層追求。
(三)《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
《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一詩,寫自元豐六年(1083)六月,這首詩也體現著黃庭堅強烈的隱逸思想。劉士彥出任福建轉運判官而與黃庭堅告別,黃庭堅借告別之機向他表達自己的隱逸思想。
秋葉雨墮來,冥鴻天資高。
車馬氣成霧,九衢行滔滔。
中有寂寞人,靈府扃鎖牢。
西風持漢節,騎從嚴弓刀。
惟閩七聚落,惸獨困吏饕。
土弊禾黍惡,水煩鱗介勞。
南驅將仁氣,百城共一陶。
察人極涇渭,問俗及豚羔。
官閑得勝日,杖屨之林臯。
人間閱忠厚,物外訪英豪。
詩中用了許多經典的道家意象,如“中有寂寞人,靈府扃鎖牢”,根據任淵的注釋,即化用自《游仙詩》《莊子》《淮南子》。“西風持漢節,騎從嚴弓刀”,化用典故,擬寫朋友遠赴福建上任的事件。“惟閩七聚落,惸獨困吏饕。土弊禾黍惡,水煩鱗介勞”,寫福建之地自然條件惡劣,百姓生活困苦,吏治腐敗,難以管理,對朋友此行前去表示了擔憂。但是,在這樣的山窮水惡之地,黃庭堅也相信友人能夠將其治理得井井有條,他構想了一幅友人到任之后惡地換新顏的美好場景。這也與前文極力敘寫所至之地的難治理形成對比,越難、越險,友人的能力越強,越值得敬仰與尊崇。黃庭堅希望朋友在政績上能有一番作為,同時,他也對朋友的精神境界表達了期待與祝愿,朋友不僅是“人間的忠厚”,在精神境界上,朋友也該是當之無愧的“英豪”,擁有身處塵世卻超然物外的曠達精神境界。黃庭堅對這種精神境界極為推崇,并以此來寄托對友人的美好祝愿。
《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也是黃庭堅的一首寫心之作,透過他對友人的祝愿,便能看出他對于何事看重,以此來推斷他的思想。他既渴望功名、政績這些世俗上的、物質上的事物,又追求超脫于凡塵俗世的精神境界。這一點與其在《送劉季展從軍雁門二首》其一中所展現出的精神追求與現實需要的矛盾一脈相承,功名、官職是他的立身之本,“身欲免官去,駑馬戀豆糠”(《己未過太湖僧寺,得宗汝為書,寄山蕷白酒,長韻詩寄答》)。但是,對現實情況的無能為力與民眾的不理解,摧垮了他對現實吏治的期待,轉而尋求精神上的解脫,認為“物外的英豪”才是值得推崇的對象,只有在精神境界上達到超脫才是真正的成功。
二、黃庭堅送別詩與吉州之聯系
吉州是山水佛禪的勝地。黃庭堅在吉州地區受到了相當多的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他對于佛家的出世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和理解,因此能從佛教中尋求慰藉,并將此作為指導自己精神生活的圭臬,在精神上獲得真正的解脫。在吏治上走投無路,轉而去尋求宗教的慰藉,是文學史上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黃庭堅即印證了這一“傳統”,但其現實的苦難并不是因為官職低微,沒能進入國家權力核心,而多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他想要改變民生,但他東西奔走,卻收效甚微,“四方民嗷嗷,我奔走獨勞”(《次韻任道雪中同游東皋之作》),“尚馀租庸調,歲歲稽法程。按圖索家資,四壁達牖窗。掩目鞭撲之,桁楊相推棖”(《己未過太湖僧寺,得宗汝為書,寄山蕷白酒,長韻詩寄答》)。螳臂當車的無力,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微不足道,所有的努力都被湮沒,作為一個小吏被無法改變的現實與善變的人心磨平了氣焰與激情,一切的一切都是讓他投向宗教懷抱的推動力。
宗教是虛假的意識形態,卻有著真實的療愈作用。在吉州任上的黃庭堅是割裂的,一面纏繞在公家的俗世之中,另一面隱匿在吉州的山水與佛教禪宗的懷抱之中。這也構成了他將來在朝中為官時的精神底色,無論現實多么苦痛,至少他還有一處自己開辟的個人精神園地可以往矣,至少還有山水的懷抱為他敞開,無須去考慮善變而復雜的人心。這是黃庭堅自吉州任上以來完成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如他后期詩作《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中即有言:“遙知更解青牛句,一寸功名心已灰。”他對于佛道思想的推崇與研討,對于佛道觀念的踐行,成為他平衡現實與內心的支點。
從黃庭堅寫于太和縣任上的三篇送別詩作看,黃庭堅的隱逸思想在這一時期已經初具雛形。“逃離”成了他作品的一個潛在主題,他要逃離令他苦痛糾結的現實,又因為現實原因而不得不對官場仕途俯首系頸。但事實上他無法逃離,便在精神上尋求皈依,佛道思想便多體現在他的詩作中。皈依佛禪,皈依老莊,構成了他的精神底色,向外求索的路徑遭遇挫折,轉而向內求索,發覺內心空茫境界,這條創作的線索就此浮現,并貫穿于黃庭堅詩作之中。